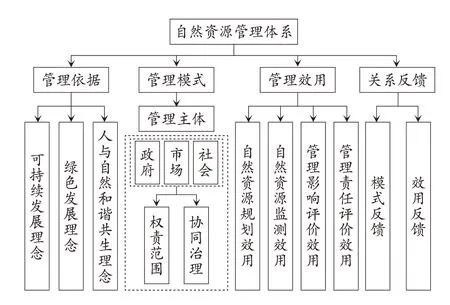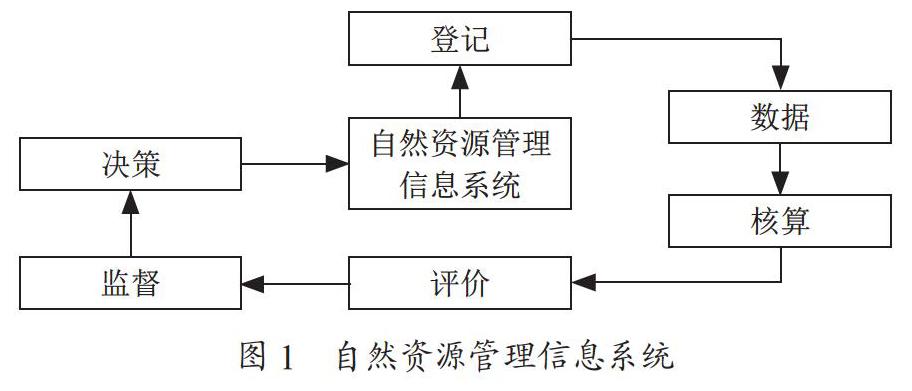摘要: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理论上这个要素能够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现实生活中自然资源常常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提高,而缺少自然资源的地区反而可能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本文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增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的重要部分,并发展了一个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变化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来解释“资源诅咒”现象。资源收入通过直接减少工作动力和间接导致较小的从事创新的劳动力比例两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诅咒;创新;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F0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50-09
一、引 言
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福还是祸?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经济增长是靠消耗自然资源为前提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资料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激烈争论,有人将其视为“神赐天粮”,是来自自然的祝福;也有人将其斥为“魔鬼的粪便”,广大民众并没有从这些资源开采中受益,大多数人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资源丰富反而陷入了贫困陷阱,给人们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诅咒。资源丰裕国的经济表现往往不及资源缺乏国,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资源的诅咒”也由此而来。“资源的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着名命题,其涵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那就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现得极为突出。20世纪的非洲(资源丰裕的国家居多数)和瑞士、日本(资源缺乏国)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还有盛产石油的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国与资源贫瘠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之间的经济差距。颇为残酷的事实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等等。
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资源的诅咒”这个概念。Sachs和Warner[1]的论文是有关该命题的经典文献,对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Sachs和Warner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以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国的资源禀赋,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负相关联系,“资源的诅咒”在国家层面上得到验证。此后,Sachs和Warner[2-3]、Gylfason et al[4]、Papyrakis和Gerlagh[5]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资源的诅咒”这一假说,自然资源丰富对经济增长更多地起着阻碍而不是促进的作用。
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增长更慢?解释资源诅咒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里最令人感兴趣的焦点之一。
目前,国外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命题:自然资源如果对其他要素产生挤出效应,就会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Gylfason[4]称之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TransmissionMechanisms)。常见的传导机制包括:贸易条件论、荷兰病、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Hausman和Rigobon[6]认为,理解自然资源的作用机制问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大部分文献只是从某一角度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实际的作用机制很可能是多种渠道的共同影响,不同的研究对象也会表现出相异的内在机制。
环顾国内我们同样会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山西、东北、西部等地其经济绩效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经济处于一个奇怪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经济始终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称的落后状态。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徐康宁、韩剑[7]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并把它看作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构建一个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重点考察我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徐康宁、王剑[8]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该命题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滕春强[9]从“资源诅咒”理论出发,对我国三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根源进行了重新诠释。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瓶颈的约束和如何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上,而对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基本上毫无意识。自然资源的多寡已不再决定一国的财富水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促进还是延缓作用?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究竟起着何种作用,是福音,还
① 早在1928年,Ramsey就提出了消费优化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型,当时未受到足够重视,直到1965年,Cass与Koopmans才重新发掘并推进了Ramsey的工作,使之成为现代增长理论的一种标准模型: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某一个目标函数的最大值,这个目标函数即为一般意义下的效用函数。
是诅咒?抑或两者都不是?丰富的自然资源能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引导我们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基于一个文献中几乎被忽略的资源丰裕挤出效应的视角:挤出创新。Sachs和Warner[3]指出
资源部门的工资水平可能诱导创新者在初级部门而不是RD(研发)部门中从事创新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发展这一假说。知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导要素,技术进步、新创意的发现和创新驱动了经济长期增长。知识产品和研究开发具有溢出效应,规模收益递增。本文选择了内生增长理论中的RD模型,一方面是在不考虑制度与伦理的前提下,技术的选择与创新是解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基于资源富足挤出创新的效应视角,技术进步、新创意的发现和新发明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本文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变化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Ramsey-Cass-Koopmans)模型①。在这个模型中,个人根据效用在消费和闲暇中进行替代配置。第三部分把资源禀赋、创新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得出动态均衡和主要命题。在一个经济体中,资源禀赋减少了稳态特征的劳动供给。资源租金使人们减少劳动供给和工作动力,并用资源收入来增加额外消费。进一步,得到自然资源富足通过导致从事创新活动人员的减少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结论。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 关于自然资源和RD的模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内生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增长理论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Romer假定由Arrow发现存在于某些行业中的“边干边学”现象可推广到整个宏观经济,从而构造出由“边干边学”机制带来递增报酬的总量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边际报酬不再递减,从而获得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率为正数的稳态增长轨迹。Lucas对Romer的“边干边学”假定进行修改,从人均而非总量资本水平对“边干边学”的反馈来描述类似增长过程,也获得了类似于Romer的结果。其它如Grossman和Helpman等人从RD出发,将RD活动视为具有投入产出机制的经济活动并分析其最优规模,也成功地将Solow技术进步内生化。虽然新增长理论解释了技术进步的形成机理,但在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仍然表现出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例如,Aghion和Howitt承认应当考虑自然资源和污染,但在他们的熊彼特模型中,智力资本的积累会克服经济活动的生态极限。在Barro、Romer和Lucas等人的增长模型中,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了全部资本。在他们看来,人类总是有办法获得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因此没有必要从自然界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现有的内生增长研究文献却较少关注自然资源问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从内生增长模型出发引入自然资源约束。在新增长理论中引入自然资源有利于说明自然资源的作用机制。本文考察一个封闭经济,整个经济分为四个部门:制造业部门、中间资本品(耐用品)生产部门、研发(RD)部门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不考虑人口增长,假设劳动力供给固定的,既可以投入到制造业部门,也可以投入到RD部门从事技术的研发,即研究开发新的设计方案。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研发部门使用投入的劳动力结合已有的技术知识存量进行研究开发,然后将新研发出来的设计方案注册为永久性专利并出售给下游的资本品生产部门;资本品生产部门使用购买来的中间产品设计方案生产新的中间产品(耐用品),然后将新生产出来的中间资本品再出售给制造业部门;制造业部门使用其购买来的新的中间资本产品,同时雇佣一定量劳动力进行生产;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开采获取资源。经济中最终产出由制造业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提供。
(一)消费者
家庭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选择跨期的消费水平和闲暇时间。把内生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在劳动附加型经济中,技术进步才能保证增长的稳态性。人们越是努力工作,创新和知识就越有效率。
假定人口在每一个时点上保持不变,那么
N(t)=N(1)
对于这类型的模型,稳定的人口水平是个有利假设,这就排除了单位资本产出长期增长率并可以使经济收敛于平稳增长路径。
个人在工作和闲暇中分配其可用的时间,l(t)是他们用于工作时间的比例,1-l(t)部分用于闲暇活动。这样,经济中劳动投入水平L(t)就得出来了:
L(t)=Nl(t) (2)
每个家庭最大化一生的效用,其跨期效用函数如下:
U=∫∞0u[c(t),l(t)]e-ρtdt(3)
其中c(t)=C(t)/N表示在t时点上人均消费;C(t)代表总消费;ρ为贴现率,并假定为正和不随时间变化,即人们在评价未来的效用时相对于现在效用而言要小些。U(t)是未来贴现的总效用,u(c(t),l(t))表示某个人在某个时点的即期效用函数。
假定即期效用函数u(c(t),l(t))与消费c(t)正相关,与劳动强度l(t)负相关。为了简便,假定一个对数的消费效用函数和有常数弹性σ的无劳动的效用函数,同时在接下来分析中省略任何贴现率。
u(c,l)=lnc-l1+σ(4)
每个家庭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时面临以下预算约束:
v·[]=wl+Q[]N+rv-c(5)
v=V[]N代表每个人持有的资产价格,加一点表示其对时间的导数。wl和Q[]N表示每个人的工资和资源收入,r是从每单位资产价值获得的真实利率。每个家庭在预算约束方程(5)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所以,构建以下汉密尔顿(Hamiltonian)函数:
H=∫∞0(lnc-l1+σ)e-ρtdt+μ[wl+Q[]N+rv-c](6)
关于控制变量c和l以及对偶变量μ的一阶条件得到拉姆齐法则(Ramsey Rule)(7)和 等式(8),它们描述了随着时间的过去,消费的演变以及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率。
c·[]c=r-ρ(7)
(1+σ)lσ[]c=w(8)
(二)生产者
假定经济体是四部门经济。首先是制造业部门,对于劳动和其他中间投入规模报酬不变。在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价格规格化成效用。依据Romer(1990)模型,采用了连续中间资本品的常规表述,表示成i∈[0,A]。每个中间资本品表示不同的设计,设计总量A测量出总的知识存量。所有的设计不能完全替代,替代水平以参数α(0<α<1)来表示。这样就可以得出制造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M=(γL)1-α∫A0xαidi (9)
γ(0<γ<1)是在制造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比例,xi是i种资本的投入。
制造业部门的厂商进行竞争性生产和选择一定劳动和资本品来追求利润最大化:
max[]γL,xi(γL)1-α∫A0xαidi-wγL-∫A0pixidi(10)
w表示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pi表示耐用品i的价格。一阶条件意味着制造业部门的厂商对劳动力和耐用品的需求为:
w=(1-α)(γL)-α∫A0xαidi=(1-α)YM[]γL(11)
pi=α(γL)1-αxα-1i(12)
得到式(11)和(12)式的一阶条件,说明厂商以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来支付其报酬。
其次,所有中间资本品都是这个资本品部门生产的。每个耐用品是不同的厂商以截然不同的专利或者创意生产的。这就意味着所有中间品的制造厂商拥有垄断能力,由于他们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产品的特征由独特的创意所决定。专利和版权的相关法律允许特有的厂商通过购买和拥有这设计来使用专有创意和生产相关的中间产品。引进创新的固定成本或设计的购买费用后,每个中间产品部门以其资本投入比例来生产一个耐用品。这样的话,中间产品也可以看作耐用品,K=∫A0xidi,K是总资本量指标。
在中间产品部门生产的厂商以价格PA购买一个设计的所有权,引进这个设计购买的固定成本,最大化利润π:
max[]xi πi=pi(xi)xi-rxi(13)
pi(xi)是制造业部门厂商对耐用品的需求函数,所以pi(xi)xi是每个中间产品部门的收益,rxi代表厂商生产耐用品xi的利息成本。由xi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dpi(xi)[]dxixi+pi(xi)=r
考虑到耐用品的需求函数(12)后,可以看出每个耐用品的垄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对于每个设计而言是相等的:
pi=p=r/α(14)
正如(14)式所示,所有的中间资本品按同一价格出售。 由于需求函数(12)涉及到单个中间产品生产,(14)式表明制造业部门购买和使用的耐用品是同一数量x。所以,可以得到:
K=∫A0xidi=Ax(15)
利润使得一项设计所有权成为有价资产,其价格为PA,这样它们可以组成这个资产价格的收益:
rPA=π+P·A(16)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等式可以简化为rPA=π。
再次,假定一个根据设计生产新中间产品的RD部门(Romer,1990),这个部门增加了知识基础。它使用部分的劳动力投入,即没有在制造业部门使用的剩余劳动力部分。相对于劳动力而言,知识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这个特殊性归结于努力的副产品,而非RD部门研究人员的正溢出效应。并且设计的生产取决于被发现的知识存量,两者正相关,是一对一的关系。这就说明创新增长率(设计存储率)独立于知识水平。RD部门研究人员可以免费获得知识,知识作为公共品,并促进创新。设计演变的依据:
A·=A(1-γ)L(17)
知识生产于创新部门,这个部门的劳动力获得边际价值。每个发明设计以PA的价格卖给中间产品部门的厂商。创新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变为:
w=APA(18)
最后,假定有一个自然资源开采部门,资源部门的产量Q取决于可获得的资源基础G和物质资本量K。资源越富足自然资源部门可开采利用的资源量越多;另一方面从资本积累效应看,资源开采利用更有效。并构建简单的比例生产函数:
Q(G,K)=GK(19)
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在考虑中间资本的同一性[(15)式所示]后变为:
YM=(γL)1-αAxα=(AγL)1-αKα(20)
式(20)显示制造部门的生产函数类似新古典的索罗模型。源于制造业和资源部门的总产出或收入Y等于消费C加上资本积累K·。
Y=(AγL)1-αKα+KG=C+K· (21)
三、分 析
(一)动态均衡
接下来就引出消费、资本、劳动力供给和创新中劳动力比重的动态分析的等式。首先,确定相对于创新部门而言,制造业部门中使用劳动力的比例。比较创新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中劳动力工资和两种资产(知识A和资本K)的收益率。制造业部门和创新部门的劳动力套利确保工资相等,这样就由(11)和(18)式得出:
APA=(1-α)YM[]γL(22)
其次,确定资本K的利率水平r。从需求函数(14)式中,通过参数α和耐用品价格p得出利率。用(12)式中p、(15)式中耐用品需求和生产量x以及(9)式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替代后,得到(23)式,利率与制造部门资本产出比成比例。
r=α2YM[]K(23)
接着计算知识的收益率。中间产品制造部门厂商的利润可以通过把(12)、(14)和(15)式代入(13)式计算出来。
πi=π=α(1-α)(γL)1-αxα=α(1-α)YM[]A(24)
(24)和(16)式可以得出在平衡增长中专利价格PA和垄断利润π,(22)式变为:
r=αγL(25)
把(23)和(25)式合并,得到制造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比例γ关于制造业资本产出比的表达式:
γ=α[]LYM[]K=α[]lNYM[]K(26)
为了动态分析,需要把等式写成密集形式(Intensive Form)。(21)式左边除以有效劳动 AK,得到经济中总收入的密集形式:
=γ1-αAk^U9α+GAk^U9(27)
小写变量上加“^”表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量,=K/AL,Ak^U9=K/AL,=C/AL。
合并(20)和(23)式,替代了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可以把利率表示成关于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数量的形式。
r=α2Ak^U9α-1γ1-α(28)
从(26)式,可把制造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比例表示为:
r=(α[]lN)1[]αAk^U9α-1[]α(29)
根据(17)和(28)式,把(7)式重写成密集形式:
·[]=r-ρ-A·[]A-l·[]l=α2Ak^U9α-1γ1-α-ρ-(1-γ)lN-l·[]l(30)
随后,根据(27)式把(21)式重写成密集形式:
·[]=γ1-αAk^U9α -1+G-[]-l·[]l-(1-γ)lN(31)
这两个式子说明消费和资本动态依赖于劳动供给的动态。为了求出l·[]l,先把劳动工资水平表示成关于单位劳动资本的形式。根据(11)和(20)式,可以计算出:
w=(1-α)kαγ-αA1-α(32)
合并(8)和(32)式,得到以下式子:
(1+σ)lσc=(1-α)kαγ-αA1-α(33)
又可把(33)式写成密集形式:
(1+σ)l1+σ=(1-α)Ak^U9αγ-α(34)
这样就有(29)、(30)、(31)和(34)四个式子,可以确定、l、Ak^U9和γ的动态了。为了用于稳态特征分析,推导出反映劳动力供给l和用了γ动态的等式。
(34)式意味着l根据以下式子演变:
l·[]l=α[]1+σ·[]-1[]1+σ·[]-α[]1+σ·[](35)
从(29)式可以看出,γ根据以下式子演变:
γ·[]γ=α-1[]α·[]-1[]αl·[]l(36)
合并(35)和(36)式,可以看出l根据以下式子演变:
l·[]l=1[]σ(·[]-·[])(37)
(二)稳态
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上,资本K、消费C、产出Y和技术A以相同的比例增长,这就意味着沿着这个路径,Ak^U9、和保持不变。从(36)和(37)式中可以看出,劳动强度l和劳动投入率γ也保持不变。所以,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上,(30)和(31)式变为:
α2Ak^U9α-1SSγ1-αSS-ρ-(1-γSS)lSSN=0(38)
Ak^U9α-1SSγ1-αSS+G-SS[]Ak^U9SS-(1-γSS)lssN=0(39)
下标SS表示出每个变量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上的动态特征值。(29)和(34)式在稳态下估计,给出了劳动供给l和创新中使用的劳动力比例γ的水平:
(1+σ)l1+σSSSS=(1-α)Ak^U9SSγSS-α(40)
r=(α[]lSSN)1[]αAk^U9SSα-1[]α=(α[]N)1[]αl-1[]αSSAk^U9SSα-1[]α(41)
(38)、(39)及以上两个式子构成一个式子组,确定SS、Ak^U9SS 、lSS和γSS四个稳态水平。通过这四个式子可以得出把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联系起来的等式:
G=ρ1+α[]1+αNN[]α+1-α[]1+σl-σSS-1+α[]1+αNN2[]α(1-α)lSS(42)
(42)式右边随着劳动力供给lSS增加,严格递减,所以只有一个稳态值,并把它求出来:
dlSS[]dG=[-σ1-α[]1+σN[]αl-1-σSS-1+α[]1+αNlSS]-1(43)
这就说明随着资源丰裕程度的增加,导致在稳态下劳动强度降低。人们以消费和闲暇来替换,获得效用。不断增长的自然资源财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以较少的劳动努力换取一定的效用水平的机会。也就是说,资源丰裕增加了闲暇,减少了人为的产出。以第一个命题来阐述这个发现。
命题1:稳态下劳动供给随着自然资源基础增加而减少。
可以从(17)式中得出在稳态下知识积累率,并把稳态下知识积累率标注为xSS=(A·SS/ASS)。
xSS=(1-γSS)lSSN(44)
把(41)式分别代入(38)式、(39)式和(40)式得到:
lα-1[]αSSAk^U9SSα-1[]α(α[]N)1[]α(1+αN)-ρ-lSSN=0(45)
lα-1[]αSSAk^U9SSα-1[]α(α[]N)1[]α(1+α)+G-SS[]SS-lSSN=0(46)
SS=N(1-α)[]α(1+σ)l-σSSAk^U9SS(47)
把(47)式代入(46)得:
lα-1[]αSSAk^U9SSα-1[]α(α[]N)1-α[]α(1+α)+G-1-α[]1+σ(α[]N)-1l-σSS-lSSN=0(48)
通过(41)式和(48)式,可以推出RD部门的劳动力比例(1-γSS)。
1-γSS=1-N+ρl-1SS[]1+αN(49)
随着资源禀赋增加,(43)式已指出稳态下劳动强度将降低,所以(49)式说明就会减少RD部门的劳动力比例。所以,知识积累有两个原因导致减少。一方面,劳动力强度的降低直接阻碍了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劳动力强度的降低通过从事RD部门劳动力比例的减少间接降低了知识积累率。从(44)式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负相关。
dχSS[]dG=[(1-γSS)N+ρ[](1+αN)lSS]dlSS[]dG<0(50)
从(43)式中已经得出,dlSS[]dG<0。
所以,一个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或者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将导致较低的稳态劳动强度lSS和知识积累率χSS。经济也将在一个较低的速度下增长。
命题2:稳态知识积累率χSS随着资源基础G降低。
资源诅咒的实质是对资源产业繁荣对创新活动的抑制。快速繁荣的资源产业和滚滚而来的资源财富,抑制了创新的活力, 恶化了创新环境,扼杀了创新文化,流失了创新人才,导致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动的衰退,进而导致了区域发展衰退。大量的案例研究成果也证实,发生资源诅咒问题的国家,几乎都是过分依赖了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任由资源优势肆孽, 妨碍了创新和技术进步,掉入资源优势陷阱。
四、 实证检验
本文以区域为比较样本,采用基本方程式以下式子:
git=α+β1Ln(Yit-1)+β2NRit+β3RDit+μi+εit
其中,i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时间下标,α为常数项,μi是地区特定且不随时间变动的误差项,用于反映一些回归方程中没有考虑的因素的影响,ε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十分显着,采用全国性的综合数据,往往会掩盖这种十分显着的省际差异。如果采用横截面数据(通常选取某一年全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时间序列数据不能反映地区间的差别性的缺陷,但其只能静态地反映某一个时点的经济情况,而不能全面地动态地从一个时段上描述经济现象的变化态势。采用包括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既可以扩大样本容量,提供了更多的样本数据和信息,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被减弱,降低了估计误差,又便于考察分析不同时间跨度内自然资源效应的动态特征,为我们的分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
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为1997-2006年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比较的方便,数据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历史变更,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作为一个截面单位,这样最终的面板数据包括30个截面单位和10年的时间序列,样本观察值共计300个。主要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97到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等总量因素的约束,绝对值指标不适合作为地区间横向比较的指标,因此,回归方程中变量值均取相对值。
具体的变量解释依次为:
git:省区i在t期的人均GDP的增长率,等于本年与上年人均GDP指数之差与上年人均GDP指数的比值(1952年=100)。选择人均GDP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的绩效指标,主要是为了剔除省区大小和人口规模造成的偏差。
Ln(Yit-1):省区i在初始(t-1)时期的人均GDP自然对数值,加入这个变量的目的是为了对增长方程的转换动态加以控制。
NRit:省区i在t期的自然资源投入水平,以农林牧渔业与采掘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来表示。徐康宁、王剑[8]采用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认为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的投入水平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把它作为表征量是合理有效的。本文认为,自然资源也是一个外延边界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在这利用的是主要的自然资源,在此,定位直接作用于自然资源,取得了初级产品的阶段,包含农林牧渔业与采掘业,不包括后续的加工业。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自然资源的经济定义,本文扩展了这一做法。
RDit:研发投入,以科技三项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表示,反映技术、创新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计量软件stata8.2对上述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表1所示,根据沃尔德F检验及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每一个模型都拒绝原假设,可以得到固定效应模型(FEM)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REM)比OLS更适用。由豪斯曼检验可知,固定影响模型更好。所以计量结果应该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
由于固定模型中可能存在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产生估计偏误,所以我们应该检验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并纠正。其中组间异方差使用修正的沃尔德F检验(Modified Wald test for groupwise heteroskedasticity),自相关问题使用伍德里奇检验(Wooldridge test for autocorrelation)。原假设是同方差,原假设是没有一阶自相关,检验得知有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
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的方法进行检验,以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运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FGLS)纠正,回归结果如表
注:(1)括号内为Z回归系数Z统计量值;(2)Obs是样本观察值个数, Wald是Wald统计量,Log为模型回归的极大似然值;(3) *、**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着。
从回归结果看:(1)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省际层面得到验证,与徐康宁和王剑[8]的研究结论一致。自然资源的系数值分别为-0.0337683和-0.0343525,均通过了显着性水平为5%的显着性检验。这说明自然资源丰裕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滞后。当然不能理解为所有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经济增长都是慢的,或者说是任何时候都是慢的。(2)RD的系数为正,并通过显着性检验,研发成果和发明专利转化为生产技术,实现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3)在初始时期的人均GDP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中国经济在1997-2006年期间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收敛,反而是发散的。①
同样,我们将前文的代表创新的变量RD对资源变量NR进行回归,得出NR的系数为-0.017731(-2.24),在1%水平下显着,说明资源丰裕度与创新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资源丰裕地区产业结构依赖资源的开发,产品又以自然资源初级产品为主,
① 目前跨省区收敛性研究,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9年的数据,发现以1990年左右为界,前期存在条件收敛而后期显着发散,马栓友等(2003)对1995-2000年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进行分析,认为该时期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是差距扩大。
其技术含量低,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滞后,弱小的制造业产品仍然是以初级产品和半制成
品为主,会对当地其他具有战略分布性的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其产业结构的极不合理与薄弱的经济基础。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资源丰富型地区实际上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则缺乏类似效应[11]。
五、 结 论
本文考察了被忽略的传导机制:自然资源丰裕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可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创新者追求新的创意和设计来自于其中的利益激励。在我们的模型中,自然资源减少了创新者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这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减少了以劳动收入来支撑消费的需要,因此增加了闲暇而降低了工作的工作动力;其次,自然资源财富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在制造业和RD部门之间的配置。
经济学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来度量用于生产的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效果。索洛先驱性的研究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80%,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Jorgenson和 Yip[12]对多国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接近50%的日本产出增长以及超过40%的德国和意大利的产出增长可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尽管这一估计低于索罗发现的80%,但是基本的结论依然证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带来了经济增长。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那么经济增长理论就不应该只关注要素投入的积累,而应关注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是索罗的最初观点,也是他的信徒和批评者的观点。西蒙·库兹尼茨很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技术主导作用的自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在电力、内燃机、电子、原子能和生物等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13]大量的经济史学家也认为技术演变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突出的是Landes、Rosenberg和 Mokyr。他们通过对技术变化的仔细研究得出,不仅技术变化对于现代工业的形成不可缺少,而且技术塑造经济活动的过程在长期内发挥着作用。经济史学家促使经济学家用长期的眼光看待经济增长过程,因为新技术影响的发挥需要很长时间。
知识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产生了递增的收益,因此抵消了投入要素中宿命的边际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创新、国际贸易、收入分配、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为了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因素促进知识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什么因素提供了对知识创造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这自然地导致我们去探求研究和开发、干中学、外部性以及报酬递增等因素,同时也导致我们去考察鼓励和不鼓励知识创造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因素。
只有真正的科技创新和持续的制度创新才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积极地寻求相关的创新,并将这些创新的思路有效地付诸实践,使得自然禀赋的应有价值得到令人满意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Sachs J, Warner A.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1995,No.5398.
[2] Sachs J, Warner A. Fundamental sources of long-run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87:185-187.
[3] Sachs J, Warner A. The curse of matural resourc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45:828-839.
[4] Gylfason T. 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45:847-859.
[5] Papyrakis E, Gerlagh R.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 32:182-192.
[6] Hausman R,Rigobon R.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ource curse:theory and implications of stabilization,saving and beyond.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on Fisc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in Oil Producing Countries.2002.
[7] 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经济学家,2005(6):96-98.
[8] 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78-80.
[9] 滕春强.我国区域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资源诅咒分析[J].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6(3):59-62.
[10] 张景华.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制度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9-16.
[11] Mehlum H, Moene K, Torvik R. Predator or prey? parasitic enterpris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3,47:275-294.
[12] Kuznets S.Modern economic growth[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13] Jorgenson W, Yip E. Whatever happened to productivity growth?[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