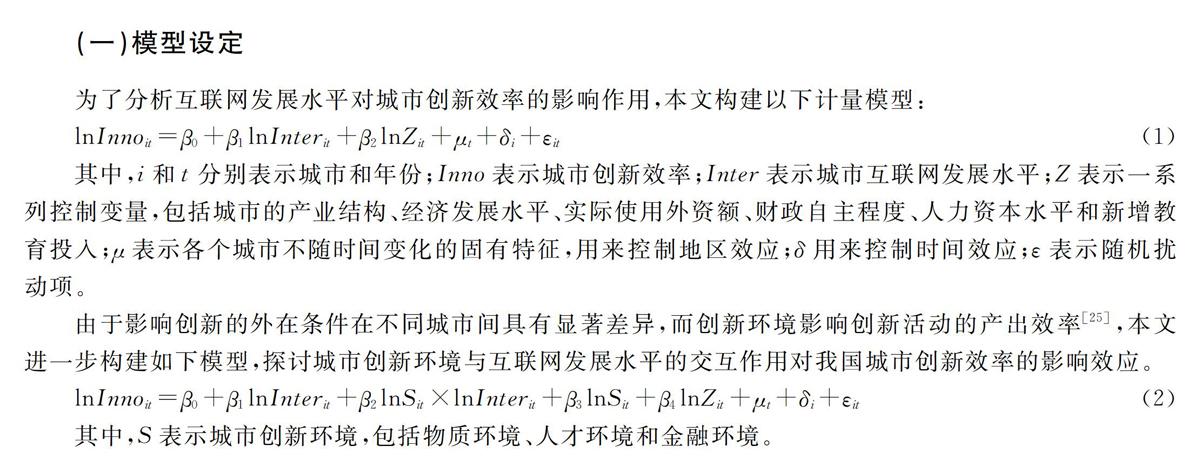喻国明 杨雅 冯莞茹 修利超
【摘要】互联网技术自诞生以来,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境况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个体赋权实现的源泉与力量。从宏观层面看,网络的信息共享、无远弗届、虚拟共在、连接一切的属性,使得个体作为网络节点的价值不断凸显,传播互动及其代表的关系联结成为新的权力来源,“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到来;从个体层面来看,网络的接触使用和赋权感知,对于人的风险偏好、决策及认知控制能力也造成了重要影响。现运用实验法聚焦网络技术赋权的个体层面权力感知,考察互联网赋权是否会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以及不同互联网赋权程度(高VS低)和不同风险偏好水平(高VS低)对于人的注意控制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影响,对网络赋权的影响提供个体层面的解释维度。研究发现,在认知控制力、注意力和执行力上,高网络赋权组的被试表现更差;而在风险偏好和决策上,高网络赋权组表现得更加谨慎保守。因此,研究认为,网络赋权确实能够为个体使用者带来权力感,且这种基于虚拟空间的权力感知要高于在现实社会的感知;感知权力越高,个人认知和行为脱序的可能性就越大,更需要通过学习机制提升人的理性责任。
【关键词】网络赋权感知;风险决策;认知控制;行为脱序;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IIV)
一、引言
“赋权”是一个跨越多个领域且不断发展的概念,起源于社会学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赋予行为。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社会生活与人的境况发生颠覆性的改变,网络逐渐成为个体赋权实现的重要源泉与力量。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网络化时代会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力”。互联网“去中心化”和“去组织化”的特性,模糊了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边界,使新的赋权形式得以产生。如果说大众媒介培育了大众的现代性,那么社交媒体则进一步消解了垄断性,增加了流动性。网络技术赋权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不仅超越和分散了传统意义上权力的限度,还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创造了新的基础结构和连接界面,甚至让两者在网络互动中重新塑造。[1]
因此,媒介的发展也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个人和群体联系的总体格局”。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并相互交融,持续不断地卷入各种领域的变化之中[2]。媒介本身也可能成为权力的主体(power of media)或者权力的中介(power though media),大众媒体技术培育了民众的现代性,而新媒体技术则进一步消解了传统传播模式的结构和通路,呈现“从家长式到兄长式,从宝塔式到扁平化,从中心—边缘到有机同步参与”的变化趋势。[3]
二、权力感知与虚拟空间的表现
网络赋权不仅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网络社会中的“大众”也产生作用。互联网时代,个体不再是工业时代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是具有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其价值和地位不断凸显,正如传播学者所言“互联网凸显出个体的异质性……形成的是多个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异质共同体,网民成为传播主体成为可能”。[4]同时互联网激活了个人资源,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机构和个人的角色不再一成不变,其权利之间的沟壑也在逐步被填平”。[5]因而,对网络赋权影响的研究不仅需要从宏观、中观层面入手,更需要从网络赋权中的个体这一微观层面切入,从而对网络赋权议题提供个体层面的解释维度。个体成为在网络中“呼风唤雨”的主角,而后真相时代又加剧了非理性和情绪感染、现代性下的困惑和异化、后现代性的解构和虚无。同时,虚拟空间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增加了个体的疏离感[6]和倦怠感[7],其与个体的执行能力水平之间呈“倒U形”关系[8],而更高强度媒体多任务者(media-multitasker)则具备更强的任务转换能力[9]和较弱的抑制控制能力[10]。
(一)权力的感知与影响
权力及其感知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权力,认为权力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任何社会的建构都离不开权力;韦伯则认为社会中的权力无处不在,并提出传统型、克里斯玛型、法理型三种权力的合法性形式;福柯认为权力有各种形态,并且“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才有意义,因为权力建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在政治传播领域,研究者们对于权力这一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权力感能够对于个体的生理水平、心理倾向、行为表现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从生理层面来看,有研究发现权力感可以提升个人体力和精力,权力感越高,个体的心率、脂肪分布等生理指标则更加正常、身体更加健康。[11]从心理倾向来看,拥有更高权力感的人,当面对其他人的痛苦时,表现出的痛苦和同情心更少[12],这也和他们更强的自主情绪调节能力有关。从行为表现上来看,凯尔纳(Keltner)认为权力越高的人在缺乏同理心的同时,表现得更加“愚蠢”(selfish)。[13]在一项有趣的实验中,他发现权力高的人在吃饼干时,会掉落更多的饼干屑在衣服上,表现得像一只“饼干怪”①(cookie monster);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权力感不同的人在合作行为[14]、道德行为[15]、主观幸福感[16]等行为取向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二)深度媒介化时代虚拟空间的网络赋权
网络技术(ICTs)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同样建构了平行虚拟空间中的权力结构,互联网赋权(E-empowerment)能力日益凸显。在深度媒介化时代,社会中的所有元素都与媒介及其底层基础设施深度联结,媒介成为重要的“模塑力”(molding force)[17]与核心的“序参量”(order parameter)。[18]媒介技术的普及,对于相对无权的个体的赋权超越以往,便利了人们接触、选择和传播信息的自主性。“那些在历史上从未被看见的个体出场,那些曾经面目模糊的个体的行动轨迹与需求偏好被洞察”。[19]
互联网赋权,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机会接触并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和传播信息与观点,以拓展现实社会中的能力。有研究者就针对互联网赋权概念进行阐述,认为赋权可以在四个阶段展开:首先是个人层面,包括个性塑造和个人技能的提升;其次是人际层面,包括社交补偿,促进跨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减少等;再次是群体层面,包括网络能促进群体成员找到彼此,增强群体的集体性,促进群体决策效率等;最后在公民身份层面,网络赋权可提升信息的可接近性,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监督及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20]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认为网络赋权会带来网络社会新的权力分层,普通个体有机会成为网络社区或网络平台具有高声量的平台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KOL)等角色,在虚拟空间的社会结构中被赋予了更高的权力,甚至“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21]
目前,学界对网络赋权的影响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互联网能够为边缘群体赋权[22],同时因其技术的双向赋权也推动了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并促进了政治自由化,使得公众从传统参与的虚假在场走向“真实在场”。[23]有研究者就曾对比了听觉障碍与听觉正常两个青少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认为可以将网络视为听觉障碍者的赋权平台。[24]网络赋权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缔造着新的不平等现象并产生新的问题。有研究者就认为网络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符号表征效果的强化和虚拟现实正发挥隐形权力,为受众不断赋权和重新赋权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平等和不平等的信息交往格局[25];另有学者指出,增权只是网络赋权中的一种可能性,在促进主体自主性获得的同时也可能使人的主体性丧失。[26]
与此同时,网络赋权也会带来更多的非理性表达,影响到舆论监督的作用,甚至出现网络暴力、网络恶搞等异化现象。[27]“社会无法给出既定的社会结构秩序,单一媒介线性的信息生产、流通过程已被取代,社会秩序基于媒介的传播实践不断被整合和延伸”。[28]所谓脱序,指的是在社会过渡状态下,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期许的抑制作用失效,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善,个体由于不适应所采取的一些偏离常态的行为。许多学者对网络赋权过程中出现的非理性表达、网络暴力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例如有学者认为很多网络舆情反转类事件中都存在认知上的“瞄定效应”。[29]然而,目前网络赋权对个体产生影响的研究多是描述性解释,有分量的定量研究较少。学者目前已经对于网络赋权角色如虚假信息的线上审核员之间是否存在旁观者效应做出讨论,认为权力感和责任感的增加,会助推人们做出某种决策行为[30],然而并没有严格区分被赋权的角色或者责任感的程度水平,而这正是影响人们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将以个体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程度的网络赋权对个体行为和认知层面的影响,为网络赋权问题提供解释水平和个体维度上的实证探索。
三、研究设计与问题提出
本研究将通过实验法,探究网络赋权对人的认知与行为层面带来的影响。研究聚焦于互联网赋权获得的权力感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其中包含著高低风险条件之下的决策行为变化,尤其在注意力水平和风险偏好两个方面的表现,从而将网络社会赋权对个体的影响拓展到更多维度,以丰富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内容。
(一)研究问题
在传统赋权研究中,大量研究表明,在个体进行决策的时候,其所拥有的权力水平会影响到个体的行为。[31]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社会经济水平低的人会更倾向于高风险的行为[32],甚至造成较高的死亡率[33],然而权力水平高低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并非如此直观。有些研究者认为高权力者更倾向于亲社会行为的选择[34];而另一些学者发现在某些情况下高权力者更倾向于做出冒风险的决策。[35]实验证明,在高收益情境下,高权力感被试的风险偏好显著高于低权力感被试[36],同时乐观主义、权力动机和权力稳定性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研究者认为乐观主义在高权力者从事冒险行为方面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37];还有学者发现,由于权力等级的稳定程度存在潜在的可变性,权力动机高的人有可能会更加谨慎,做出更保守的选择[38],而低权力者则在不稳定性越大时越愿意承担风险。[39]
综上所述,本研究设计行为实验,从个人心理层面探究网络赋权的影响,通过不同情境赋予参与者不同水平的权力,从而研究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网络赋权、风险程度对个体的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研究问题要进行考察:
问题一:互联网赋权是否会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
问题二:互联网赋权是否会影响个体在进行风险判断时的注意控制水平。
问题三:互联网赋权是否会影响个体在进行风险判断时的执行能力。
(二)实验设计
1.实验变量
研究采用2(权力类别,分为赋权组和无赋权组)×2(风险类别,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权力类别为组间变量,分为实验组(赋权组)和对照组(无赋权组);风险类别为组内变量,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
在探究权力感对个体影响的实验中,操控个体权力感的方法有很多种。以往研究采用情境回忆、角色扮演、叙述写作等多种实验材料启动被试的权力感,并被认为是有效的权力操作范式。[40]为更加直接地研究网络赋权中权力对个体的影响,研究借鉴角色扮演法,通过模拟不同形式的网络赋权情境,使实验组和对照组产生不同程度网络赋权下的权力感。因此,实验搭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平台,对于实验组进行赋权启动。
研究的因变量是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trial-to-trial intraindividual reaction time variability,IIV)。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指标可以反映个体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功能,与个体的持续注意能力和抑制控制能力都具有关联性,是反映个体认知水平、注意力的一个通用指标。[41]个体在完成一系列的认知任务时,完成每个任务的反应时间会发生一定的波动,即出现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数值较低,则代表该个体拥有更好的执行功能;而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数值较大,则代表该个体注意力越不集中[42],认知控制能力表现更差。[43]因此,研究采用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作为反映被试的注意力集中水平及认知控制功能的指标。
2.被试情况
研究在预实验之后,为达到有效的实验结果,通过G*power软件计算效应量(power analysis)得出,所需被试量为48名。实验后剔除1名无效被试后,最终有效被试为47名。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24人,7男17女,年龄=21.75±1.984岁,范围18岁至25岁);控制组(23人,8男15女,年龄=22.48±2.213岁,范围19岁至29岁)。所有参与者都是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史和家族病史,实验之前没有服用酒精、烟草或其他任何精神药物。被试在实验前都进行了中文版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和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测试,均未出现临床上明显的焦虑或抑郁症状。
3.实验程序
一是个体的赋权控制和网络权力感知。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分别使用同一部实验手机进入平台,分别接受两种实验条件的处理。实验组为高赋权组,参与者被赋予平台管理员的身份,要求进行删帖、置顶、打分、评价等行为,行使平台管理权力;而控制组为低赋权组,参与者则只能发布信息,等待管理员的评价。实验将用摄像头记录下被试的操作情况。具体流程如下:
实验组阅读下列要求并按其采取相应行动:“您好!现在您将进入一个网络社区平台,您是该社区平台的管理员,需要您对该网络社区进行管理。您可以对社区内现有的帖子和回复进行点赞、加精、删帖等操作。同时您也需要发布帖子,可以是回复他人帖子、发布新帖子,修改发布社区规定等。需要您在本社区内活动10分钟左右。”
控制组则阅读下列要求并按其采取相应行动:“您好!现在需要您回答平台管理员提出的问题,并在该平台上发布答案。平台管理员会对您的评论和回答进行评论、置顶、加精、删帖等操作,如果获得平台管理员的青睐,您可以获得额外被试费,如果被删帖,将不会拥有额外奖励。需要您在本社区内活动10分钟左右。”
随后,两组被试都会通过权力感知调查问卷测量赋权结果,该问卷改编自个人权力感知量表[44],信效度良好(Cronbach α=0.767,KMO=0.68)。题项分别为:“在刚刚的过程中,我可以对我认为优质的内容进行置顶加精等操作”;“在刚刚的过程中,我可以对我认为不符合小组要求的内容进行删帖等操作”;“在刚刚的过程中,我可以对他人发布的内容进行评判”;“在刚刚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和观点可以影响到小组内的其他人”;“在刚刚的过程中,我认为我有权力对该社区进行管理”。
不同赋权条件下,实验组即网络社群管理员角色的权力感知值(24.83±3.60)高于控制组即普通网民的权力感知值(19.61±4.23)。通过差异性检验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权力感知差异显著[t(45)=
-4.570,p=0.000,d=0.673]。可见,不同程度的互联网赋权过程对于被试的权力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是个体的非确定型决策:爱荷华博弈任务。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IGT)是一项模拟现实决策情景的实验室任务,用于测量非确定型的决策中的模糊决策,即概率未知且结果不确定的决策。博弈范式可以有效测量风险偏好的程度[45],已有研究证实,可以把百个试次以上的爱荷华博弈任务作为测量风险决策的工具。[46]
因此,在权力感操作任务之后,研究安排两组被试完成爱荷华博弈任务,通过计算个体选择得分和个体内反应时间变异性(IIV),测量个体在决策行为过程中的风险偏好和认知控制。任务程序采用E-Prime3.0编制,每个试次(trial)以500ms的注视点开始,然后呈现500—800ms随机时长的空屏。之后屏幕上呈现ABCD四个选项,要求参与者操作相应按键做出选择,其中A与B为高风险选项,即投入较大而获胜概率较小;C与D为低风险选项,即投入较小而获胜概率较大。在500—800ms随机空屏之后,呈现2000ms的反馈界面。在500ms的空屏后该试次结束,进入下一试次。每10个试次为一个组块(block),共180个试次,构成18个组块,一个组块内的10个试次随机呈现。其中A和C选项的输赢比例为5∶5,即出现损失的概率为50%;B和D选项的输赢比例为9∶1,即出现损失的概率为10%。
四、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风险偏好
本实验中共有47名被试参加,均为有效被试。每个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可以根据其每次投入数额的选择结果进行计算。具体操作过程为,计算参与者在每个组块的选择得分(选择得分=选择有利数额的次数-选择不利数额的次数)。最后得出其所有组块选择得分的平均数,即为风险偏好数据结果,得分越高则该被试在作选择时更偏向保守,得分越低则更偏向冒险。两组参与者的选择得分通过SPSS 26.0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相较之下,高赋权组更倾向于保守决策,得分(1.493±4.080)略高于低赋权组得分(0.627±3.915),两组被试之间的风险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t(45)=-0.744,p=0.461,d=0.110]。
(二)个体内反应时间变异性(IIV)
首先分别计算两组被试每个区组的平均反应时,剔除其中低于100ms(由于被试预期导致的提前反应)的数据,有效数据为91.57%(>70%)。之后计算出每个被试18个区组平均反应时的平均数和方差,方差值即为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数值(IIV),其中均值(M高赋权高风险=888.51±521.87,M高赋权低风险=801.64±483.06,M低赋权高风险=185.43±87.51,M低赋权低风险=137.68
±67.06)。
研究用SPSS26.0进行2(互联网赋权程度高VS低)×2(风险偏好水平高VS低)的两因素方差分析,其中互联网赋权为组间因素,风险偏好水平为组内因素。结果发现,互联网赋权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1,45)=50.348,p=0.001,η2P=0.708]。风险偏好的主效应不显著[F(1,45)=1.837,p=0.182,η2P=0.039],互联网赋权和风险偏好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45)=0.155,p=0.696,η2P=0.003]。分析结果显示,无论风险偏好水平高低,高赋权组的个体内反应时间变异性都要比低赋权组更大(p<0.01),而且没有出现随着风险偏好水平的增高而个体内反应时间变异性增大的情况(p>0.05)。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实验法聚焦被网络技术赋权的个体层面权力感知,通过考察互联网赋权是否会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以及不同互联网赋权程度(高VS低)和不同风险偏好水平(高VS低)对于人的注意控制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影响,对网络赋权的影响提供个体层面的解释维度。研究证实了网络赋权确实能够为个体使用者带来权力感,且这种基于虚拟空间的权力感知要高于在现实社会的感知。研究发现,在认知控制力、注意力和执行力上,高网络赋权组的被试表现更差;而在风险偏好和决策上,两组虽未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高网络赋权组的被试的确表现得更加谨慎保守。
(一)互联网赋权程度显著影响个体的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能力
在本研究中发现,互联网赋权与个体内反应时变异性(Intra-individual reaction time variability,IIV)呈现显著相关,且与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高低无关。这表明互联网赋权会对个体的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即在网络赋权过程中那些被赋予“管理员”角色的普通人,表现出了更低的注意稳定性和认知控制能力。这也和人们的经验性感觉即前文提到的“饼干怪”的假设相一致。互联网赋权程度较高的个体,表现出较差的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能力及反应抑制能力,这可能是所需的注意负荷更强,因为其在网络空间的社会结构中拥有更多的权力,需要思考和掌控更多的事务,不仅要对实验中社群关注的普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还要对虚拟社群的整体发展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正如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一个人不可能花费所有时间去了解和把握所有问题,当他关注于某一事件的时候,其他数以千计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非他能够准确判断,时间精力投向何处能够最合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长,否则违背其固有的能力,做他不胜任的工作,他只能感到迷茫”。[47]对于互联网低赋权者来说,他们只需要专注于实验环境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用对问题以外的事情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操作,因而他们具有更好的注意力、控制力和执行力。不过,现实情境下,这些浅层思考却具有高执行力的人群,倘若在网络社区中不断聚集,极有可能会呈现出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所提到的“乌合之众”的样态,“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48]因此,网络赋权程度高,可以让个体行动之前进行更多思考,有助于减少网络上无意识的狂欢和乌合之众效应的发生。
(二)互联网赋权程度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加谨慎保守的风险偏好倾向
关于研究方向,不同互联网赋权程度的两组被试,在风险偏好方面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是分析数据可以发现,高赋权组的被试任务得分高于低赋权组,表现出更加谨慎保守的倾向。这也符合“感知权力越高责任越大”的研究假设。高赋权者在网络空间中的决策行为表现得更加谨慎,能够更加理性地去看待发生的问题,“随着深度体验和参与的加深,他们越来越理性,发言、转发、评论的内容更多的经过了选择”。[49]与前文结论相关联,在实验过程中,高赋权组进行了更多的分析和思考,采取更加保守的风险决策,同时在实验中表现出较差的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能力;而低赋权组在实验过程中未对任务风险性做出过多的分析和判断,更加偏向做出冒险的决策,同时表现出较好的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能力。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对上述实验结果的解释。因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要进一步扩大网络对个体权力的赋予,让网民真正地感知到权力,给予网络空间中的个体更多行使权力的空间,让个体能够面对问题更加理性,更好地进行分析和思考,审慎地做出决策。
(三)互联网赋权的影响机制与现实空间存在差异
互联网所建构的虚拟空间中,赋权的影响机制与现实空间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互联网赋权水平下,个体风险偏好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已有关于现实中权力感知与冒险倾向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原因之一在于,在赋权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权力稳定性(power stability)因素起着重要作用,高权力者更愿意在身份稳定的情况下去冒险。[50]当前网络社会并没有与现实社会完全“打通”,即互联网社区中权力的有无与现实社会结构中权力的有无并不相同,网络赋权程度缺乏实在的权力等级、稳定性和获得感。也就是说,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目前并没有形成真实社会中的“科层制”②(bureaucracy)。关于权力体系,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更加自由,给予不同赋权程度的个体更多权力的可能性,因而更能够让个体发挥“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力量,这也是在传统社会中处于结构边缘的弱势群体,在网络上发声更容易被大众听到的原因。因此,互联网“去科层化”的空间结构让网络使用者普遍具有了获得权力的感知。相较于现实社会的无权者,即使是低网络赋权的个体也有着更强的权力感知。因此,避免虚拟空间走向僵化的“科层制”结构,社会需要对网络技术发展抱着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在合理范围内促进互联网发展,进而充分激活网络空间人的自由度。
此外,互联网“去抑制效应”(disinhibitioneffect),往往让人们在虚拟空间表现得更加坦率,同时也表现出自制力差,甚至是反规范的行为。“网络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51],如何让网络空间更有利于公共交流一直以来是众多学者思考的问题。研究发现,由于对事件进行更多的分析和思考,高网络赋权的普通人表现出较差的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能力、反应抑制能力,面对风险决策时,他们往往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而低网络赋权的普通人因其思考分析较少,表现出较好的执行力和认知控制能力,同时偏向做出更冒险的决策行为。因此,通过网络赋权,尽可能发挥自组织的力量和积极作用,使原本在去中心化和去组织化的网络环境中呈现出“乌合之众”样态的个体,能够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判断,尽可能减少无意识的群体行为,自发地进行进一步组织化,实现去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过程。随着网络赋权的范围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网络环境中的个体则更需要提高自身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信息分辨能力和对事件的分析判断能力,使自身能够具有应对信息化社会中海量数据的多维能力,降低成为“乌合之众”的可能;随着技术与社会的进步,需要持续保持和增强互联网对于个体的赋权,给予网络空间更加包容自由的发展程度,使自组织的循环和“意见的自由市场”得以实现,并由此促进网络参与者的学习与素质提升,最终实现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环境,从而让网络赋予的权力展现出应有的个体效用和社会价值。
注 释:
①也译为“大胃王”,美国著名卡通片《芝麻街》的动画人物。
②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亦称官僚制,指权力依据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
参考文献:
[1]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0.
[2]曼纽尔·卡斯特.传播力[M].汤景泰,星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4.
[3]黄梓航,王俊秀,苏展,敬一鸣,蔡华俭.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及其对心理学家的启示[J].心理科学进展,2021(12):2246-2259.
[4]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5]喻国明,李彪.互联网平台的特性、本质、价值与“越界”的社会治理[J].全球传媒学刊,2021(4):3-18.
[6]姬广绪,周大鸣.从社会到群: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J].思想战线,2017(2):53-60.
[7]Bright,L.F.,Kleiser,S.B.&Grau,S.L.Too much Facebook? an
exploratory examination of social media fatigu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5,44(3):148-155.
[8]麻雅洁,赵鑫,贺相春,任丽萍.社交媒体使用对执行功能的影响:有益还是有害?[J].心理科学进展,2022(2):406-413.
[9]Rogobete,D.A.,Ionescu,T.&Miclea,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multitasking behavior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adolescence:a replication study[J].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2020,41(5)725–753.
[10]Baumgartner,S.E.,&Wiradhany,W.Not all media multitasking is the same:The frequency of media multitasking depends on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combinations[J].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2021,Doi:10.1037/ppm0000338.
[11]Magee,J.C.&Galinsky,A.D.Social hierarchy:the self-reinforcing nature of power and statu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08,2(1):351-398.
[12]Van der Molen,M.Energetics and the reaction process:running threads through experimental psychology[J].Handbook of Perception & Action,1996(3):229-276.
[13]Keltner,D.How power makes people selfish.Video source:Fig.1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EB/OL].2006,Web site:https://www.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fig1.
[14]Wang X.,Wang M.,Sun Q.,Gao Q.,Liu Y.,Deng M.Powerful individuals behave less cooperatively in common resource dilemmas when treated unfairly[J].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19(3):177-186.
[15]Piff,P.K.,Stancato,D.M.,Coteb,S.,Mendoza-Denton,R.& Keltner,D.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J].PNAS,2012,109(11): 4086-4091.
[16]Kifer,Y.,Heller,D.,Wei,Q.,& Galinsky,A.D.(2013).The good life of the powerful:the experience of power and authenticity enhances 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ical Science,2013(3):280-288.
[17]陈昌凤.元宇宙:深度媒介化的实践[J].现代出版,2022(2):19-30.
[18]喻国明,滕文强,王希贤.分布式社会的再组织:基于传播学的观点: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中协同创新理论的实践逻辑[J].学术界,2022(7):184-191.
[19]喻国明,耿晓梦.“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12):76-91.
[20]Amichai-Hamburger,Y.,Mckenna,K.,& Tal,S.A.E-empowerment:empowerment by the internet[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08(5):1776-1789.
[21]梁颐,刘华.互联网赋权研究:进程与问题[J].东南传播,2013(4):14-17.
[22]Mehra,B.,Merkel,C.& Bishop,A.P.The internet for empowerment of minority and marginalized users[J].New Media & Society,2004(6):781-802.
[23]王亚婷,孔繁斌.信息技术何以赋权?网络平台的参与空间与政府治理创新[J].电子政务,2019(11):2-10.
[24]Barak,A.,&Sadovsky,Y.Internet use and personal empowerment of hearing-impaired adolescent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08(5):1802-1815.
[25]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J].文化学刊,2011(3):70-73.
[26]张波.新媒介赋权及其关联效应[J].重庆社会科学,2014(11):87-93.
[27]张冠文.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表达与引导[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90-95.
[28]陈龙.深度媒介化趋势下新闻传播学科再定位和再调整[J]. 社会科学战线,2022(4):7.
[29]张华.网络舆情反转现象中的“参照点效应”[J].新闻界,2016(7):28-32.
[30]Bhandari,A.,Ozanne,M.,Bazarova,N.N.&DiFranzo,D.Do you
care who flagged this post?effects of moderator visibility on
bystander behavior[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21(5):284-300.
[31]Quirin,M.,Beckenkamp,M.& Kuhl,J.Giving or taking:therole of dispositional power motivation and positive affect in profit maximization[J].Mind & Society,2009(1):109-126.
[32]Capaldi,D.M.,Stoolmiller,M.,Clark,S.,& Owen,L.D.Heterosexual risk behaviors in at-risk young men from early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prevalence,prediction,and association with STD contraction[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2(3):394-406.
[33]Marmot,M.G.,Shipley,M.J.& Rose,G.Inequalities in death-specific explanations of a general pattern?[J].Lancet,1984(8384):1003-1006.
[34]Winter,D.G.&Barenbaum,N.B.Responsibility and the power motive in women and men[J].Journal of Personality,1985(2):335-355.
[35]Lammers,J.,Galinsky,A.D.,Gordijn,E.H.&Otten,S.(2008).Illegitimacy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power on approach[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6):558-564.
[36]何琪,孙倩,刘永芳.损益情境下权力感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权力动机的调节作用[J].应用心理学,2020,26(4):340-347.
[37]Anderson,C.,& Galinsky,A.Power,Optimism,and Risk-taking[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6(4):511.
[38]Maner,J.K.,Gailliot,M.T.,Butz,D.A.&Peruche,B.M.Power,risk,and the status quo:does power promote riskier or more conservative decision making?[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7(4):451-462.
[39]Hiemer,J.,& Abele,A.E.High power=motivation? low power=situation? the impact of power,power stability and power motivation on risk-taking[J].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2(4):486-490.
[40]Rucker,D.& Galinsky,A.D.Desire to Acquire:Powerlessness and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8(35):257-267.
[41]Lu,H.,Fung,A.W.,Chan,S.S.& Lam,L. C.Disturbance of
attention network functions in Chinese healthy older adults:An intraindividual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2016(2):291-301.
[42]Van derMolen,M.Energetics and the reaction process:running threads through experimental psychology[J].Handbook of
Perception & Action,1996(3):229-276.
[43]Bielak,A.,Hultsch,D.F.,Strauss,E.,Macdonald,S.,& Hunter,M.A.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s related to cognitive change in older adults:evidence for within-person coupling[J].Psychology and Aging,2010(3):575-586.
[44]Anderson,C.,John,O.P.,& Keltner,D.(2012).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J].Journal of Personality,2012(2):313-344.
[45]Thielmann,I.,&Hilbig,B.E.Trust:an integrative review from a person-situation perspective[J].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15(3):249–277.
[46]Brand,M.,Heinze,K.,Labudda,K.,&Markowitsch,H.J.The role of strategies in deciding advantageously in ambiguous and risky situations[J].Cognitive Processing,2008(3):159-173.
[47]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3.
[48]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张艳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13.
[49]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7.
[50]Hiemer,J.,& Abele,A.E.High power=motivation?low power=situation?the impact of power,power stability and power motivation on risk-taking[J].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2(4):486-490.
[51]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2.
[喻国明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杨雅(通讯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冯莞茹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修利超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实验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