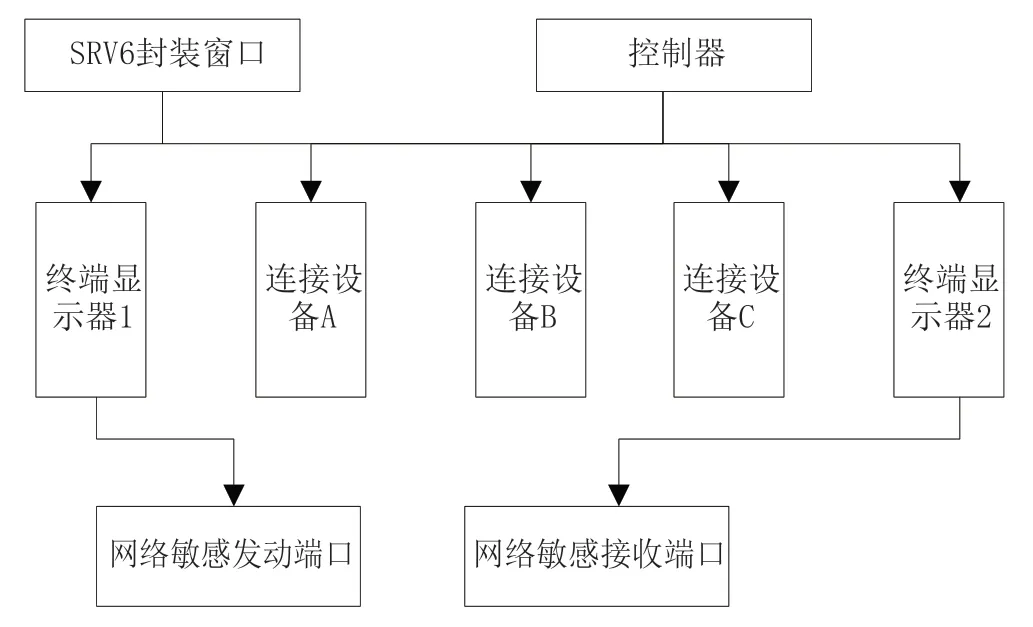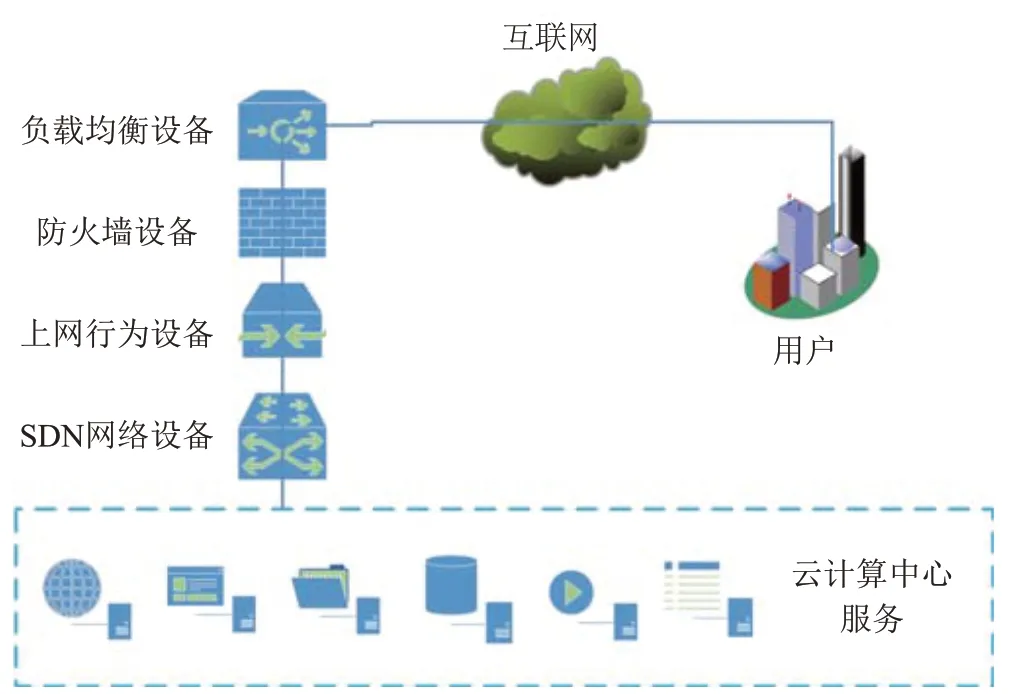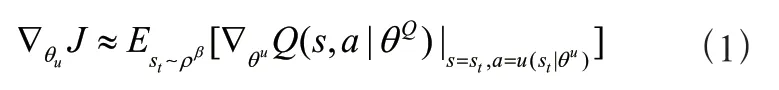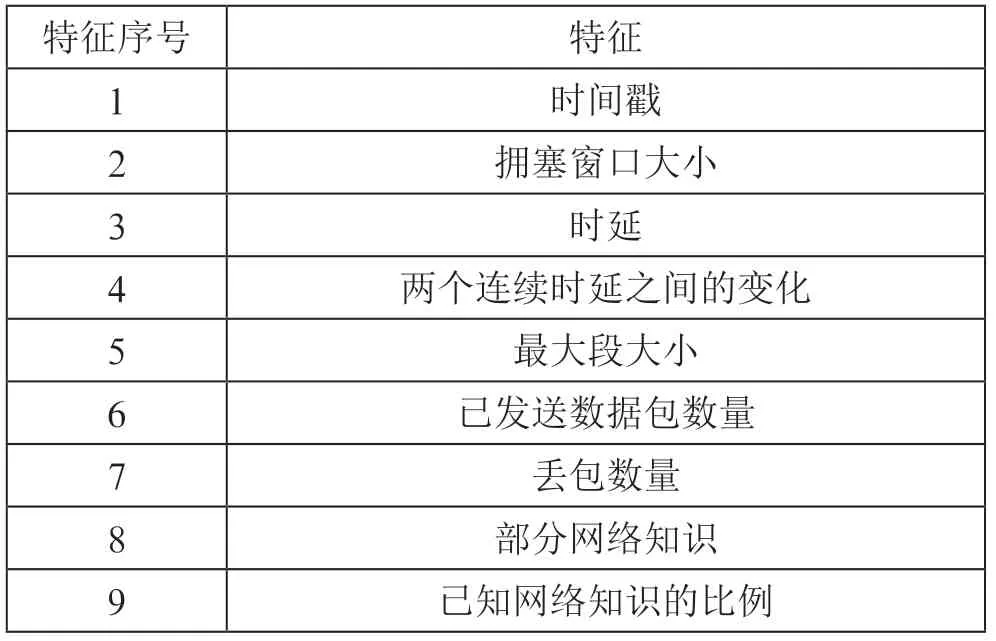端木怡雯 王丽娜 李睿
【摘要】以“Z世代”数字化生存为研究视角,探究了高校大学生数字化生存特征,具体体现为“趣缘化”社交取向与网络社群圈层化,网络舆论场重塑与公众话语权回归,个性化网络参与与意见领袖的崛起和“在场”式传播与沉浸式“狂欢”等四大方面。最后,提出要坚持弘扬主流价值观,把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导权;要优化内容供给,把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要破壁出圈融圈,把握网络舆论引导的话语权。
【关键词】融媒体;网络舆论引导;“Z世代”;大学生;数字化生存
“Z世代”(Generation Z)被学界普遍定义为1995—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即与网络时代无缝对接,已成为大学校园中的生力军,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无人不网、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媒介化生存场景[1]。网络繁荣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格局和媒介交互生态,对“Z世代”大学生的思维认知、价值塑造与行为养成均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同时为高校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带来全新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高校大学生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则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基于此,本研究拟从“Z世代”数字化生存特征入手,洞察高校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面临的挑战,并尝试探究融媒体时代高校优化大学生舆论引导机制的实践路径。
一、“Z世代”数字化生存的现实样态
(一)人以群分:“趣缘化”社交取向与网络社群圈层化
兴趣聚合是社群的基本功能,社会交往是社群的重要功能,而圈层化则充分彰显了网络社群的兴趣聚合功能,并以实现“趣缘化”社交作为社交的主要方式为旨归。在数字化媒介场域中,“Z世代”不再受制于物理世界的身份标签和社会现实环境,而是基于一致性的兴趣需求和个性偏好,同质化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寻求“志同道合”的群体而集聚于共同的虚拟场域,进而构筑认同度高、代入感强的网络圈层。圈层内部成为“Z世代”彰显个性、价值认同与情感慰藉的重要场域,形成“同类聚集”的网络社交文化景观。譬如,在bilibili,“Z世代”会因同款游戏而加入家族,因喜爱同一本小说而成为“道友”;在“Melon”、微博等平台,会为支持的偶像“买砖”“切瓜”(指为偶像歌曲打榜),进而聚集成线上追星社区等。无论是汉服热、手办潮,还是洛丽塔服饰和cosplay(扮装游戏),抑或是电竞和二次元,“Z世代”依赖于自身热衷且熟知的“部落化”圈子以获取信息、沟通情感、互动交流,在“趣缘化”的朋辈社交中形塑自我、深化认同,并建构形成前卫新潮的“Z世代”圈层文化。该圈层文化与生俱来的个性鲜明的话语模式、表达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有效迎合了Z世代“做更真实的自己”的强烈诉求,推动圈层文化呈现封闭、固化的趋势,并不断延展圈层文化内涵[2]。
(二)技术赋权:网络舆论场重塑与公众话语权回归
数字技术的赋权,为公众开辟了媒介信息自由传播、情绪观点畅快表达的广阔渠道,网络传播格局日渐呈现出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分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等特征,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信息生产机制被消解,公众被广泛赋予能够自由发声的网络话语权。网络传播模式的重大变革,打破了传统的“舆论一律”模式,引发人类的传播行为由单纯的信息传播转向权力和关系重构,由传递、获取转向分享、参与。[3]网络社会以其自由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质赢得了青年的关注和参与,尤其是社交新媒体的勃兴俨然成为青年网络社会参与和话语表达的新型阵地,网络话语场演变为公众交流信息的不设界的意见广场[4]。“Z世代”作为“网生代”,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各大网络媒介平台的浸染和影响,借助于其先天具有的“网言网语”优势,以及很强的互动、交流、表达、分享和社交的欲望[5],更容易在网络舆论场中围观集聚并引发热点,并且能够根据媒介议程设置和社会逻辑框架来阐释社会现象、表达个人观点并作出价值判断,甚至还会影响其身份认同、社会参与和个体的社会化进程。
(三)围观集聚:个性化网络参与与意见领袖的崛起
Web2.0时代社交媒体的兴起,最大限度地赋予了普通个体网络话语权,增强了其意见表达和内容生产的能力,更激发了作为普通公众的“Z世代”的参与热情。社交媒体这种自我赋权的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生在网络舆论话语结构中的被动地位。[6]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依托知乎等社会化网络社区实现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呈现着互联网依赖度强、内生性驱动力强以及圈层化符号性强等典型特征。[7]在知识生产泛化、知识传播社交化、知识共享扁平化的网络社会中,大学生只要对特别事件或特定领域拥有话语权,便可以在其中有效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解构和重构来实现信息或知识的生产,并借助社交化媒介完成信息传播,并在特定场域中形成一定的影响。
(四)可视可感:“在场”式传播与沉浸式“狂欢”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短视频不仅能够自由转发分享,还能够实现实时评论,其场景营造和展示手段也更为多元立体,实现了“多中心”的实时互动和资源共享,成为广受“Z世代”欢迎的资讯获取、娱乐社交和意见表达的重要渠道。沉浸传播通过“感官共振”与“形象还原”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在场参与”的沉浸式体验,彰显了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价值。[8]在线直播在全社会风靡并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网络社群形成热潮,更成为大学生生活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向互动、共同在场、深度参与、情绪共振的直播社交模式给“Z世代”营造了直观的视觉冲击力和身临其境般的沉浸式体验,娱乐、社交和求知成为其收看网络直播的主要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Z世代”网络社交的参与感和融入感。[9]
二、“Z世代”数字化生存视域下高校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的现实挑战
(一)网络不良社会思潮蔓延,削弱高校网络舆论引导效果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非主流价值观在网络中快速传播,网络生态庞杂丛生,非主流价值观呈现渗透倾向,影响着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与传播。随着商业资本的涌入、网络技术的支持和公众焦虑情绪的宣泄,戏谑、恶搞、审丑、摆烂等泛娱乐化倾向逐渐抬头,并逐步演化为一种社会思潮,推动着公众逐步进入了波兹曼提出的“娱乐至死”状态。加之网络媒介特别是短视频媒介的迅速兴起,泛娱乐化作为娱乐的“异化”进阶,跻身国内十大社会思潮。“Z世代”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受网络社会多元思潮影响,其身心容易呈现出相对矛盾且不平衡的状态。长期以来,高校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弘扬主流价值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大学生往往能够树立正确清晰的价值取向。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也随之在网络舆论场蔓延。“Z世代”正处于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不良思潮的传播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的重要变量。此外,自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主流媒体的垄断地位,作为 “鲜明旗帜”和“绝对权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逐渐被消解甚至旁落,高校主流价值引导正遭受严重冲击。
(二)圈群文化建构“信息茧房”,圈层壁垒阻碍主流价值传播
因共同的兴趣爱好、风格志趣和价值立场等而集聚形成的圈层化的网络社群,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往往能够逐层过滤、屏蔽掉与圈群内部不一致的信息、观点和价值观,集体无意识地构建内容局限、渠道封闭的认知环境会逐步形成“信息茧房”。圈层内部的青年基于意见气候感知的自我判断与观点选择,如有某些意见、立场的偏向,他们在集体商议后会进一步强化既有的群体认同,坚持向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导致群体极化现象。这种群体极化思维导致圈层之间形成对冲、区隔和分裂,忽视、抵制甚至排斥圈外群体的不同意见,进而形成具有偏好度极强且难以融入的圈层文化。圈群里的青年人将网络空间作为其获取影响力、存在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来源之一,甚至会在网络平台表达乃至宣泄自己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极端情绪和消极态度。在网络话语场“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圈群中的“意见领袖”能够通过重复、感染、强化等方式来引导圈群的舆论导向和个体信息选择。网络圈群的高进入壁垒,给高校破壁入圈带来极大阻碍。如若主流价值与“圈群”成员日常传播和接受的主流话语和信息内容有差异,便极易导致主流价值被自动忽视或屏蔽。高校在“圈群”中网络阵地是缺失的,舆论宣传队伍是缺位的,主流话语是失声的。[10]
(三)现实网络形象分化,大学生的“双面人格”难以把握
“Z世代”的网络形象与现实形象显著分化,在真实社会与虚拟世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呈现出“社会人”与“虚拟人”的双面性特征。作为“社会双面人”,“Z世代”能够在网络场域建构“另一个我”,其往往在网络连接和断掉的瞬间切换着不一样的面具,且他们在不同的媒介社交平台亦表现出异质性的参与特征。譬如,在微信朋友圈只发布寥寥数条的青年,可能会在微博平台大量发帖;在QQ、微信、微博、小红书等APP拥有大量粉丝的青年,现实中可能没有几个可以倾诉的朋友。在如今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场景中,积极的网络参与和媒介表达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自由社交的内在需求和空虚迷茫的外在释放。相较于实际人格,“Z世代”的网络人格更加真实地展现了“Z世代”渴望博取关注的存在感和主导舆论走向的满足感。因此,仅仅研究现实中的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行为表现仍具有局限性,更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精准地捕捉网络舆论引导对象个性化的社交特征与表达特点,从而有效增强舆论引导效果。
(四)信息获取方式碎片化,排斥精深思维引发供给与需求失焦
网络媒介的蓬勃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快速革新,颠覆性地形塑着公众的信息获取习惯和媒介接触模式。在“人人皆媒”的时代,公众借助于技术赋予的网络话语权,在网络公共空间自由地进行信息的加工、生产、发布和传播,网络媒介信息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碎片化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典型特征。同样,“Z世代”也容易被碎片化的媒介信息裹挟和左右,甚至自身也是碎片化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沉迷于浅表速览所带来的即时刺激和便利欢愉,久而久之形成了“快餐式”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容易将碎片化的浅层速览误认为是系统性的深度思考,陷入碎片信息的浅表化认知困境而排斥精深思维,甚至呈现出机械围观、懒于思考的畸形样态。然而,传统的高校舆论引导所供给的正向叙事往往具有思想深度,风格也更为严肃客观,这就导致大学生对舆论话题的思考容易“蜻蜓点水”,较少作深层次、本质性的探究,有的甚至忽视挖掘事实真相和底层意蕴,进而陷入人云亦云的认知处境,这对融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挑战。
三、高校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的路径探析
首先,高校要坚持培根铸魂,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启智润心的作用,从党史学习教育、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鲜活的“大思政课”教材中挖掘舆论引导的生动素材,以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赋能媒介场域,把正能量、高质量、有分量的主流文化融入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
其次,高校要坚持示范引领,积极培养青年“意见领袖”。组建一支媒介素养好、媒介技术强的融媒体学生骨干队伍,有效打造“自带流量”的学生“意见领袖”,引领其成为学校沟通师生的桥梁。
再次,培育网络媒介素养,引导大学生理性发声。引导他们进行逻辑缜密、严肃认真的思考,有效区分理性表达与情绪宣泄的本质性差异,准确把握网络舆论背后的立场观点,引领其成为倡导主流价值的主力军。
最后,高校要引导青年突破圈层对冲思维。积极引领大学生深刻认识到圈层中也有美好、正向的一面,而不应该是与“他者”隔绝对立的桎梏和枷锁,圈层边界的打破也不意味着丧失个性、独立性和群体认同,真正优秀的圈层文化应该是有“圈”无“壁”,能够实现圈层之间的良性交互。
参考文献:
[1]钟宇慧.零零后的“长大”:教化与内化互构的典型媒介形象呈现[J].中国青年研究,2021(3):5-12.
[2]王肖,赵彦明.“Z世代”大学生媒介化生存的审视与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22(3):90-95.
[3]葛自发,王保华.从博弈走向共鸣: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治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8):140-144.
[4]邓鹏,陈树文.网络话语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9):103-107.
[5]高菲.Z世代的短视频消费特征分析[J].新闻爱好者,2020(5):40-42.
[6]布超.社交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参与的新动向及引导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18(6):84-87.
[7]李济沅,孙超.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研究:基于1159名在校大学生的实证分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03):64-74.
[8]李蕾.新传播生态下主流媒体传播力构建路径探析:以中央级主流媒体二十大融合报道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3(1):30-32.
[9]乐晓蓉.大学生参与网络直播的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18(2):76-80.
[10]叶荔辉.高校“网络圈群”舆论引导的困境及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18(1):135-138.
作者简介:端木怡雯,同济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宣传处处长,副研究员(上海 200092);王丽娜,同济大学宣传处理论与舆情科副科长,讲师(上海 200092);李睿,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上海 200092)。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