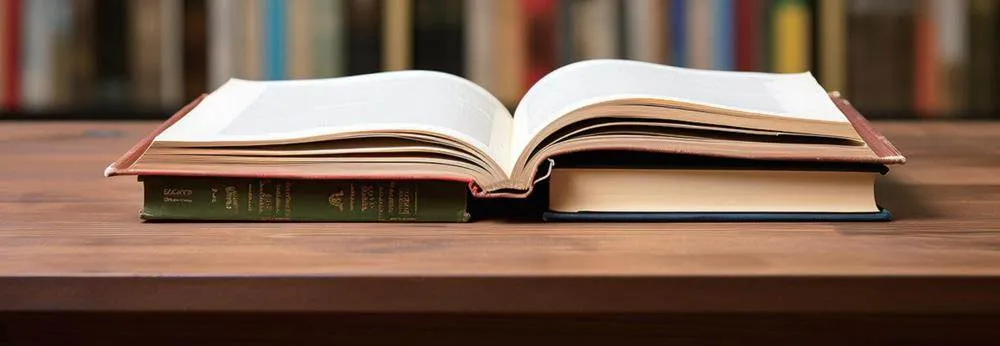摘 要:本文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旨在开拓家庭微观领域的研究边界。鉴于农村消费供给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构建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经过回归分析,深入探究其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家庭消费结构,但对农村家庭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进一步通过对样本分组回归及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改善消费结构方面存在数字鸿沟,这会导致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在消费结构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同时,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优化消费结构,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增加相关农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产品的供给;坚持加强农村教育建设,以充分发挥教育水平提升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农村消费结构;数字鸿沟;主成分分析;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35;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a)--05
1 引言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移动支付与农村电商兴起,在改善消费环境、增加收入、促进借贷便利等方面大有作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消费水平提升有利于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同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0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城市消费水平(范剑平,2000),并处于低端消费结构,以维持温饱的生存型消费为主(刘玉玲,2002)。进入21世纪后,农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基础型消费占比越来越少,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李劲松和金莲,2020)。然而,农村消费仍同城市存在差距,直到数字经济崛起,数字普惠金融带来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改善农民消费结构,但是对城乡消费结构差距的作用效果仍不明晰。
当前正处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数字经济正以一种非常迅猛的发展方式改变着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活力,是否存在城乡数字差距,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普惠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普惠金融微观层面研究引入农村消费研究领域,拓展数字经济在农村消费领域的研究边际,从家庭微观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建立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及组间系数检验评价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与城市进行对照。鉴于城乡之间存在数字差距的事实,建议解决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城乡差距问题,通过提高农村商品供给质量、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等举措来缩小城乡数字普惠金融差距,进而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城乡均衡发展。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衍生出的新事物,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并借鉴G20峰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将“以负责任、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为关键,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正规金融服务行动”定义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消费的有益作用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它能通过减少支付成本,显著刺激消费(Agarwal, Set al,2020),还可优化城市和乡村的消费结构(焦晋鹏和李纯昊,2024)。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改善是不平衡的,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比较有限(谭思进和陶士贵,2024)。当前,学者在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农村消费结构上达成共识,但对其是否缩小城乡消费结构差距存在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认同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来看,它以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这与弱势群体追求更高物质水平的公平感和获得感内在一致,所以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实际中,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信贷可得性、客户金融能力,还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靠数字化工具实现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提升,为缩小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提供了现实支持(王奕霏等,2023)。但是,部分学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与这一观点相反,比如在岳喜优和陈桂生(2022)的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分组中对农民消费升级存在负向作用;黄漫宇和窦雪萌(2022)的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增益是不均衡的,导致城乡数字差距的出现,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Ozili(2020)也指出,数字金融会使经济弱势群体面临风险,对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提出了质疑。
农村长久受制于较差的经济环境、收入差距、不良的未来预期、沉重的经济负担、流动性限制、不合理的产品结构等因素(胡宝娣和梅洪常,2005;王珊珊和王德勇,2005;万广华等,2001),导致消费水平较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流动性缺乏,并提高农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刘彤彤和吴福象,2020),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和更丰富的就业渠道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张勋等,2019),但是对于农村消费品供给结构的影响仍然有限。本文对山东日照市岚山区、寿光市羊口镇及河北衡水故城县等地的农村进行调研,农村产品丰富程度远低于城市。大部分农村地区缺乏儿童素质培养机构,电影院和KTV等娱乐场所也很少见,诸如瑜伽、健身和舞蹈这类面对成人的兴趣拓展课程更是不存在,且村民对这类文艺消费品兴趣较低,即便数字普惠金融可提高农民收入,并优化支付环境,但受制于消费品供给结构和观念认知,消费结构难以有效改善。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改善消费结构,并进一步分析这种改善效果是否存在城乡差异。考虑到类似研究使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Li,J.et al,2020),存在统计口径问题,因此本文对研究方法有所优化,借鉴尹志超等(2019)编制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方法,将家庭微观指数引入农村消费结构领域进行研究。
3 指标构建
3.1 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编制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调查数据质量高,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43个区县、1360个村(居)委会,最终搜集34643户家庭、107008个家庭成员的信息,该数据具有全国及省级代表性(甘犁等,2013)。
指数区间在0~100,越接近1,则代表该家庭数字金融使用程度越高。由表1可知,全部样本的数据特征为:商业保险普及率较低,仅12.6%,仅有11%的家庭申请获得正规贷款,家庭平均持有2.28张银行卡,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家庭达到50.88%,持有信用卡的比例为16.24%。
3.2 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所使用的变量(Khera, P.,Ng,S.,Ogawa,S.,amp; Sahay,R,2021),按照尹志超(2020)设定的五个维度,从银行账户、正规贷款、商业保险、信用卡和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情况这五方面入手,选择问卷中的相关数据构建指数,并对五个因子进行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打分,获得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本文对五个因子进行Bartlett检验,在0.05显著性水平上p值显著;在KMO检验中,KMO=0.700,高于0.5,故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计算得到各成分的特征值如表2所示。
依据表2结果,特征值超过1的仅有一个因子,该因子累计解释力度为37.19%。因此,可通过主成分分析计算得到每个家庭的得分f,将该评分标准化至区间1~100,记录为每个家庭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汇报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城乡家庭数字金融水平差距较大,均值相差两个单位。虽然农村有个别家庭拥有较高的数字金融水平,但是整体数字金融水平落后于城市。
4 实证分析
4.1 建立回归模型
以往研究已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高消费结构(Feng,G.,amp; Zhang,M;2022)。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建立基本回归模型(1)如下:
Leveli=β0+β1*Fini+Controli+μi, i=1…n(1)
其中,i代表每个家庭。
再分别对农村家庭样本和城市家庭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并进行组间系数的比较。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金融对于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因为城市组和农村组在相同的宏观经济社会背景下,两组之间的干扰项可能相关,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城市组和农村组的模型简写如下:
城市组:Leveli1=β01+β11*Fini+βk1*control+μ1i,i=1…n, k=2…5
农村组:Leveli2=β02+β12*Fini+βk2*control+μ2i,i=1…n, k=2…5
其中,i代表每个家庭;k代表每个控制变量。
若假设corr(μ1i,μ2i)=0,则可使用OLS分组进行回归估计,但是本文假设干扰项存在不同分布,且可能相关,因此采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SUR的检验进行分组系数比较(连玉君,2017)。
回归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前文计算得到的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消费结构水平(cons_level)),根据已有研究,可以使用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在所有消费中的占比作为消费结构(Hu,D.等,2023),本文以该比例作为消费结构,并将该变量规范化到0~100。
出于以下考虑,本文选择家庭总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胡宝娣和梅洪常(2005)认为,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农村居民内部消费差异扩大。贾小玫和焦阳(2016)认为,人口结构对消费结构有影响,更高的少年抚养率会降低消费结构,而更高的老年抚养率会提高消费结构。借鉴陈战波等(2019)的研究,考虑教育水平和家庭性别结构两类社会人口观察变量的影响,本文引入家庭总收入(total_income)、年龄水平(age)、家庭教育水平(education)、家庭性别结构(gender)作为控制变量(control)。其中,家庭总收入(total_income)使用项目组自行汇总生成的家庭层面变量;年龄水平(age)取家庭成员的年龄均值;家庭教育水平(education)取家庭成员的教育均值,教育水平从低到高编号为1~9,分别代表:1为没上过学;2为小学;3为初中;4为高中;5为中专/职高;6为大专/高职;7为大学本科;8为硕士研究生;9为博士研究生。另外,家庭性别结构(gender)取家庭成员性别虚变量的均值,男=1,女=0。由于问卷未收集16岁以下受访户的教育水平,缺失值被剔除,故只计算家庭16岁以上成员的教育水平(表4)。
4.2 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Stata执行上述检验,检验步骤为:(1)分别对城市组和农村组进行OLS估计;(2)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相关检验及关键步骤结果如下:
首先,分别对两个组进行OLS估计,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该回归方程整体是显著的,可以解释城乡两组的消费结构变化。其中,对于城市组,数字金融显著提高消费结构;对于农村组,该系数并不显著,无法验证本文假设H1。观察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得到收入提高对城市组的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但是会抑制农村消费结构的提高。无论是对于城市组还是农村组,教育水平提升都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而年龄增加会显著抑制消费水平提升,且控制变量性别的系数显示男性成员增多也会抑制消费水平提升。
其次,通过分组系数回归差异检验,如表6所示,可以证明城乡两组的所有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后续可以将两组系数进行比较。
最后,根据表6可以验证本文假设H2,数字金融对消费结构的提振存在城乡差异,且城市组得到的益处远大于农村组。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收入、年龄和性别的效果都存在城乡差异,会使城市消费结构提高快于农村。唯一不同的是教育一项,虽然存在城乡差异,但是会使农村消费结构提高多于城市。
4.3 分组检验
按照城市发展水平,本文将样本分为“一线/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分组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初步估计系数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按照所属几线城市对样本进行分类后,所有回归数字金融系数均显著,可以证明假设H1,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家庭的消费结构。在前述报告中,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样本之间差异过大,整体回归时便不显著。收入系数的显著性在一线城市组中发生变化,该组别收入提高也可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提高。年龄、性别和教育的结论未发生改变,具有稳定性。
对组间系数差异显著性进行检测,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知,一线城市除了性别不再具有组间差异,其他系数均显著有差异;二线城市的教育、性别均不具备组间系数差异;三线城市全部系数都具有组间差异。在三组不同城市片区检验中,数字金融存在城乡差异的稳定性得到证实,更有力地证明假设H2,数字金融存在城乡差异,且这种城乡差异无一例外,使得城市消费结构提高多于农村。在具有组间系数差异的收入、年龄和性别上,仍然保持城乡差异,且对城市家庭消费结构提高多于农村。教育在二线城市组别不具有组间系数差异,在一线和三线城市组别具有差异,且这种城乡差异有利于农村,使得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提高多于城市。
5 结论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无明显作用,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中数字鸿沟的存在。经过分组检验,进一步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存在城乡差异,对城市消费结构的影响力度远大于农村。
本文分一、二、三线城市检验得到的结果,虽然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农村家庭优化消费结构,但是也显著存在城乡差异。由于城市消费结构提高远多于农村,消费结构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农村家庭正逐渐被边缘化,调研显示,即使数字普惠金融让农村家庭的消费变得更为便捷,但由于农村消费品的匮乏,仅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也无法提升。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还发现另一结论:在控制变量中,家庭受教育程度不仅显著提高农村消费结构,还能显著缩小城乡消费结构差距,且在分组回归中具有稳定性。这说明在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积极作用时,为了兼顾城乡发展的公平协调,应注重农村人口的教育改善。具有更高水平的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村家庭选择结构更优化的消费方式,进而缩小城乡消费结构差距。
针对数字金融在提高家庭消费结构上存在的城乡差距,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增加农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产品供给。借助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特色化农村文旅产业提供信贷支持,刺激乡村文旅消费市场发展,增加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农业文化的文旅产品供给。另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可对农村养老体系建设提供个性化服务,丰富农村养老产品供给,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周华敏等,2024)。
(2)坚持加强农村教育建设。保障和巩固农村基础教育建设,鼓励农村家庭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推动农村受教育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教育开拓眼界,改善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实现消费结构的提高。
陈战波,黄文己,郝雄磊.移动支付对中国农村消费影响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5):123-141.
董志勇,黄迈.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J].经济科学,2010(5):72-79.
范剑平.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J].宏观经济研究,2000(6):32-36+50.
甘犁,尹志超,贾男,等.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4):1-14.
胡宝娣,梅洪常.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差异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1):75-79.
黄漫宇,窦雪萌.城乡数字鸿沟会阻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9):47-64.
贾小玫,焦阳.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6,32(2):29-34.
焦晋鹏,李纯昊.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理论机制、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J].商业经济研究,2024(4):184-188.
李劲松,金莲.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趋势与区域特征[J].商业经济研究,2020,(12):134-137.
连玉君,廖俊平.如何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7,35(06):97-109.DOI:10.19327/j.cnki.zuaxb.1007-9734.2017.06.010.
刘彤彤,吴福象.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互联网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115-125.
刘玉玲.我国农民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2(6):53-56.
谭思进,陶士贵.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影响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4,40(4):152-156.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94.
王珊珊,王德勇.浅析农民消费结构变化[J].商业研究,2005(11):144-146.
王奕霏,杨卫东,王海南.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理论逻辑和优化路径[J].农村经济,2023(8):98-105.
商海岩,孙云涵,赵培坊.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农村消费升级[J].农村金融研究,2021(10):37-46.
尹志超,彭嫦燕,里昂安吉拉.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J].管理世界,2019,35(2):74-87.
尹志超,张栋浩.金融普惠、家庭贫困及脆弱性[J].经济学(季刊),2020,20(5):153-172.
岳喜优,陈桂生.财政支农、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J].中国流通经济,2022,36(9):60-70.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8):71-86.
周华敏,方冬莉,李国英.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容增量的机理与措施完善[J].农业经济,2024(5):129-131.
祝仲坤.互联网技能会带来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吗: 基于C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20,37(9):68-81.
S. Agarwal, W. Qian, Y. Ren, H. Tsai and B. Yeung, The Real Impact of FinTech: Evidence from Mobile Payment Technology[J]. Productivity.2020
G. Feng, and M. Zhang, A Literature Review on Digital Finance,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2022, 11(4).
D. Hu, C. Zhai, and S. Zhao. Does digital finance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J]. Economic Modelling, 2023,125: 106-377.
Khera, P., Ng, S., Ogawa, S., Measuring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A new index[J].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22,17(2):" 213-230.
J. Li, Y. Wu, and J. Xiao.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2020,86:317-326.
P. K. Ozili. Contesting digital finance for the poor[J]. Digital Policy,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2020, 22(2):135-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