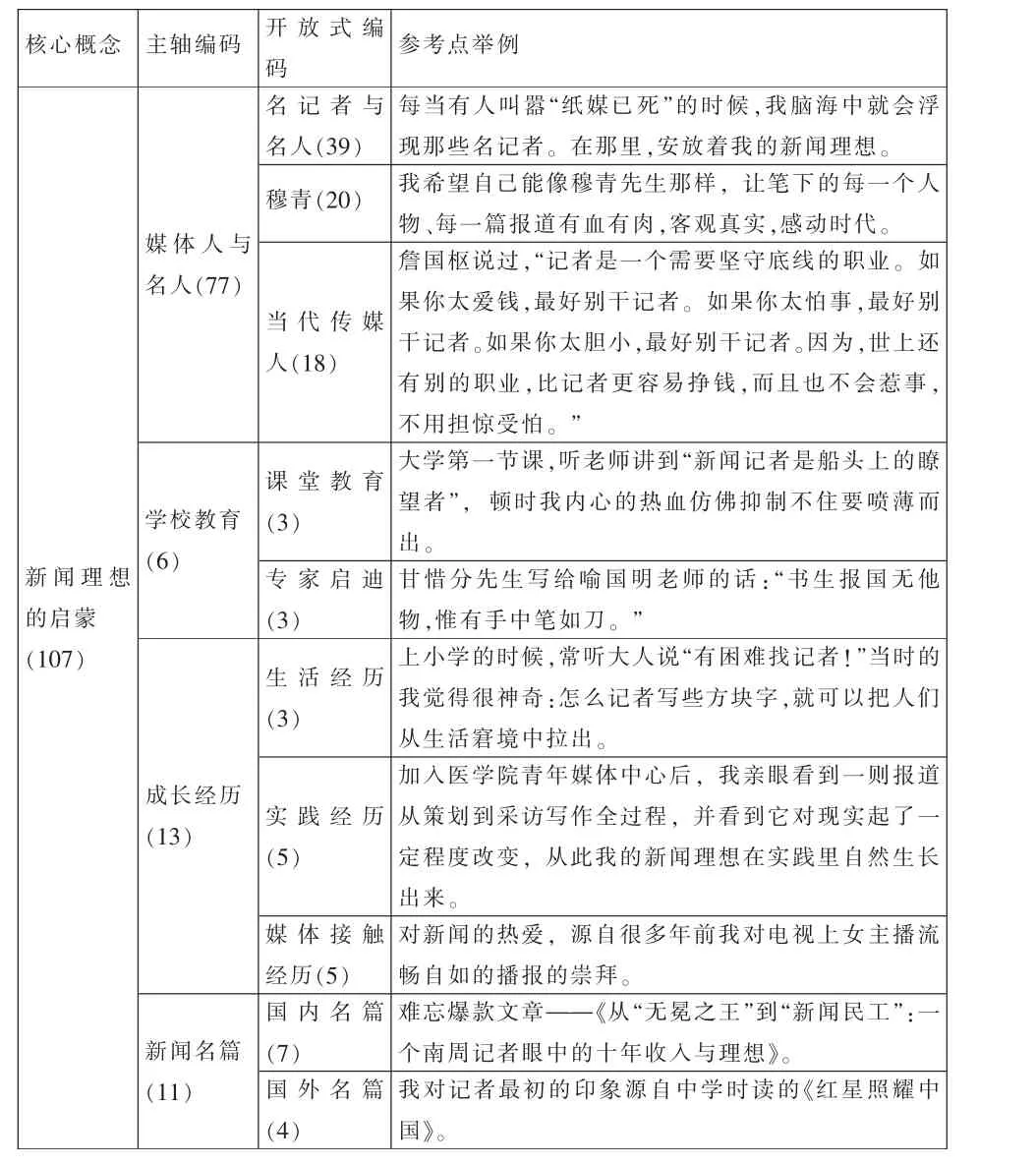马强 张辰昊 苏小龙
【摘要】新媒体时代基于自媒体的“公众新闻”兴起,是新闻业媒介化的重要体现,它具有个体情感参与的个人导向生产理念。公众新闻采用的是一种以自媒体为节点的去中心化传播,议程设置转向民众议程,通过社交媒体达到了高交互性,最后根据公众新闻在生产和传播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规范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公众新闻;传播
我国的移动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高,5G技术在国际上拥有领先地位,是全球首批提供5G服务的国家之一。“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已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达74.4%。”[1]新兴媒介技术对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媒体时代典型的标志便是“自媒体”应运而生,非新闻工作者能够在信息平台发布“新闻”,技术变革背景下产生的“公众新闻”改变了新闻业的生态与结构布局。
一、公众新闻的生产理念
公众新闻基于个体的内容生产,不同于传统媒体机构对专业新闻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传播。“普通民众在自媒体上发表亲历或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公众已经成为新闻生产者,这种由公众而非专业新闻机构进行的新闻内容生产是公众新闻生产”。[2]
(一)新闻业的媒介化
新型媒介技术的应用与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需求让公众新闻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参与新闻的生产源头,实现个体自我对“公民社会”的构建并重新塑造新闻的内核。当前的媒介环境下,公众能够快捷地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博客、论坛等平台制作文图或视频类新闻内容,平台对信息进行筛查、审核、推送,自媒体成为大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比如《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学术造假的新闻事件便是经过知乎、微博等网络平台的热心群众(非新闻工作者)曝光,并迅速引发社会热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新闻的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各种网络平台纷纷推送一些由普通人制作、发布的新闻信息,扩大了信息源,让大众及时全面地了解疫情相关信息。
公众新闻充分体现了新闻业的媒介化,“艾斯克·卡默(Aske·Kammer)指出,新闻业的媒介化(The mediatization of journalism)是新闻业被媒介系统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如经济压力、技术变迁等)所中介的过程”。[3]普通大众作为公众新闻的生产者考虑的是自媒体的媒介逻辑,而非专业新闻机构工作者的职业规范。艾斯克·卡默从媒介化角度出发,预测新闻业的发展趋势之一便是受众参与新闻生产,“里斯托·库内利乌斯(Risto Kunelius)和埃萨·雷尤纳宁(Esa Reunanen)强调新闻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和更易于受到公众注意力的影响”。[4]新媒体时代大众的新闻注意力被传统新闻机构及各类型自媒体、社交媒体所分解,当前的媒介生态环境是一个多元竞争、多元融合、多元并存的结构,新闻生产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新闻机构及其所涉及的社会领域,而是基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来重构新闻业的布局,公众新闻是基于自媒体逻辑生成的一种新的新闻样态。
(二)情感参与的个人导向
公众新闻是一种“自我主导”式的“参与式新闻”,本质来说是一种个体的信息分享行为,参与和分享欲望一直存在于大众的社会生活中,新媒体提供了数字化互联途径,构建了新型的社会交互网络。“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5]
麦克卢汉将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公众新闻是个人主导的媒介实践活动。这与职业新闻记者的新闻实践活动有着根本性不同,新闻从业者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进入工作岗位。比如记者会根据事件的新闻价值来判断是否对其进行报道,“新闻价值的要素包括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真实性和趣味性”。[6]公众是不会从专业的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价值判定的,普通个体决定发布一条信息的理由仅仅是自己的直接体验。
公众新闻的生产者是个性化特征明显的个体,他们并不会进行新闻的挖掘和探究,没有探寻真相的强烈动机和责任感,信息采集往往是自己的亲历事件或者所处社交群中的信息,新闻制作和发布也缺少专业的知识技能,更多地使用自己的见解,主观情感明显投映在客观事件上,公众新闻的表述通常是一种情感化、非正式的。
比如2021年6月3日“@大米Video”的博主发布的一条“男子抱小孩找妈妈被当成人贩子:被误会也要帮”的视频信息引发热议,并被各大日报公众号转发评论。博主的这条信息使用手机拍摄,并配用监控画面。内容呈现过程中明确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对男子的“爱心”给予了高度赞扬。情感参与凝聚出“情感共同体”,“被当成人贩子也要帮忙”是视频所表达的情感诉求,该新闻消息的制作者具有高度的“当事人情感认同”,该新闻的受众使用点赞、评论、转发、分享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认同,共情效应促成了舆论发酵。
二、“后真相”时代的公众新闻传播
《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解释是“相对于事实,人们的态度更容易受情绪影响,事实不敌情绪,因此世界步入了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7]即便是传统的新闻机构也无法绕开主观性,新闻真相与主观情绪并非完全对立,后真相体现出的是对事实真相的相对认识观。
(一)自媒体的去中心化传播
媒介技术的革新促使自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信息资源的垄断,与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辐射式传播方式不同,新媒体采用的是节点互联的信息共享模式。“去中心化的特点是多节点、高度自治、自由链接、弱控制性”。[8]分布式网络结构中用户之间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自主性,信息之间虽然有着高强度的关联性,但是自媒体基本是自治状态,不由一个控制枢纽掌控。
每个自媒体都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依照相对自由的规则来进行信息的传播行为。移动互联网串联起了规模庞大的网民,在遵守法律规范的框架之下可以进行自由、平等的表达,摆脱了传统新闻传播模式的媒体机构中心制。节点内容凭借其传播影响可以形成小的圈层传播中心,甚至发展成更大的中心。在网络传播结构中,任一节点都有成为阶段性中心的可能,自媒体的技术准入门槛低,任何大众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主体,最大范围囊括新闻信息源头,特别是当事人和亲历者。
去中心化并不是没有中心,虽然自媒体的信息是分散的,但是平台能够汇聚注意力,形成新的关注中心。比如每天的“热搜”“头条”便是大众的注意力中心。现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接收尽可能重要的信息,媒体平台的智能化推送依据受众的兴趣中心来分发信息,同时会按照转发量、评论量、点播量、点赞量等参数来筛选“头条”信息,将分散于媒介关系网中的小中心串联成一个个更大的中心,形成“泛中心”化的传播格局。
(二)议程设置转向民众议程
从议程设置的理论来看,在传统的新闻传播结构中媒体机构是议程设置主体,媒体机构按照新闻的标准工作流程来筛选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并进行加工制作,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呈现给受众。大众从接收到的新闻信息中选择设置议程,而没有被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自然不会成为大众的议题选项。新媒体时代自媒体兴起,公众新闻的议题选择来自于公众,议程设置转向民众议程。公众新闻的内容多来自传播主体自己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活动。
作为公众新闻的传播者,发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自身经历和社交群体,从自身感受出发来判定其重要与否。在新闻编辑方面,公众作为非职业人士,往往以自己的意见、情感、理解来对事件做出评论,多是个性化主张,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毕竟他们没有官方新闻的严肃、客观、公正等规矩束缚。
比如抖音平台中一条“女外卖员途中停车在路边喂孩子”短视频2021年6月3日发布,短短3个小时内就获得了2.5万的点赞量。视频中的女外卖员信息不详,事件的前因后果也不做介绍,只有一名穿着外卖员服装的女性在路边喂孩子。这条不全面的新闻信息却迅速引发了热议,类似“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感恩父母”“为你的坚强点赞”“生活不易”等评语充斥评论区。
(三)“可供性”理论视角下的交互传播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是节点网络结构,节点之间可以自由地互动交流,公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具有接受者和传播者双重角色身份。公众新闻的生产同样是普通个体以民众为主体开展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个体不再只是一名新闻信息的接收者、旁观者。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双向流动,但是这种交互关系是不对等的,关键便在于传统媒体机构作为“新闻把关人”,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是自上而下的,新闻信息以媒体机构为中心向下传播,受众的反馈需要媒体机构设置相应的通道来收集,并由工作人员进行选择、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媒体机构中;而通过自媒体技术手段,公众可以参与新闻生产、传播,成为受众的同时也可以转化为传播者,个体具有高度的主动性,新媒体赋予了公众在新闻传播中更多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可供性”理论来探讨。
首先,新媒体技术为信息传播主体提供了原创生产平台,其海量存储和传播空间的“可供性”将多元的传播主体链接成“信息共同体”,这个可编辑、审阅、复制、关联的平台降低了新闻生产壁垒,使得自媒体传播主体得以进入新闻生产领地,“生产可供性”决定了公众新闻的个性化制作。
其次,新媒体平台通过广泛连接和激发用户、有序组织专业媒体,为多元的传播主体提供了充分协作和对话的可能,分散的、非持续的信息生产与专业的新闻生产交织,形成多渠道、系统性分发的传播矩阵,“社交可供性”使得公众新闻交互行为中通过媒介示情的倾向更容易得到满足。
最后,便于携带、可定位和兼容的“移动可供性”,使用户的信息消费不再受制于媒体已定的时空,公众新闻信息内容生产与分发由于这种“移动”形成含有各种变量的共享。一条新闻信息由某个用户制作并发布,有可能得到千万个用户的反馈,这千万个受众通过转发和评论再成为新的传播者。
三、公众新闻的规范策略
(一)专业新闻机构的吸纳与引导
公众新闻的生产者具有非职业、非专业的特点,只有少数从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转型而来的自媒体工作者具备一定的新闻采编能力,绝大部分自媒体无法完成专业新闻的生产制作,因此公众新闻容易出现新闻失实现象,甚至会造成虚假新闻的传播,引起负面舆论效应。专业新闻机构正好可以弥补公众新闻的缺陷,同时公众新闻为专业新闻生产提供了更广阔的信息源,特别是一些社会突发事件,主流媒体与当事人、亲历者比起来还是反应迟滞。自媒体链接的是整个社会关系网,而媒体机构只是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构建出自己的一套信息网,涵盖范围有限,社会生活中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无法第一时间掌握。媒体机构的新闻从业人员可以将公众新闻的信息作为专业报道的线索,把自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渠道,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报道。
(二)厘清权责归属
公众新闻产生于自媒体,自媒体的运营同样牵涉各种商业利益,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取关注从而进行变现,一些自媒体经营者使用违规手段来借助社会热点打造爆款。个体毕竟缺少从事新闻采编的能力、资源、保障,多数情况下大众只是“热点消费者”,形成典型的“个案围观”现象。因为没有权责归属限制,导致个性化的表达泛滥,其中不乏煽风点火、语出惊人之词句,对于舆论影响通常不会考虑,因此厘清权责归属至关重要,公众新闻一样要具备社会责任意识,政府相关部门应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加强监管,完善媒介暴力事件的惩治细则,对新闻舆情进行鉴别,形成平台负责制的“网络新闻把关人”机制。公众、自媒体运营者、媒体机构、网络平台、政府监管部门等要各负其责,防止公众新闻传播失范。
[本文为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规划项目“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高校政治安全教育实践研究”(编号:18YJA710036)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我国网民规模10.5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74.4%[EB/OL]https://new.sina.ca/2022-0831/detail-imizmscv8462853.d.html.
[2]陈鹏.公众新闻生产如何改变新闻业:基于新闻规范、观念与文化的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12):63-67.
[3]陈逸君,贺才钊.媒介化新闻:形成机制、生产模式与基本特征——以“脆皮安全帽”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9):125-131.
[4]陈逸君,贺才钊.媒介化新闻:形成机制、生产模式与基本特征——以“脆皮安全帽”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9):125-131.
[5]刘丽,武晓习.“we media”是新媒体还是伪媒体:“自媒体”概念真实性的求证与反思[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5):118-123.
[6]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8.
[7]王建峰.“后真相”语境下对客观性新闻理念的反思[J].青年记者,2019(9):38-39.
[8]张鑫.自媒体去中心化传播分析[J].传媒,2017(7):47-48.
(马强为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安全工作部副研究员;张辰昊为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安全工作部研究实习员;苏小龙为天津师范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