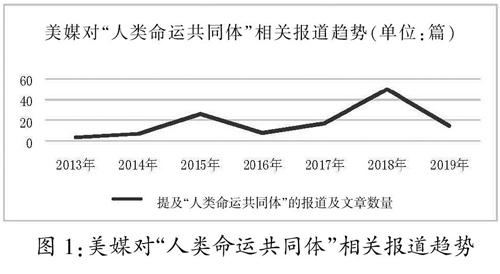□李 怡 王雪桦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风云巨变、生死存亡,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强悍的共同体意识。文化具有记忆、宣传功能,是唤起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武器,华语导演胡金铨(1932—1997),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改弦更张、民族气节寄付光影之内,在中国电影制作技法、艺术水平进步和国际传播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对胡金铨的重提并非为了重复对其早已有之的旧评,而是为了说明胡金铨的艺术实践放之今日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将个体观众凝聚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力量。
一、遗失的故乡:胡氏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及辩证弗洛伊德说,那些清醒状态下似乎已遗忘的儿时经历,很可能再现于梦中[1]。作为“造梦者”,胡金铨的自身经历对其创作有深刻影响。
(一)家风传承:血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共同体”一词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追求共同意义上的善而建立的,滕尼斯认为共同生活是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生活。家庭这个组织形式正是建立在亲密的私人关系基础上,以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的亲密互信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成员奉行的统一原则,亚里士多德谓之“共同意义”,放置在家庭中便是“家风”。
胡金铨五岁时开始与胡氏族亲在一座四合院中共同生活。胡金铨的祖父胡景桂曾为清末大员,学识渊博、急公好义、懿行佳话①;父亲胡源深作为实业家,秉持工业救国的理想;五哥、六哥、五姐出于对国民政府的失望都加入了共产党。如此优良正直的家风正如滕尼斯规定的精神共同体状态 “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的相互影响、彼此协调”[2],胡氏家族由“血缘共同体”而形成的“精神共同体”氛围对胡金铨影响至深。1949年解放前夕,胡金铨只身一人来到香港,与内地的至亲失去了联系,留给他的便是胡氏家族精神的影响。
(二)情感升华:家族精神共同体-民族情感共同体1950年代,胡金铨开始辗转港台两地拍电影,当时港台两地刚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根亲意识缺失,内地南下移民众多[3],大量迎合这些观众乡愁想象,披着中华文化符号外衣,有表无里的影片涌现。为此胡金铨以创作文史武侠,严格考究史实来纠偏不良现象,《侠女》《忠烈图》中的道具服装、场景布置和景深处的字画都力求符合朝代背景,这种务实求真的态度与胡氏家风一脉相承。
胡家曾是北平长安大戏院的股东,胡金铨从小就对京剧十分熟悉,他影片中脸谱化的人物表现方式、独特的武术技击节奏都是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结果。他的六伯母是佛教徒,胡金铨自小见伯母念经修习②,自然对宗教思想、佛家文化多了一层思考,为其暧昧的中式儒释道美学埋下了种子。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这些经历都成为残存于胡金铨潜意识中“梦”(电影)的原型。
经年的漂泊使胡金铨渴望找到一个心灵的寄寓地,而常年与亲人的“失联”使他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地方作为“故乡”怀念,只得将自己民族一员的共同身份放大,表达对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处境的关怀。抵抗外族入侵的《忠烈图》;诉说儒家忠义的《侠女》;抒发离散情怀的《画皮之阴阳法王》,体现的都不是对某地的缅怀,而是对民族的依恋。
建立起观众的情感共同体,认同机制非常重要,[4]通过电影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伦理温情与文化传承[5],是构建共同体美学的必由之路。胡金铨将在家庭熏陶中得到的传统文化知识,运用于寄付寻根情结的电影创作中,激发起中华民族固有的共同体情感,完成了民族情感共同体对家族精神共同体意识的超越。
二、人物图谱:空间、身体与文化内核胡金铨的电影中,客栈、朝堂、寺庙和阴阳场景较为突出,并产生了相应的人物,最终指向社会这个虚空的大场域,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保持着互生,形成了以空间情景为脉络的人物关系图谱。
(一)客栈:侠客/匪徒角色《大醉侠》《龙门客栈》《喜怒哀乐之怒》《迎春阁之风波》是广为人知的“客栈四部曲”,客栈往往设置在大漠孤烟、鱼龙混杂的江湖深处,人物被自然地分为侠客、匪徒两个阵营。以儒家义德为参照,这两类人物对客栈空间有着不同的感知。
儒家道德中,“义”往往与“利”对立,强调为人的道德、良知要大于个人利益。胡氏武侠江湖中,营救友军、报仇雪恨的忠义之后(如金燕子、朱骥),匡扶正义的江湖游侠(如萧少镃、范大悲);与那些为祸朝纲的奸臣(如曹少钦、李婉儿)和心狠手辣的山匪贼党(如索命五虎),前者为公,而后者却是为了个人私利。胡金铨将对儒家义德观的强调与空间—人物的感知并置,在侠客的感知中,客栈是一个甘愿舍生取义的壮烈空间,在匪徒的感知中,客栈则是一个阻碍利益实现的诡诈空间。
(二)朝堂:掌权者/弄权者角色《迎春阁之风波》《忠烈图》《天下第一》中出现的朝堂场景较多。君与臣是朝堂空间的主要人物关系,君臣关系首先建立在权力的从属秩序上,可从掌权者和弄权者两种身份视角加以考察。
影片中君主角色的失败,多是因为权力滥用导致的掌权者身份缺席。《忠烈图》中的君主缺位、官员失职,即使俞大猷等人全力抗击,终究落败。《天下第一》中的君主偏信谗言,不加约束自身欲望,没有做到“举直错诸枉”、克己复礼、为政以德,最终自食恶果。而对于臣子来说,儒家忠德要求为臣忠、为民忠、为人忠三位一体,电影中弄权者的身份确立是由于儒家忠德的缺失。欧阳年、曹少钦和李察汗等奸臣,欺君弄权、阴险狠毒,为臣不忠君报国,为人不忠厚诚恳,如此,忠德成为判断臣子身份在场的标志。
(三)寺庙:邪恶者/正义者胡金铨评价他个人是 “俗念未尽,临时抱了佛脚”[6],影片中对佛理感悟的表达也融入了世俗伦理层面的是非观,人物定性的参照物并非信仰身份而是“欲望”。
《空山灵雨》起源于权财欲望的冲突,《山中传奇》《画皮之阴阳法王》中的鬼怪都保留着人的欲望。佛教将欲望视为人痛苦的根源之一[7],它的任务是教人从痛苦中解脱,并非维护社会道义。可胡金铨影片中的邪恶欲望持有者们都以一种狰狞的形态被身体消灭了,如乐娘在死后虽面目全非但神态极其不甘,这在佛教层面并不算是真正得到了解脱,而是胡金铨从社会道义出发做的处理。
在中世纪神学统领下,精神救赎必以牺牲身体的方式来达到。欲望使寺庙空间这个超验性空间中的人物有了身体感知的权利,正如白狐悟到《大乘起信论》的真正法理后剃度出家,以身体上的受戒表现精神上的超脱。人物的身体感知能力便与寺庙空间的超验性意义产生了互生。
(四)阴阳界:人/鬼角色胡金铨拍摄的电影似乎总是着力于传达儒家和佛家思想,道家仿佛被忽略了,但影片中常出现的“鬼”的角色却离不开道家文化。“鬼”原是佛教宇宙“六凡四圣”中的一凡,[8]佛家中未论及鬼的 “超能力”,道教却发展出人鬼相克的观点,“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人遂除之之谓人伤鬼也”,在老子看来鬼神能对人产生威慑和伤害。[9]胡金铨影片中鬼的形象显然借鉴了道家的鬼人观。
影片中鬼与人能够共处一个空间,也是在道家鬼人观影响下以重获身体感知为基础的。阴阳法王来到阳界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满足身体感官来确认自己的阳界空间在场。尤枫被困在阴阳界时要靠画皮遮面度日,被剥夺了身体感知能力,片尾她投胎为王顺生的孩子,重获肉身,身体感知成为她由阴界走向阳界的反映。
以“儒释道”文化为人物在场的条件,客栈、朝堂、寺庙、阴阳这四类原本只带有民族文化特征的空洞的能指符号拥有了深厚的所指意涵,由实体空间转变成可被感受的文化空间。自古以来,儒释道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这种价值选择中的集体无意识正是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共同体意识。
三、类型拓殖:民族诉说的变与不变胡金铨拍摄的电影中,《大醉侠》《龙门客栈》《喜怒哀乐之怒》《侠女》《迎春阁之风波》《忠烈图》《空山灵雨》《山中传奇》《天下第一》《大轮回之第一世》《画皮之阴阳法王》可算作广义上的武侠电影,《玉堂春》是黄梅调电影,《大地儿女》是革命战争影片,《无冕皇后》《终身大事》是现代时装片,它们涉及中华民族发展的多个节点,是从封建传统到现代化的民族命运缩影,共同诉说着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命题。
(一)殊途同归:题材选择的一致性上述几种美学风格相差甚远的电影类型,有着明晰的线索:忧患意识与救亡情结。武侠电影中的“患”是邪恶、朝堂奸佞之患,而“救”,《大醉侠》《龙门客栈》《侠女》是对“忠义”的拯救;《迎春阁》《忠烈图》是对家国民族危机的拯救;《空山灵雨》《山中传奇》是对自我精神困境的拯救;《画皮之阴阳法王》是对处于“中间”的“无根之人”的自救③。
1960年代,在当时大拍娱乐片的邵氏,胡金铨将自己独立执导的首部作品定为抗日影片 《大地儿女》。《玉堂春》不同于同时期的黄梅调电影注重对缠绵的爱情故事的表现,而将造成苏三悲剧的社会原因道出,使影片有了一定的反思意味。《无冕皇后》体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反思。胡金铨对台湾的广告夸大和环境污染严重印象很深④,便以此为主题拍摄了《终身大事》,反映经济起飞下“四小龙”之一台湾的行业发展乱象,这些都体现出他对古今社会弊疾敏锐的洞察力。
(二)以小现大:时涉古今的忧患意识胡金铨对古今社会忧患意识的表现,皆是从小人物入手,无论是顾省斋、何云青,还是客栈老板、伙计,都是时代裹挟下的小人物。他们在历史浪潮的裹挟中,无法掌握命运的主动权,不得不被动地做出抉择,这正是历史忧患加至个人的结果。关于《大地儿女》,胡金铨表示“抗日战争连那些地方(小都市和农村)也影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各行各业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想写的正是这种反应”。⑤《终身大事》更是表现个人抉择在社会急速发展下的无奈。
这种底层关怀与胡金铨的个人经历影响有关,他幼时随父母在外漂泊,见惯了战乱年代的人世百态,后又目睹亲人们在混乱时局中各自沉浮,17岁离开故乡身无分文地开始谋生。事业有了起色后辗转于港台之间打拼,晚年定居美国。可以说他本人正如电影中的人物一般,是被卷入时代浪潮的微小个体,反映出了时代的变迁与无奈。
中国文人历来有着“位卑不敢忘忧国”的传统,一面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一面对国家的发展抱有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0]。对民族文化的守护责任使得胡金铨根本不像一个国际名导一般风光,时常捉襟见肘。他举债自费送《侠女》前往戛纳参展,才有了影片在国际影坛的成功;此后拍摄了十部电影,仍然是入不敷出的境地。[11]未完成的《利玛窦传》表现利玛窦带西洋技术到中国的过程中,对腐败官僚主义思想的批判,“万历皇帝”这个角色又带有知人善用、慧眼识珠的光环。这正是胡金铨文人精神的体现,即肯定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态,又对现实社会痼疾有着针砭时弊的责任感。
四、从民族想象到共同体意识的诗性语言策略通过将传统儒释道精神具身化为微观人物,将其抛入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命运的困境之中,胡金铨将故事世界勾连为一个带有相同文化根基,经历了相同命运变迁的民族整体,并从技术美化和诗意影像表达两方面激发起观众的民族想象。
苏联蒙太奇学派对胡金铨产生了很大影响,《侠女》采用了四格镜头快速、简短的剪辑方法来表现“女侠”不凡的身手。⑥该片中月下弹琴的场景,胡金铨用拆去聚光镜的采光灯和涂满浆糊的白纸造了一轮明月,⑦还原了李白《月下独酌》中明月高悬的清冷氛围。技术雕琢带来的美化影像是对民族文化符号的理想化展示。
克里斯蒂安·麦茨提出了电影的认同机制:观众首先与摄影机产生认同,再与银幕中的世界产生认同。通过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借鉴,胡金铨将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融入电影创作当中。
“意境”是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既要求实境的景物描写,又要求虚境的审美想象。胡金铨擅长以“人在画中游”的卧游形式,实现虚实结合。《山中传奇》中有一段山水镜头和何云青行走镜头,这个片段中,观众通过摄影机随着何云青“行走”,对山水风光进行卧游式的观赏,达到了对山水风光的族地认同,另有一段“在早年间,咱们中国有不少的传奇故事”的旁白生发了观众的文化认同,并给静谧的湖光山色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产生了看山非山,看水非水的虚情。借鉴自戏曲的武打动作、配乐,富于韵律;建立在“儒释道”文化基础上的主体经验抒发,都符合古典诗学的要求,使观众在熟悉的审美习惯当中,认同了故事世界中的民族整体,并在诗意影像中生发出对其的美化想象。
然而,民族与共同体还有些许差别,安德森将民族视为人造物,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亚里士多德、滕尼斯概念中的共同体都是建立在成员亲密互信基础上的自然状态。要将两者等同,便为电影诗学提供了空间。波德维尔提出“电影是如何同各种跨文本规范相关”的问题,电影诗学便是以历史的语境来同时揭示规范之间的变化与连续。[12]胡金铨电影的诗性气质正是来自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跨媒介式体现。胡金铨个人情感的影像表达通过中国古典诗学的整合,被转化为全体中华儿女都可以体味到的“我们”之共有情感,实现了胡金铨的“我”之诗性语言到观众之“我们”的共有感受之间的流动,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浮于表面的文化符号,更是熟悉的诗性传统和中华美学气质,产生了关于中华民族文化与命运共同体的心照不宣的“我们感”。
五、结语胡金铨电影中从人物到意蕴,从外延到内涵而构成的独特话语表达体系,都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坚持与探索下得出的,这些积淀着民族精神内核的多元文化形态,是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文化语境与修辞基础。[13]胡金铨通过人物图谱、类型拓殖、民族想象三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赋予了电影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成为唤起观众共同体情感的艺术力量。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胡金铨、山田弘一、宇田川幸洋著:《胡金铨武侠电影做法》,厉河、马宋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16页、第210页、第67页、第119页、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