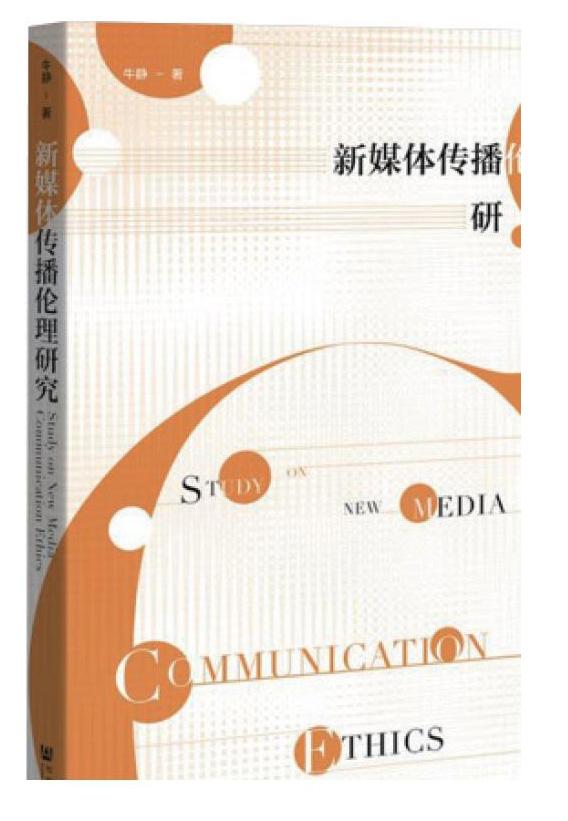在传统新闻媒体占主导的新闻实践中,新闻伦理规范中的客观性原则一直受到新闻工作者的认可。在这种理念下,情感被视为是影响新闻真实、客观的非理性因素。这种以尽可能避免情感介入为基础的新闻报道,有时会引发新闻报道的伦理争议。在各类社交媒体对传统新闻业带来巨大冲击的今天,受众更容易被情感性的内容所打动,更愿意基于情感性的内容进行是非判断。新闻伦理规范中的客观性与新闻实践操作中的情感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时常会反映在新闻报道上,成为一个需要从理论上来进行探讨的问题。
受众希望通过新闻报道获得对社会事实或群体组织的情感确认,并在连续性的情感关怀和认同中形成连贯的情感价值。这与关怀伦理的核心性要旨有相符之处。关怀伦理是对义务论和后果论等主流伦理框架的批判性回应,关怀伦理学家认为这些框架未能捕捉到道德生活的重要维度,如关系性和相互依存性。关怀伦理认为同情、怜悯和关心等情感是道德资源,而不是障碍,情感调和有助于我们识别需求并做出适当反应。如何在客观报道的前提下,汲取关怀伦理的理论内核,将关怀合理地融入新闻报道中,从而构建“有理、有情”的新闻报道,这是本文需要回应的问题。
一、理论的启发:关怀伦理在新闻实践中的意义
传统新闻业的实践框架更多是基于客观与主观、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而建构的,“客观、理性、中立”成为“好新闻”的评定标准。但缺少关怀的新闻报道无法抵达受众内心,甚至引发新闻二次伤害。所以,“情”与“理”的矛盾与调和逐渐成为新闻学的热点议题。
在承认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者需要将关怀伦理引人工作实践中。关怀伦理是一个道德框架,强调关系、情感投入和相互依存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性。关怀伦理强调了同理心、同情心和关系动态在理解道德责任方面的重要性。关怀最早是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用德语“sorge”(操心)这一概念来表示,他认为关怀(操心)不能从意志、愿望、嗜好、冲动这些东西派生出来,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奠基在关怀(操心)之中。在《关怀: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观点》中,诺丁斯(NelNoddings)认为关怀作为一种联系或遭遇是根植于人类生活的属性,并不是强加的属性,所有人都希望被关怀[2。关怀伦理与传统的道德逻辑不同,将依赖性和脆弱性视为人类主体的普遍特征,且无须克服。关怀伦理虽然属于女性主义,但这种依赖性与脆弱性并不局限于女性。这打破了传统逻辑关系中任何情境下的普遍规则,将关怀他者视为一种道德责任[3。卡罗尔·吉利根(CarolGilligan)强调了传统的道德框架往往忽视了关怀关系中产生的经验和道德观点,倡导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承认关怀在人际交往中的道德分量4。此外,关怀伦理提出对他者的关怀应是长期的认同与支持而不是片段性的关心。虽然新闻业秉持客观性原则将真实、客观的新闻事件传达给受众,但新闻业同样需要承担关怀责任。关怀伦理中指出,人的依赖性、脆弱性特点与报道主体的特点暗合,共同构成新闻实践中关怀实施的理论基础。
在关怀伦理框架中,关怀被着作一种劳动,新闻业务的实践形式与关怀劳动暗合。萨拉·鲁迪克(SarahRudick)认为,关怀确实是一种劳动,却又远远超出了劳动[5。她在书中写道:“关怀工作是通过给那些给予和接受关怀的人的关系所构成的。”二者都将关怀指向了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敏感性以及依赖性致使新闻工作者需要考量与他人的关系,需要从事关怀劳动。
以弱势群体和灾难事件的报道为例,新闻报道者往往会将采访对象悲惨的境遇投射到自己的实际情绪中,达到与采访群体的情感共振状态。这类蕴含了关怀劳动的报道,往往会得到受众的肯定。
新闻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实践,这一特性要求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深入理解特定的采访主体。根据诺丁斯的观点,“真正的关怀行为涉及对特定他人情感、动机的敏感性”6,关怀实践中需要对他人的感情保持敏感的能力,来弥补理性报道为导向的伦理缺陷。在良好的沟通关系中,相互之间的认识和敏感致使成员们之间知道如何避免争端或者受伤。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同情、尊重、倾听、关怀等情感性伦理,敏锐捕捉采访对象和受众的情感需求,把握报道的情感倾向,使新闻报道有助于达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共识。
总体来看,关怀伦理并非停留在单纯的理论讨论层面,其有着丰富的实践价值。关怀伦理强调承认人的脆弱性等特性,认可关怀是一种劳动,这为新闻实践提供了启发。
二、实践的思考:关怀伦理中的具体要求对新闻实践的启发
康德道德伦理和功利主义伦理追求强调道德人的理性决定,美德伦理学将关注重点放在个人的视角之下,关怀伦理学将关怀视为人在关系中相互依赖的情感需求。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Holder)阐明了“关怀的人”的动机起点,即“关怀的人”不仅有关怀动机,还需要有从事关怀实践的能力。悲剧性事件的报道者应是具有关怀能力的传播者,如果一味地强调中立、客观地呈现悲剧事件的当事人,那便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儒家伦理学中,“关怀”表现为“泛众爱”,即“推己及人”的情感关怀,对血缘亲情的关爱推衍至陌生众人的移情。中西伦理学中的关怀理念都为将关怀纳人新闻实践活动中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关怀伦理中的移情原则,启发新闻工作者报道有温度的新闻
关怀伦理强调情感参与在道德推理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将情感视为理性决策障碍,关怀伦理承认,同情、怜悯和爱等情感是我们道德判断的核心。这些情感不仅指导我们的行为,而且还指导我们在人际关系背景下对是非对错的理解[7]。关怀伦理启发新闻工作者开展有关怀的工作实践,促使新闻工作者有更好的移情能力。“移情”(empathy)一词最早在英语中出现是在20世纪早期,而移情所蕴含的思想在大卫·休谟(DavidHume)的《人性论》以及亚当·斯密(AdamSmith)的《道德情操论》中天量出现。只是他们没有使用“移情”而使用了“同情”(sympathy)这一词汇[8。后来西方伦理学将“理性”作为判断道德的标准,忽视了大卫·休谟所倡导的情感主义,直到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Sloot)提出应当把人的情感和动机视为道德行动的前提,移情开始被伦理学家所重视。在他看来,“移情”不仅指感同身受地感知他人的实际情感,而且指移情于他人将会如何感受”。按照斯洛特的说法,移情就是“看到他人痛苦的时候,使得我们似乎能感觉到这种痛苦也侵人了自身”[9]。
如何以关怀的参与者角色开展新闻实践,进行新闻内容的生产,这是新闻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关怀伦理强调自身的具体情境,讲究实际的“移情”。如果忽视报道主体的个人情感,只是将自己的理解投射到他人的个性之上,这不是真正的关怀关系。在悲剧事件中,需要新闻工作者设身处地地感知当事人的情感,只有这样才可以写出有温度的报道。斯洛特认为对他者的尊重、理解、关爱可以通过“移情”实现。大体来说,当且仅当一个人对他人表现出恰当的移情关怀时,才能够表现出对他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
一些报道往往打着“为他好”的旗帜而违背他人的意愿,这缺乏对事件受害者的尊重,实际上也是缺乏对他人作为个体的尊重。在新闻实践中,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情感的有效传递和相互理解是获得认同的有力方式。在实际采访中,新闻工作者如果无法进行移情式的思考,一味追求新闻效果而过度干涉采访对象则无法开展关怀和进行符合人性的报道。
(二)对具体的他者的关心而形成的关怀关系为持续性的新闻工作提供保证
新闻活动是以“现实的人”为核心开展新闻实践,新闻实践中同样需要关怀关系的支撑,这关系到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所引发的社会效果。关怀伦理学中承认人的情感需求,强调只有将伦理关系和行为诉诸道德情感因素,开展关怀才能消弭距离感。所以新闻工作者认识并持续性地践行关怀关系,是职业要求也是社会责任。将关怀伦理引入新闻实践中,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在新闻实践中构成良好的关怀关系。
关怀伦理中“强调关系”而非行动者,重视的是关怀关系,而非将关怀只看作一种美德。关怀伦理认为个体天生相互依赖,依靠彼此获得情感支持、实际帮助和社会凝聚力。作为女性主义立场的伦理学,吉利根(CarolGilligan)提出的关怀伦理源自女性的立场和视角,发觉女性在面对冲突时更注重关系的维系。在诺丁斯、斯洛特等人的研究中,关怀伦理的理论范畴突破了性别界限,提出关怀是依据“关怀关系”来衡量的。而关怀关系要求对需求的回应、敏感、共情以及信任10在关怀关系中,感受到对方带来的幸福,关注对方的情感、尊重对方在现实情境中的需求、并能够有效回应。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Holder)在《关怀伦理学》一书中认为:“认真关怀他人的人不是在追求扩大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所关怀的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他们追求并保持着与他人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爱关系的健康状态包含着关系人的良好合作,还有关系本身的良好。”[1关怀不再是一个单向的动作,是双方建立的互惠互动的伦理关系。关怀伦理是一个重视合作、同情和相互责任的道德框架。
弗吉尼亚·赫尔德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权利或个人的偏好作为重要聚焦。因为人被视为关系之人,而不是作为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中自足的个人,关怀关系被视为核心价值。”[12]对于新闻实践中如何建立良好的关怀关系的问题,关怀伦理认为应当叙述理解而不是公式化地应用规则,它从敏感、共情、责任等方面为新闻实践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新闻实践中要求新闻工作者首先拥有敏感的能力,关注到采访主体的真实感受,切实地理解对方的处境。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应避免使用过于刺激性的语言和画面,尊重受难者家属的隐私和感受,体现人性的关怀。其次,在报道中理解并传达采访主体的情感和经历。通过共情,新闻报道不仅能够呈现事实真相,还能引发公共的思考和共鸣。如在报道创伤事件时,关怀型记者或许会考虑到对弱势群体的片面报道可能会延续伤害。这些考虑不会降低新闻标准,而是通过承认有道德的报道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准确性一它需要人性的敏感性来提高新闻标准。关怀伦理支撑下的新闻实践,并不是通过新闻报道向受众列举应该实施的道德清单,而是通过关怀鼓励人们如何在人际关系中践行道德价值,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三)关怀伦理中的利他性原则规避了自我中心视角,利于建立共通的新闻关怀理念
开展有关怀的新闻实践,进行关怀式新闻报道,前提在于明确利他性在关怀关系中的作用。在诺丁斯看来“关怀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实施该行动的关怀是否充分地或者良好地展现了其关怀动机。”[13]利他性要求关怀者理解他人,在具体的情境中感受被关怀者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利他性关怀具有可行性,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关怀。这种关怀无须从伦理道德层面努力,是由人本能的直接感受而发。二是基于自然关怀提出的伦理关怀具有可操作性。“利他”的关怀要求双方无须承担完全对等的责任,更多的是对被关怀者的境遇关注,暂时搁置主体角色以被关怀者视角看待当前的情境,同时密切关注对方的需求、情绪和行为。新闻工作者具有优于被采访者的权利优势,现实情境中新闻工作者对他人需求的预判总是基于自己的认知和立场,容易基于自己的主观偏见去看待被采访者。这就要求新闻实践中的关怀行动要以被关怀者为出发点,努力接近对方以实现利他性关怀。
利他的关怀关系内核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对当下情境的道德认识[14]。这种关怀行为区别于个人立场下的情感付出,而是尽力达到关怀者付出一一被关怀者有回应的关怀闭环。这提醒我们,采访者在新闻实践中以他利性关怀为出发点,以伦理关怀为责任要求维持利他的关怀关系。特别是负面事件的新闻报道,通过实际的采访活动,新闻从业者需要基于他者的经历开展切实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同样也反馈给被采访者,采访对象感受到新闻工作者的真切关怀后对采访工作给予真实且自由的回应,此时新闻工作者实现了作为关怀者的自身价值。关怀伦理通过强调记者与消息来源和社区建立关系和互惠来改进新闻报道方式。关怀型记者不会通过交易互动来获取信息,而是花时间与他们报道的人建立信任和理解,从而达到互惠的效果。
总的来说,新闻工作者在遵循客观性新闻原则和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同时,要保有一种被激发、被唤醒的情感反应,需要具有关怀认识,以关爱和道德来考量自己的工作。新闻实践中的利他性关怀旨在确保健康、自由的双向沟通,以达成新闻采访。
结语
关怀伦理的理念在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工作、社区建设等领域已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因为关怀伦理的框架可以指导专业人员解决实践中复杂的道德困境。本文通过对关怀伦理中的关怀关系、移情、利他性、情境性等方面的阐释,探究新闻业如何通过关怀伦理理念消除媒体与用户、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性关系,探讨关怀伦理作为新闻理念和实践的补充规范的可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实践中要防范过度关怀。如新闻工作者受情感驱使过度关心对方的故事,忽视了被关怀者真正的需要,采访对象被新闻工作者个人的关怀情感所裹挟,极易引发采访主体的二次伤害或侵犯其隐私权。所以,新闻工作者需要拥有良好的关怀动机,不过度“消费”苦难,这不仅包含道德层面上的相互平等,还涉及实践环节中的尊重、体谅、理解。同时,关怀伦理也强调情境敏感性,认为在一种情况下适用的做法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并不适合,因此,伦理决策必须考虑到所涉及个人的独特需求、历史和环境。这提醒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实践中应实际考虑到他人的具体工作环境,而不是遵循一些抽象的道德原则。新闻采访情境中的关怀关系往往要通过对现场采访、观察和个人感悟来建立,而非仅仅按照既定的脚本生成。
关怀伦理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框架,为传统的以正义为中心的道德理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的基础建立在一系列哲学见解之上,这些见解强调关系、同理心和人类经验相互联系的重要性。传统新闻伦理优先考虑公正和情感距离,而关怀伦理则引人了一个重视关系、背景以及报道对他人、对社区的潜在影响的框架。因为记者不可避免地会与消息来源、受众和他们报道的社区建立关系,通过承认这些联系,记者可以进行更细致入微的报道。关怀伦理启发我们,新闻业所关注的不应是表象的事件,而是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成员的关系性。新闻媒体正视新闻工作者在事件中的情感表达,基于情感上的移情进行报道,有利于建立新闻机构良好的公信力。将关怀伦理引人新闻实践中,或将显示新闻工作者对新闻责任的根本性重新概念化一一新闻不仅仅是准确报道事实,还要考虑这些事实如何影响受众。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211.
[2]Noddings.Startingat home.Caring and Social Policy[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11.
[3]刘念,李萍.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何以可能:以弗吉尼亚·赫尔德的关怀伦理为视角[J].道德与文明,2020(3):109-114.
[4]孙岩,陈露.女性主义视域下关怀与正义的哲学审思:基于弗吉尼亚·赫尔德的关怀伦理学[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3(1):116-121.
[5][11][12][美]弗吉尼·亚赫尔德.关怀伦理学[M].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5;15;190.
[6][9][美]迈克尔·斯洛特.关怀伦理与移情[M].韩玉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14;16.
[7]Reich,W.T.EncyclopediaofBioethics[M].New York:Simonamp;SchusterMacmillan,1995:319-331.
[8]王建斌.“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何以可能: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正义观探析[J].齐鲁学刊,2020(2):92-98.
[10]Virginia Held.Can the Ethics of Care Handle Violence?[J].Ethics and Social Welfare,2010(2):113-119.
[13]陈欢.关怀伦理学的两种理论进路:论赫尔德对斯洛特的批评何以无效[J].世界哲学,2020(1):136-143;161.
[14]石中英,余清臣.关怀教育:超越与界限:诺丁斯关怀教育理论述评[].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4):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