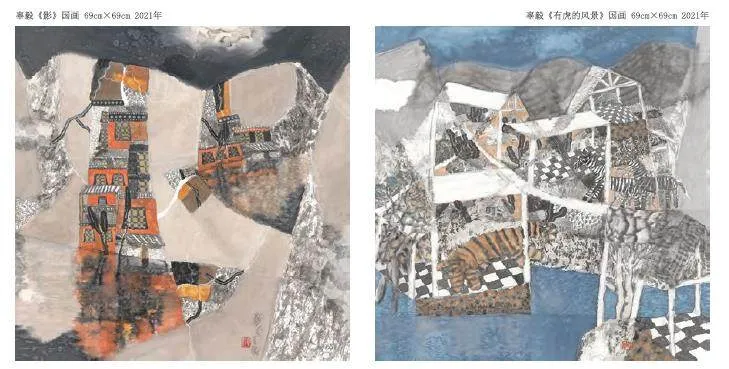沙" 汀
1904年12月19日—1992年12月14日
本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被鲁迅称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1922年,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6年,师范毕业后赴北京等地求学不成后返回四川;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由于政局动荡,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白色恐怖迫使其前往上海,并与川籍学友任白戈等创办“辛垦书店”;
1931年,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在上海相遇,共同研究探讨小说创作;
1932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同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
1938年,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同年11月随贺龙同志去晋西北和冀中一带体验生活,后写出《随军散记》《奇异的旅程》;
1940年,回到重庆,陆续发表《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堪察加小景》等短篇小说,三部长篇《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也相继问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担任全国和四川省文学界的领导工作,继续创作出版短篇小说散文集《过渡》;
1976年,“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执笔,先后创作中篇小说《青㭎坡》《木鱼山》《红石滩》。
1992年12月14日,沙汀于四川成都病逝,享年88岁。
对于文学大家的形象到底该如何塑造,笔者试图从他人笔下的文字描绘一位从未亲眼见过的文学大家,那里有他的生平,有他的历程,有他的心血,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人?“他叫沙汀,本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出生于四川安县。”这是如今大部分人初识“沙汀”时所知的基本信息。一眼茫然,却成了知晓的契机。为撰写本文,笔者开始阅读他的事迹与作品,于是对沙汀先生的人生轨迹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由此,笔者将借由其作品、创作历程、生平记录及他人的评述,尝试塑造出我眼中的这位文学大家。
起源
杨朝熙出生的安县得名于大安山,处在山地与川西平原交接的边缘。境内82%为丘陵地带,与紧邻的成都地区的富庶恰成对比。虽然四面环山,但是杨朝熙小时候居住的宅子却是极其宽阔的,家中还有一位精明强干、读书致仕、写得一手好字的祖父,可惜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逝世。之后的长辈在料理家业方面都不精通,对功名利禄也不热衷。等杨朝熙长大到识字之时,家中只余下一屋子的书籍文献还昭示着这个家曾是书香门第。至少在那时,还很难将这般境地下的他与“文学大家”这样的称呼联系在一起。在小学时期,杨朝熙也是个不爱学习、会逃课的“问题学生”,是母亲的庇护与正确教导加之他本身的敏感与自省,才彻底改写了他们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
母亲一心要延续书香人家的香火,于是杨朝熙七岁发蒙读书。他的第一任先生名为孙永宜,因为受同行排挤,一气之下不再教书改种庄稼,这般奇怪的志气,让杨朝熙对文人的骨气有了初步印象。后来又经历了帮他定性的蒋品珊、文学启蒙人于瑞五、为他的写作打下基础的游春舫和谢建卿……就这样他的私塾生涯断断续续到了18岁。相较于大多数文学家,杨朝熙的写作生涯要来得略晚一些。虽然在之前的学业中已渐有文学底蕴,但因为长期处于小乡村,未能及时接触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所以真正开始接触现代文学还要等到前往成都读书之后。彼时的他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学校师生的影响,逐步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末和其间的人物与文学作品。终于在政治、学业、情感的悲欢离合之下,1931年与阔别六年的汤道耕(艾芜)的再次相遇,成了杨朝熙(那时的他叫“杨子青”)正式踏上文学之路的契机!
杨朝熙的写作生涯起源于带有自述意味的《俄国煤油》,但“沙汀”的开端应该是《码头上》。在《俄国煤油》受到鲁迅一针见血的点评后,杨朝熙不再轻易描写知识分子,而是改为描述自身更易把握的土地革命文学,如《码头上》《老人》都是这种类型。挺过“一·二八”事变的杨朝熙遵照鲁迅的指导,又陆陆续续写了《风波》《酵》《莹儿》和《没有料到的荣誉》等文风朴实的作品。沙汀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哪怕是这些早期尚青涩的作品,在日后公布时,也是受到了之后一些同行们的极大赞赏。当然,彼时的杨朝熙还对此毫不知情。在1932年时,杨朝熙已积累了12篇习作,几经斟酌后,他决定发表短篇小说《码头上》《伙伴》和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并最终将笔名定为“沙汀”。这一年,便成了沙汀与他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小说集一同诞生的一年。
升华
不过,时代是变幻的,文学的风向也在跟随时间的轨迹不断起承转合,初接触文学时所赞扬的文学风格,到他时或许已不再是被大众所推崇的潮流。但家乡却是不变的,四季流转,人与景故去,可留在书中与心中的仍旧是儿时的家乡,那些潜藏于心中的情感与记忆,依旧刻画在每一位游子的面庞之上。这便是沙汀对自己的家乡爱恨交织的原因。他“恨”家乡的局限,小地方让他“大器晚成”;但却是爱到极深,因为这是独属于他的、无第二人可感知的心绪。对于文学家来说,浅薄使人彷徨,但独一无二的“浅薄”,却是上好的精神食粮。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这里的山水风光、民俗风情、历史传说等,都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正是这片土地孕育了他对乡土情怀的深厚感情,使四川的影子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在连续写了《战后》《老人》《爱》《一个人的出身》《一个绅士的快乐》《巫山》《喝早茶的人》等一系列阶段性作品之后,沙汀从带有革命哲思的小说故事,到更多是富有自传意味的生活小说,再到四川风俗气息浓郁的社会小说,短短两三年时间的转变已然可以看出其未来会转向创作乡土文学的迹象。
1936年还出现了一件足以说是影响他后半生轨迹的事件——母亲的去世。对杨朝熙来说,母亲是最爱护他,也是他最亲近的人。尽管随着成长,阔别多年,思想或许有了隔阂,但是记忆中母亲不够宽阔的背影与儿时的依赖之情,又怎么会轻易因为时间和距离被磨灭?借由母亲丧事,沙汀回到了四川。家中落魄远超他的想象,百感交集之下,他写出了《一个人的出身》,详细讲述了丧事的过程。之后他做主处理家中田产,北上北川,一路见证了战乱后的残骸、废墟、孤儿、饿殍,亲眼看到重灾,也亲眼看到重税。民不聊生,数不胜数。也是这短短的两日之行,将他学生时期为人民、为公正呐喊的愤慨再次唤醒,造就了他未来乡土文学的创作契机与温床。
还清家中债务后,沙汀只身回到上海。但他的人回去了,心却永远留在了家乡,借此契机写出的《苦难》将对不公的训斥、对天灾人祸的苦痛详尽道出,虽然淡化了人物的存在,却极大增强了情绪引导力,这篇受到了好友艾芜的大力赞赏,也是因为这篇,沙汀定下了“沙汀的乡土文学”的基调。之后,沙汀还在同样的情境下撰写了《兽道》《在祠堂里》《灾区一宿》《逃难》《查灾》《代理县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悲愤情绪强烈的乡土文学,皆是在一年之内写出,可见此次回川见闻对他的影响之大、记忆之深,也对他的创作灵感、情感激发之巨。
1936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沙汀等五人被选为候补理事;6月14日,沙汀从《文学界》调任至《光明》,到“七七事变”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乡土文学发表在《光明》。这一年对沙汀来说的确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因为在好不容易适应了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变化后,同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在初出茅庐之时,沙汀就对鲁迅十分尊敬,之后这位前辈更是成了他文学路上的引领人之一,哪怕后来的论述多有分歧,也改变不了鲁迅在他心中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的事实。作为抬棺的十四位青年之一,沙汀算是送完了自己尊敬的前辈最后一程,些许报答拳拳教导之恩。这场葬礼对文学界和沙汀个人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首先是受鲁迅逝世的影响,“批评文学”的火苗在文学界冉冉燃起;其次,沙汀在葬礼上与巴金结识,不但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一生之友,之后还受其委托,完成了《逃难》等作品。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对之前波澜迭起的人生来说,可以说是平和的。在平和的滋养下,沙汀再次完成了如《龚老法团》《轮下》等这些以故乡中的人、事、景为背景的乡土文学。
“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再回看之前的日子,应该有不少人会觉得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是之后大风雨的前兆。抗日战争爆发后,沙汀见到过毅然回国的文学家,也见到过近在眼前的血肉模糊,一切对于我辈来说只是书上的寥寥几字,却都一一真实地展现在了他的眼前。但是文学家在这样的场景中又能作甚?“可以帮他们(战士)写写信,读读报纸,做我能做的……”这是沙汀给的答案,只是也未能如愿。但文学家的使命似乎从未离开这位青年人,虽然未能如愿在医院帮上忙,沙汀却在医院中的伤兵口中知晓了其背后的故事。1937年12月,因生活所迫最终辗转回成都的沙汀将医院中得知的故事编写成了小说《出征》,然后又应友人的邀约撰写了几篇相关题材的评论文章。
1938年3月6日,沙汀与周文等人发起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但计划随之流产;8月14日,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11月,随贺龙同志去晋西北和冀中一带体验生活,后写出《随军散记》《奇异的旅程》《贺龙将军在前线》。学生时期的杨朝熙认为家乡限制了他的文学之路,但是青年时期的沙汀回到四川之后,却有了更宽广的文学社交圈。家乡是不变的,但是家乡赋予的意义,每每再去,总有所不同。
高潮
1940年,回到重庆,沙汀陆续开始撰写描述“收拉壮丁”的兵役主题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利用“夺金矿”来展现人性与现实下的黑暗长篇小说《淘金记》等。这时期沙汀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潮,每一篇都是后来堪称其代表作的作品。走出家乡容易,回到家乡却往往艰难。但此时几乎已经是为了写作而生的沙汀,对于家乡的隔阂早已挡不住想要完成《淘金记》和不让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的冲劲。所以在周恩来的一番激励之下,沙汀毅然带着家人重返“山区”,回到与故事背景中环境最为吻合的安县。
回到家乡后,沙汀并没有急于续写《淘金记》,而是先把在安县的新见闻编撰成短篇小说《艺术干事》 《小城风波》。之后,他才像是正式转换了心情,成功挣脱了写作的桎梏,搬到刘家酱园后院住下,潜心创作《淘金记》。说来刘家酱园与沙汀的相遇也是个传奇,外人传它闹“鬼”,有“鬼”的房子却恰成了作家的养分。这之后的生活,便像是完全冲着《淘金记》去的,言行食宿,行走坐卧,思考言语,身边的一切仿佛都化为了灵感,都能被写进书里去。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就这么反反复复、删删添添,等落下《淘金记》的最后一笔时,已过了两个春秋。这是沙汀的巅峰之一,也是他人生一阶段的解脱。若是阅读沙汀的回忆录,再去阅读此书,你会发现似乎他的一生都在《淘金记》里有迹可循,到处都是现实的影子。不过,这一特点也并非仅存在于此书,不如说沙汀的每本书都是这样得来,只是《淘金记》涉及的时间、空间跨度尤为宽广,仿佛涵盖了他的前半生。
而要说下一个阶段,笔者认为可以说《困兽记》。如果说《淘金记》是写的社会,那《困兽记》更像聚焦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每一个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有无法冲破的困境,或是金钱困顿,或是精神困顿,宛如与看不见的牢笼作斗争的困兽。一部分人甚至不惜争得头破血流也要打破现实的桎梏,努力活下去或是完成自己的梦想。说是以身边的诸位知识分子为原型,何尝又不是在映射他与那时的文学,与那时的社会?当《困兽记》完成,沙汀也正式钻出大山。短短的四年时光化作两部长篇巨作和大量精品短文,以及一个全新的沙汀。按照友人的话形容便是:他好像变成了自己书里的人。斗胆猜测,在外人看来他是变成了“深山里的人”,但在沙汀自身看来,何尝不是变成了理想的模样?作家创作时多有代入以期情节能够使人身临其境,沙汀深入深山的潜心习作,正是一种身临其境。他不仅身临,甚至还成为了。
《堪察加小景》《悼念叶紫先生》《中学生》《两兄弟》《春期》《替身》等都是这之后的作品,也成为在《还乡记》之前的铺垫与衔接。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从天而降,正逢他构思已久的《还乡记》的主题,而胜利到来的轻松喜悦,不可谓不适合创作。一切天时地利人和,都在督促着又一部力作的诞生。只是好事多生变革,之后在重庆的一番会谈让沙汀意识到初版《还乡记》中政治元素的欠缺,于是决定回到家乡后,重整旗鼓。有了之前长篇小说的撰写经验,再加上内容方向上的确定,《还乡记》不仅承接了之前作品中以现实为原型的设计,还尝试插入了一些纯“设计”的内容。作为文学家的沙汀,其文学成就在不断升华,但是生活却因为那个时期的到来,陷入了某种停滞不前的地步。
转折
1948年,沙汀大病一场,险些丧命;1949年,创作“实录”小说《炮手》《医生》《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创作短篇小说散文集《过渡》;1955年,创作个人风格浓厚的新农村文学《堰沟边》《卢家秀》,以及工业特写《柳永慧》《炮工班长冯少青》……年年写,年年作,沙汀的笔从未停歇。只是命运的规划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在1964年完成《煎饼》之后,文学家迎来了那段不得不停笔的日子。两年时间,沙汀不仅经历了爱妻的离世,还被迫与自身的“灵魂”暂别。1966年,不祥的五月,文字的囚牢将他们紧紧锁在方格子之中。进了这里,知识分子们失去了姓名,笔不是为了创作,而是为本不应该称之为“罪”的罪名而存。被迫做不擅长的体力“表演”,被不知情的群众批斗,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是手无缚鸡之力且最看重名声的文人?难以想象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怕是要耗尽毕生勇气,靠停留于脑海中的每一本书,为自己未来将写的每一个字,才能勉强支撑着活下去。
但历史的车轮碾过,却又不轻不重地远行,只余下再难褪去的车痕印迹。1972年,68岁的沙汀脱离了“方格子”,却好像还被困在其中,亲友不敢接近,组织也对他尚存隔阂,直到五年后在正义之士的帮助下,生活才终于重回正轨。“文革”结束后,重新执笔的沙汀,创作出中篇小说《青㭎坡》《木鱼山》《红石滩》。对于此时期的评价,笔者很喜欢吴福辉先生撰写的《沙汀传》里的一段话:“描摹社会的小说家,观察着中国的人间。他后来追记过这几年成都和全国发生的事件,想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动荡。”
时代仿佛即刻便开启了下一个世代。随着同行、好友的纷纷离世,新一代作家的冉冉升起,为沙汀带走了过往的尘埃,又为他带来了崭新的朝阳。《睢水十年》《应变》《抵制》是年近八十的他在同辈的子嗣、后辈们的启发下创作而出的。社会在开放,不断发展,往前数的日子历历在目,往后数的日子欣欣向荣,沙汀的生活前后一统,皆被记述在他的笔下。晚年的沙汀,过上了青年时期曾梦寐的生活,写作、写作,还是写作,平和地、只一心沉浸地写作,再无任何纷扰。直到1992年12月14日,于四川成都,病逝。
总结
无论是成组的第三人称评述,还是这短短的千余字,时光的错过,让我辈年轻人无法亲眼见证其波澜的一生,仅仅只能通过这些资料看见一位片面的“沙汀”。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沙汀先生,甚至是诸位文学家的先见之明。他们用文字留下每个时代的当下感受,用故事去记叙那个时代的现实。言及此处,笔者陡然对开头的提问有了解答。如何在文字中塑造一位“文学大家”?答案是:根本不必。并非不必在文字中留存,而是根本不必塑造。因为其创作的作品必然能连成一部创造史,哪怕只是从他们的生平中采撷些许细节串联起来,那也是极其精彩的。从他们的作品之中,对万事万物的主观视角描述和独到理解又能串联成一部独一无二的文学史、革命史,更何况他们亲历的事迹要比书上撰写的更加丰富、复杂。
时至沙汀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去32周年,学识浅薄的笔者才得以有机会系统地初识这位川籍作家及其作品。若是说撰写本文的初始是为了探索一位“陌生”的文学大家,那么在这短短的千余字之后,已然找到了探索的目的。希望能够通过这篇文章,让和笔者一样初识或浅识“沙汀”的人能够对他精彩的生平、独特的思考与背后蕴含着另一个故事的每一部作品生出兴趣,并以此作为契机,继续深入追寻“沙汀”,乃至其文学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