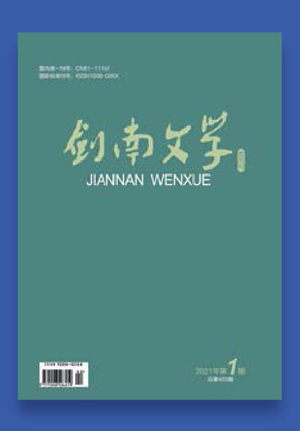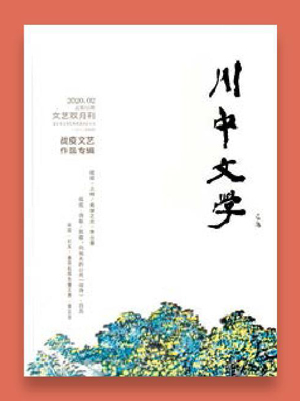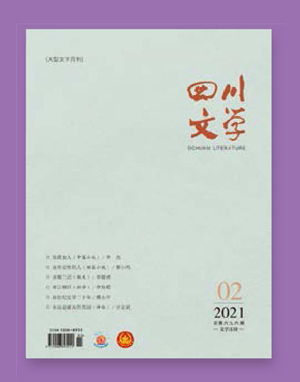清明的雨,还没有正式落地,离别的泪,却提前来了。2024年3月28日,忽闻马识途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回顾《现代艺术》与马老的过往,不禁哀思阵阵。往事云烟,冉冉萦绕胸际,不胜伤感之至。巴山蜀水,大地悲泣。理性的声音提醒我们,生命终将有离别的一天。感性却更胜一筹,让人难以直面这痛苦的别离。
古往今来,文坛不乏轶闻趣事,友谊颂歌。四川近现代文学史上,便有这样一个作家群体——“蜀中五老”。他们是张秀熟、艾芜、巴金、沙汀和马识途,其中张秀熟年岁最长,马识途最年轻,艾芜、巴金、沙汀“三老”则为同龄。在民间,他们与郭沫若、李劼人又被敬称“七贤”。他们各自独立,彼此成就,是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在各自的创作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为四川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24年,是张秀熟逝世30周年,是艾芜、巴金、沙汀诞辰120周年,是马识途离开我们的第一年……这些时间节点提醒我们,缅怀和致敬既在永恒,更在当下。
张秀熟是“蜀中五老”中的长者,其作品《二声集》《畅言诗录》,如他以风竹为题,著诗言志凝练的“一竿袅袅气凌空,四面风来我挺中。中空自是无穷力,愈是狂飙我愈中”一般,发出不肯向时间低头的“铁汉”之声。其中,《二声集》的序由沙汀和马识途所作。
艾芜、巴金、沙汀同庚。艾芜和沙汀,是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他们在文学路上并肩奋进,被誉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双子星”,后于1992年同月逝世。艾芜以代表作《南行记》首创“流浪小说”书写,开拓新文学创作“边地文学”题材领域的先河,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流浪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艾芜也以此获得“流浪文豪”之誉。
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和真挚的人文关怀,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尤其是他晚期的《随想录》,真实而深刻地映照出一位敢于说真话的作家形象。他不畏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勇于揭露社会的不公,用文字的力量呼唤真理与正义。
沙汀的文学创作生涯丰富多彩。其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就展现出他独特的文学风格。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众多优秀的短篇小说,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绘,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黑暗面。长篇小说《淘金记》更以其幽默诙谐的笔触,揭示了社会的种种弊端。
马识途先后出版了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诗词等大量作品,柔情细腻的《老三姐》、深刻诙谐的《夜谭十记》、波澜壮阔的《清江壮歌》,近年来陆续出版《夜谭续记》《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等新作。他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历史的沧桑,映现着时代风云的家国情怀。
1987年,83岁的巴金从上海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成都,与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欢聚,吟诗作文,相谈甚欢。一行人(艾老因病缺席)来到李劼人的故居菱窠,参观其生平事迹,并在塑像下合影。人事兴衰变倏忽,转眼近四十年矣!五老不在,物是人非。
文艺无边界,刊物重情怀。本着对文学艺术的热忱与执着,和对老文学艺术家的崇敬与感恩,2018年,《现代艺术》重阳节特别献礼推出“寿从笔中来”策划,呈现马识途等9位老者的书画艺术作品及其相关文章,表达对老文学艺术家“鹤算千年寿,松龄万古春”的美好祝愿。(详见2018年10期)2022年,郭沫若诞辰130周年,《现代艺术》特别策划“弘扬沫若文化 谱写时代新篇”专题,遴选130件文艺作品,以此缅怀、纪念、弘扬沫若精神。(详见2022年11期)2024年,110岁高龄的马老离开生养的巴蜀大地,“蜀中五老”天堂再相聚,继续以文学咏叹生命的壮阔与厚重,他们的精神将恒久地闪耀在中华大地。在这里,《现代艺术》围绕他们的生平,梳理其一生文艺轨迹、文艺成就、文艺故事,谨此表达全体杂志人的敬仰和怀念之情。囿于编者个人学识与掌握文献资料,文本难免疏漏,敬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