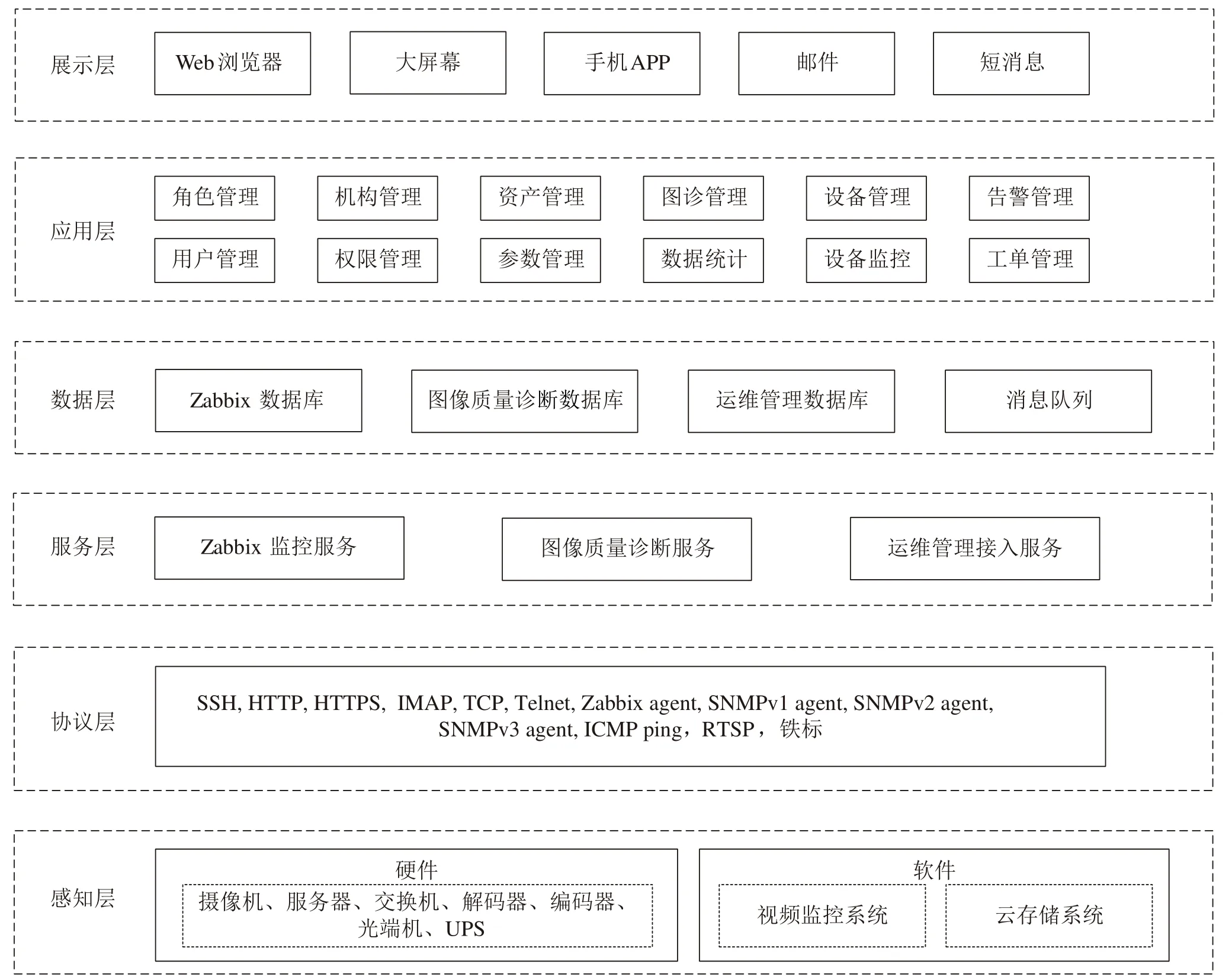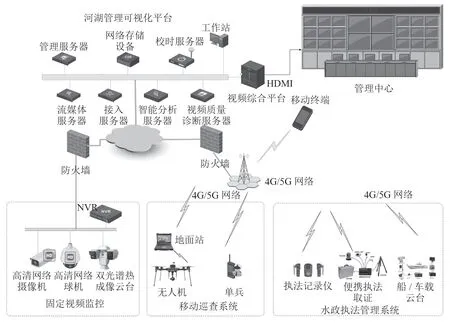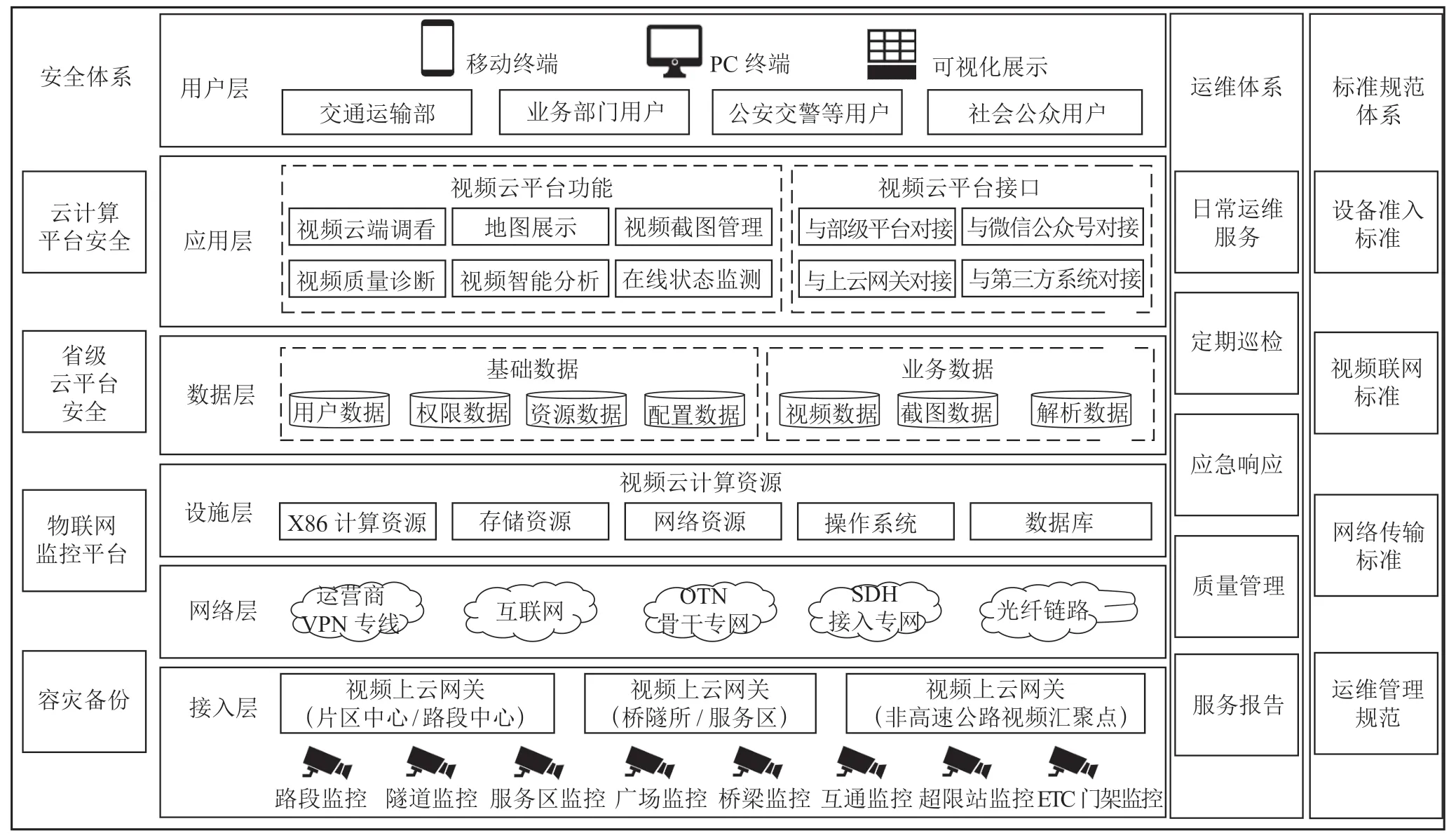摘要 数智时代的“视频化”发展转向对媒体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媒体融合的发展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转变。具体来说,媒体融合的“视频化”转向意味着:在技术之维,媒体融合的数字基础设施转向以“视频化”为主;在形态之维,“视频化”的传播新场景得以搭建;在内容之维,叙事、价值与文化将得到创新发展。在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媒体融合的“视频化”将迎来人机共生、虚实共生、智慧共生的“共生融合”新生态。
关键词 媒体融合 人工智能 “视频化”共生融合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逐渐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达10.74亿,其中移动端网络视听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87分钟,超过3小时,短视频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51分钟[1]。与此同时,ChatGPT、Sora等人工智能大模型由“文生文”“文生图”走向“文生视频”的发展趋势,“短视频+”“微短剧+”的新型传播形态以及广电媒体致力于构建的“未来电视”和“大视听格局”战略部署似乎都预示了一个“视频化社会”的到来[2]。值此巨大变革之际,媒体融合在迈向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新阶段或将向着视频化的方向深度发展,呈现出一种技术、形态、内容多维度互动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共生”“共在”的融合生态。
一、技术之维: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基础
2020年国家明确提出将人工智能作为“新基建”的重要一环,2022年连续发布的《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与《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打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组合拳”[3]。2024年全国两会中,“人工智能+”被首次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有力印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当下及未来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媒体融合正在随着智能技术的变革而出现视频化发展的趋势。
(一)视频化:数智技术驱动下的高维媒介状态
直观来看,“视频化”是以视觉、观看为主的一种媒介形态,并逐渐形成具有统一特征的主流趋势。这个统一特征一方面代表了其本身视觉化的形态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观看的行为特征。“视频化”与先前存在的视觉文化、影像化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发展与形成更多依赖于数智技术。
其一,社会的“视频化”首先依赖技术升维[4]。正如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所认为的数字技术可以整合人类所有的媒介形式,促使其不断地趋向于全息化,数字视频就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高维媒介[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视频化”本身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代表了数字技术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并且,在技术的变革和数字化的形成过程中已经逐渐取代过去的视觉媒介的技术内涵,表现为一种新的技术维度和媒介形态。
其二,在技术升维的基础上,“视频化”来自于智能技术对媒介业态和人们观看习惯的重塑。智能技术对媒介业态的重塑能够促使“视频化”的形成,一方面主要依赖于智能技术本身更倾向于向着视觉呈现的方向发展,比如以“视频生成”“视频合成”“图片生成”等功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促使更加智能、更加高阶的“视频化”维度形成。另一方面主要基于智能技术在媒介中的应用,譬如利用AI生成和制作短视频,或在短视频中加入虚拟数字人等智能化产品,进一步促使“视频化”与智能技术的互嵌。面对技术的升级与进阶,受众不断深刻嵌入“视频化”传播场景就不足为奇。从受众的接触情况来看,“永久在线”与“永久在场”的介入程度早已使人们与可接触到的视觉内容形成“具身互动”,沉浸式地将个体的视觉感官与视频内容相连接;从受众的观看状态来看,虚实融合的视频内容消弭了观看者、现实状况与虚拟视频之间的边界,观看即神经的投射和延伸,在较大程度上促使“视频化”观看习惯的形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视频化”是数智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的技术状态或媒介状态,根植于数字、智能技术,深刻嵌入媒介业态与受众接触媒介的习惯中。也正因如此,“视频化”使得媒体深度融合的数字基建具备充分条件。
(二)新基建:搭建“视频化”的数智基础设施
数智基础设施是指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支撑而形成的一种技术基础设施或智能基础设施,可以作为技术基点运用于媒体深度融合。作为数智时代一种高维度的媒介状态或技术状态,“视频化”将成为媒体融合深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基础设施。
自从以视频生成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问世,已经有多数主流媒体将其作为媒体融合的基础设施纳入到顶层设计和新闻实践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以及上海广播电视台应用于两会报道的AIGC工具Scube(智媒魔方),这些案例表明,“视频化”技术基础为数智时代的媒体深度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资源的整合可能会从媒体间的互通互联转变为整体式的数据“投喂”,抑或媒体内部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创新会进一步优化媒体生产流程。
不过,“视频化”基础设施的搭建并不局限于媒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包括主流媒体的“视频化”平台建设。在“视频化”的影响下,主流媒体的平台建设主要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搭建自由账号平台,诸如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湖南广电、河南广电等主流媒体纷纷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创建优势账号,搭建自有账号平台。二是主流媒体通过建设自有APP渠道,打造了一个覆盖中央及地方的矩阵式的视听传播全平台体系,这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央视频”APP、云听APP,省级广电打造的“芒果TV”“冀时”“百视TV”“四川观察”“大象新闻”等。
“视频化”数智基础设施的搭建从更加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维度促使媒体融合在生产流程、资源整合及自主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迈向以视觉观看为核心的“纵深”发展阶段。可以预见的是,“视频化”技术将加速媒体的生成式转型,重塑媒体融合。
(三)新赋能:“视频化”重塑媒体融合的技术逻辑
媒体融合也是技术融合[6]。在数智技术的推动下,“视频化”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数智基础设施在较大程度上通过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技术赋能媒体融合转型发展。其赋能逻辑主要体现在通过视频生成推动融合生产、搭建“视频化”平台完成资源重整、以“视频化”赋能传播能力提升三个方面。
以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技术推动融合生产旨在将视频生成大模型与媒体生产流程相融合,创新媒体生产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技术赋能生产方面起到了引领的作用,陆续推出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200集动画片《千秋诗颂》,首部AI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话》以及首部AI译制英文版系列微纪录片《来龙去脉》[7],积极探索“视频化”的人工智能在媒体领域的创新应用,也为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媒体融合提供了新的模版。
在创新生产的基础上,搭建“视频化”平台完成资源重新整合是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变化,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值得一提的案例是“央博”数字平台的建设。“央博”数字平台以“用前沿科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定位,重新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优质传播资源、广泛传播渠道、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整合[8],同时以先进技术融合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以数字视觉为主的数字文化传播矩阵,实现技术与资源、媒体与资源的重组,创新媒体融合发展进路。
与此同时,“视频化”技术将抽象内容形象化、可视化、具象化,提升媒体传播能力。比如AI微短剧《中国神话》将复杂抽象的文字描述具象为生动、绚烂而接近真实的影像,满足观看者对神话的想象。如此一来,媒体的创新生产、资源重组以及深度融合等各个方面又随着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形态之维:搭建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场景
从“永久在线”转向“永久在场”,智能媒体融合的视听传播场景化成为新常态。在视听传播领域,人类的听觉与视觉被全面激活[9]。基于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似乎在进一步消弭视听传播领域与其他传播领域的边界,多数传统媒体以及传统的传播形态逐渐向着“视频化”的方向发展,诸如《北京日报》等纸媒也开启了“短视频+评论”的传播新形态,可以说“视频化”正在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态、新趋势、新场景。
(一)从“渠道”到“形态”,媒体融合的“视频化”转向
在媒体传播过程中,传播渠道与传播形态基本可以归属为同一种类,但是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我们可以把媒体传播的“渠道”与“形态”分为两种模式来看,而这两种模式的交替与转换则可以进一步理解媒体融合的“视频化”转向。
“渠道”可以指媒体传播过程中传递新闻信息所使用的媒介,比如传统报纸使用网站发布报纸电子版来实现新闻信息的传递,在这里网站可以被理解为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渠道”。显然,“渠道”具有一定的中介特质,是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种介质或载体。在媒体融合从“相加”到“相融”的进程中,可以将“相加”视为多种媒体“渠道”的组合传播,比如前期的新媒体矩阵、“两微一端”等说法都可以归类为媒体“渠道”的融合发展。而“相融”则离不开媒体“渠道”的进阶发展,也就是说从“渠道”到“形态”。
“形态”可以看作媒体在传播新闻信息时使用到的一种媒介状态或传播形态,这与“渠道”所具有的中介特征有所不同但又紧密相连,“形态”也可以看作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种介质或载体,但区别在于“渠道”更偏重于借助某种载体对新闻信息进行传播,“形态”则偏重于载体与内容的统一与融合。比如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新闻信息,在这里短视频就成为载体与内容的统一形态,它既可以作为一种载体而存在,同时又具备了与载体相统一的内容表现形式。
媒体融合从“相加”到“相融”的发展进程中,由“渠道”到“形态”的变化更多地伴随着“视频化”转向,以至于以视频化的传播形态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比如我们常提到的“短视频+”的融合模式。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0.6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97.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53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96.4%[10]。由此可见,“视频化”正在成为媒体融合的重要形态。
(二)从短视频到微短剧,形态融合与创新发展
短视频是视频的新媒介形态和新内容呈现形式,经过了近10年的发展,已经从初期的零星尝试转向成熟期的“短视频+”[11]。在数字、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之下,媒体融合的“视频化”转向也促使“形态”迅速更新,从“短视频”衍生出“微短剧”,推动媒体的形态融合与创新发展。
“短视频+”是媒体融合进程中“视频化”转向及形态融合的典型案例。《北京日报》就是在这样的进程中创立了“新闻我来说”融媒体工作室,并推出“短视频+评论”的新形态,旨在将短视频形态与传统纸媒的新闻评论内容相融合,不仅让新闻评论在新的传播形态中大放异彩,还使短视频获得增益效果。此外,“短视频+直播”“短视频+知识”“短视频+政务”等传播形态的出现不断推动形态融合和创新发展,可以说在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形态之维,短视频发挥着重要作用。
短视频经历了持续而快速的发展之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2],其传播形态也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革新而重塑与改写,微短剧在形态融合与创新发展的助推下由短视频衍生而来。从传播形态来看,微短剧是短视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除了具备短视频的形态特征外,还具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梗概和戏剧性的剧情情节,这使得其在内容承载方面较之短视频有更多的包容度和创新性,能够承载意涵深刻、情绪饱满的内容。微短剧的出现也在传播形态上进一步为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添砖加瓦。
(三)从微短剧到社会生活,媒体融合背景下的视觉场景融合
微短剧刚进入大众视野之时是以快速反转的剧情和戏剧冲突性较强的情节而获得青睐的,随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先后出台《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等政策措施,微短剧的发展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专业化、精品化的道路。微短剧延续短视频在媒体融合中的重要作用,以新的形态特征助力媒体深度融合,“微短剧+”成为当下及未来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趋势。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当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的“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该计划不仅掀起了一场“微短剧+文旅”的浪潮,也加速了媒体与社会生活的深度互嵌。其一,“微短剧+文旅”的融合模式以新的传播形态承载丰富的文化内容,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可见性使其得以广泛传播,河北广电局首映的《等你三千年》,河南广电局计划推出的《“洛”花如有意》《天青色等烟雨》等微短剧都将地方文化特色融入剧情情节中,使得城市特色、文化元素透过微短剧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其二,“微短剧+文旅”的融合模式增强了观看者的视觉体验,让乡情可见,文化可感。譬如微短剧《我等海风拥抱你》让观众感受了福建省泉州市惠安新渔村民俗与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惠安新渔村。其三,“微短剧+文旅”的形态模式增加了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更多可能性,微短剧《别打扰我种田》带动了地方文化旅游行业发展的同时,还通过将甜宠题材融入乡村故事创新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不难发现,从形态维度观察媒体融合的“视频化”发展逻辑,可以看到一种由媒体搭建起来的视觉与社会生活场景的融合关系。视频形态建立起观看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视觉桥梁,并邀请观看者在进入“视频化”传播形态的同时,深度沉浸于视觉的感官体验中,进入由媒体构建的视觉场景之中。其中,“视频化”的媒体内容则是与传播形态不可分割的重要维度。
三、内容之维: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重心
内容是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重要维度。在这里内容这一概念的范围限定在主流媒体生产制作的产品内容、作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信息、融媒体作品等。乍看似乎没有太多说服力,因为内容在媒体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处于重要地位,不过在以“视频化”为数智基础设施的背景下,内容有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视觉感官内容成为媒体生产的关键,这为媒体创新生产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使内容生产的难度增加;另一方面,视觉内容可能对观看者的情绪、态度和思维等产生深刻影响,这使得媒体规范与引导内容生产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在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进程中,内容之维的逻辑重点在于创新叙事、传播文化和壮大主流价值等三个方面。
(一)技术与审美:视觉感官下的叙事创新与融合
在数智技术背景下,媒体融合的“视频化”发展离不开技术与审美两个重要因素。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智能技术,特别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等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内容叙事的过程中,可以说创新媒体内容叙事数智技术是关键。从审美角度看,在视觉感官之下,可观、可见的内容大多都与审美有关,这意味着在“视频化”的背景下创新叙事更多地依赖于审美。因此在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内容之维,创新叙事就是要实现技术叙事的创新和审美叙事的创新。
技术叙事的创新并不是从数据、代码或编程的角度探讨技术的形成与应用,而是从技术功能的角度探讨人工智能运用于内容创作对叙事产生的影响。譬如北京广播电视台在重点节目《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130个瞬间》中通过“AI智能辅助制作”训练AI绘画模型,生产符合节目调性的版画风格动画,使得技术亮点成为节目叙事亮点之一。同时,在《2024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北京广播电视台应用自主研发的AI视频互动小程序“龙年AI就福你”,开创AI代言的创新叙事模式[13]。可见,技术叙事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视觉化叙事的优势,将人工智能的技术点转换为节目内容的创新点或视觉叙事的关键点,进一步完成新技术与新叙事的融合,从而实现叙事效果最大化。
审美叙事的创新可以从两个主要层面来探讨,一是技术审美层面的叙事,二是结构审美层面的叙事。技术审美层面的叙事主要由人工智能技术的视觉化呈现来实现,比如AI微短剧《千秋诗颂》中通过技术训练使人工智能大模型充分理解“国风、唐代、写意、工笔画”等文化词汇,生成工笔、水墨等国画风格的美术素材,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诗词的意境美感[14]。结构审美层面的叙事则是通过适应短视频或微短剧等新传播形态,重塑审美的时间、空间,在当前“视频化”的审美环境中进一步完成瞬间美学和场景美学的塑造,达成令人耳目一新、情感迸发的叙事效果。
(二)流量与质量:“视频化”背景下主流价值的引导与融合
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内容逻辑中,流量与质量是两个关键因素。如今,流量似乎逐渐成为衡量内容好坏的重要标准,通俗来讲,流量高的内容说明颇受观看者喜爱,流量低或没有流量的内容则无人问津。这使得在内容生产与制作环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唯流量”而不“唯质量”的问题。不过,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流量与质量的融合才是内容生产突破“唯流量”困境,提高内容品质的发展之道。而让流量与质量相融的关键则在于用主流价值“驾驭”流量,让主流价值成为内容生产的核心理念、重要导向和主要素材。
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借助“玉壶回国”这样一个拟人化的小叙事,将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等主流价值融入其中,以细腻、平实的手法展现了爱国、团结、友善的价值观念,使得该微短剧的内容有了强大的精神价值和饱满的情感内核,成为拥有较高流量的优质作品。此外,微短剧《大过年的》《超能坐班族》《我的归途有风》等等则是以主流价值为重要价值导向,做到流量与质量相得益彰。
可以说,主流价值对于流量与质量的“两手抓”,不仅能够让内容的生产与创作以质量为先,流量为后,同时引导流量向着优质内容“流动”,还能够从根本上为内容生产与制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正向的情感能量。
(三)本土与出海:全球视野下的文化融合与传播
在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内容维度中还有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文化。换言之,在媒体融合“视频化”内容生产与制作过程中,文化内容或文化叙事是主要素材。这其中既包含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在内容中的注入,也包含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在国际中的传播。
2024年初,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牵头推出的“跟着微短剧去旅行”计划就是本土文化注入融合内容的典型案例。比如,邯郸市丛台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出的《邯郸梦之AI在战国》微短剧讲述了女主人公在一次偶然的VR体验中“穿越”到战国时期的奇妙故事,将邯郸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15]。一方面,“穿越”等剧情情节很容易融入地方特色文化或地方文化理念,另一方面,代表地方文化的特色元素,比如古城墙、民俗、特色景点以及风土人情等也将作为内容的一部分呈现出来。
除此之外,本土文化融入内容生产再借由“视频化”转换得以广泛传播的融合过程也不仅仅带来文化在国内广泛传播的结果,还带来了本土文化在国际广泛传播的良好效果。比如“2023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中,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报送的《借助民间体育赛事 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以“村BA”“村超”传播为例》立足当地富有魅力的人文生态,通过“民间球赛”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叙事“小切口”,用视觉化的方式深刻而饱满地反映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后,“乡土”中国的生命活力[16]。由此可见,在媒体融合“视频化”发展的未来,本土文化的对内对外传播,也可以通过一种在全球视野下的文化内容的视觉融合来实现,而这种以视觉化的本土文化内容来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将成为重要趋势。
四、生态之维:从“媒体融合”到“共生融合”
媒体融合的“视频化”转变正在逐渐改变媒介生态和传播生态。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下,“视频化”转向带来的不仅是媒体融合在技术、形态与内容上转型和突破的“小融合”,更是建立在思维、制度、文化、关系基础上的“大融合”。“视频化”发展将推动“媒体融合”迈向“共生融合”生态,这意味着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更加深刻,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更加模糊,全方位可视、全社会为媒的智慧生态正在形成。
(一)人机共生:互动关系的融合与重塑
诸如ChatGPT、虚拟数字人、采访助手、人工智能合成主播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深刻改变了媒体的传播形态、内容生产模式等等,人机互动特征显着并成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这也为媒体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人机融合[17]。“视频化”的到来则进一步推动人机关系由融合进阶为共生。
一是自动化文本生成进阶为自动化视频生成,增强了原本的实时性、动态性和具身性。在自动化视频生成的驱动下,多元主体、时空同步成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新型要素,人脑生产的抽象素材投喂到人工智能后,经由数据库的结构化转换而自动生成机器叙事风格[18],这个过程完成了人类思维的机器呈现,再投入使用和传播,除了提高生产效率节省人力之外,由人输入,由机器生产再由人观看的类似“自循环”的“共生系统”已然初具其型。
二是虚拟数字人的积极探索与广泛应用加速了人机共生。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小妮”,抖音平台推出的虚拟美妆达人“柳夜熙”,还有虚拟主播节目《AI主播说两会》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虚拟数字人,从中已然可以看出人机互动融合的特征。随着“视频化”发展的更加普遍和深入,虚拟数字人将可能成为更多人身体的视觉化投射,人类与媒体、人类之间的交流也可能通过一种“视频化”的有着“视觉生命力”的数字人来完成,从而形成人机共生的“视频化”生态。
(二)虚实共生:时空边界的消弭与融合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进一步赋能媒体融合发展,虚拟和现实的边界逐渐被打破,传统的时空维度在虚实融合的数智背景下被重塑,在“视频化”发展的未来,虚拟与现实的时空边界将进一步消弭,形成一种虚实共生的融合状态,新感知、新关系、新场景的多维新生态系统将会逐渐形成。
“视频化”发展带来的新感知、新体验推动虚实融合向“共生融合”发展。一直以来“临场感”是新闻传播实践所追求的目标,VR、AR、MR、XR,抑或“元宇宙”都在不断拓展人们的视觉感知体验,“我看故我在”[19]。比如元宇宙以多元数字技术还原线下交往场景,让受众利用虚拟数字人形象在虚拟空间进行交往,又或者受众通过景区的AR或VR技术沉浸式体验自身与历史文化的共在。虚拟与现实、在场与临场、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就在这样的感知体验与视觉互动中不断消弭、融合并走向共生。
“视频化”发展的新技术带来虚实共生的新趋势。在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出现之后,Open AI就展开了构建世界模拟器的蓝图,这也使得虚实共生的新趋势成为可能。在Sora的功能里除了更长的生成时间能力、更自由的视频尺寸剪辑能力以外,还具有向前或向后扩展视频的能力以及模拟真实物理世界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虚拟与现实边界消弭的可能性。
(三)智慧共生:全社会为媒的融合生态
在数字、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驱动下,媒体融合的“视频化”发展也势必会随之向着更加智能乃至智慧的方向深入。随着“视频化”社会的来临以及“大融合”“大视听”局面日渐形成,媒介似乎在人们的视觉感知中消失和隐退[20],取而代之的是智慧的生活状态以及全社会的视觉化连接。从人机共生到虚实共生,“视频化”正在推动一种“全社会为媒”的融合生态的形成。
视频是连接社会的界面。随着视频的技术、制作、观看与使用逐渐成为主流,媒介将进一步隐匿在社会中,转而以视频的形式存在和传播,视频则成为连接社会的界面。比如实景三维技术打造的现实世界的三维空间,以视频的形式在人、三维空间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融合关系,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推出的《三维地图新闻〡万里长江无限情》《实景三维+可视化仿真〡看“神十七”飞天之路》等融合报道都在一定程度上使观看者“身临其境”[21],这种感知正是“视频化”发展带来的“超时空感”。在这个过程中,观看视频的人、视频界面、三维空间和现实空间都互为连接、互为媒介。
全方位可视、全社会为媒的智慧生活将成为新的融合生态。例如,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暖城记”公益节目联动社会资源搭建了一个技术支持、媒体推动、城市为媒、视频传播的系统化、智能化的公益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户外工作者、休息驿站和制作播出的节目都可以视为一种媒介,互相连接、相互融合。
结语
当全面“视频化”来临的时刻,媒介将以全方位可视的形态呈现,技术、内容与形态的多维互动将推动“融合”走向“共生”,人与人、人与视频、人与社会等都将成为麦克卢汉当年断言的媒介的延伸,成为智慧融合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未来,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模拟的分类可能会被可能与不可能、具体与抽象所代替。
参考文献:
[1]德外5号.网络视听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市场规模超万亿[EB/OL].(2024-03-29)[2024
-06-01].https://mp.weixin.qq.com/s/eFPGZ4tn54
GGEAwwSgrvJw.
[2][4]孙玮.“视频化社会”的来临:从ChatGPT
展望媒介通用性变革[J].探索与争鸣,2023(12):55-62.
[3][11][17][18][19]殷乐,葛素表,林仲轩等. 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2-202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5-45.
[5]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73.
[6]赵琪.媒体融合的新方式和新影响[EB/OL].(2024-01-29)[2024-06-01].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1/t20240129_5730990.shtml.
[7]德外5号.AI加持“新质生产力”,第一批“广电版Sora”实践来了花Young洞察[EB/OL].(2023-03-19)[2024-06-01].https://mp.weixin.qq.com/s/MEbYwlS-s9BNb0HKjNzK5w.
[8]中央广电总台总经理室.总台“央博”数字平台2024年重点项目发布仪式在京举行[EB/OL].(2024-01-16)[2024-06-01].https://mp.weixin.qq.com/s/TwdYY1WnE_csFq3uVf6lbw.
[9]殷乐.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EB/OL].(2024-02-29)[2024-06-01].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amp;iid=6768amp;eid=48449amp;sid=224249amp;idate=12_2024-02-29.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3-02)[2024-06-01].https://www.cnnic.net.cn/n4/2024/
0322/c88-10964.html.
[12]祝燕南.短视频发展格局与趋势思考[J].传媒,2024(4):13-15.
[13][14]德外5号.AI加持“新质生产力”,第一批“广电版Sora”实践来了花Young洞察[EB/OL].(2023-03-19)[2024-06-08].https://mp.weixin.qq.
com/s/MEbYwlS-s9BNb0HKjNzK5w.
[15]民生大视野.跟着微短剧游河北 邯郸梦之AI在战国[EB/OL].(2023-05-21)[2024-06-08].https://mp.weixin.qq.com/s/zBXeuz8VhrJJlnrU-BxFzA.
[16]霍瑶.“2023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发布[EB/OL].(2024-05-31)[2024-06-08].https://mp.
weixin.qq.com/s/KbPuBwRHdc5EjqCWKxyHag.
[20]胡翼青,赵婷婷.作为媒介性的具身性:对具身关系的再认识[J].新闻记者,2022(7):11-21.
[21]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虚实融合?智能技术如何引领新闻样态革新[EB/OL].(2025-05-30)[2024-6-8].https://mp.weixin.qq.com/s/z5RMrLeR
UX4ZFOGCgItG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