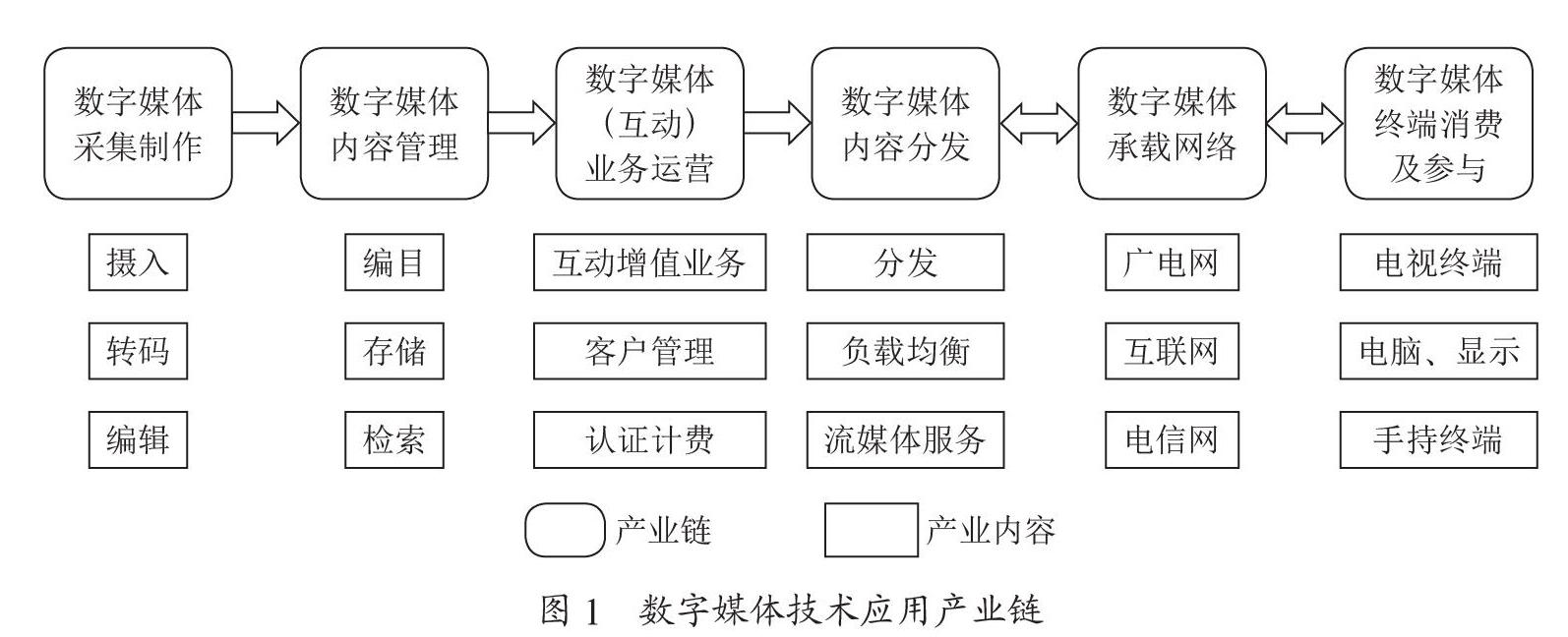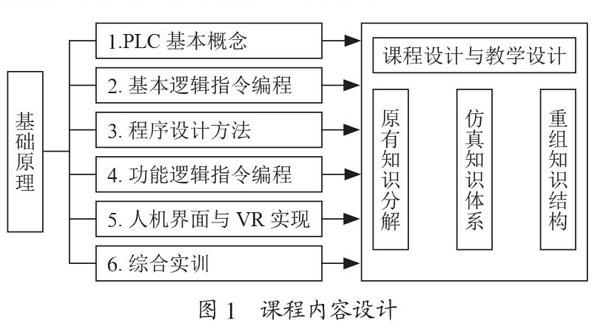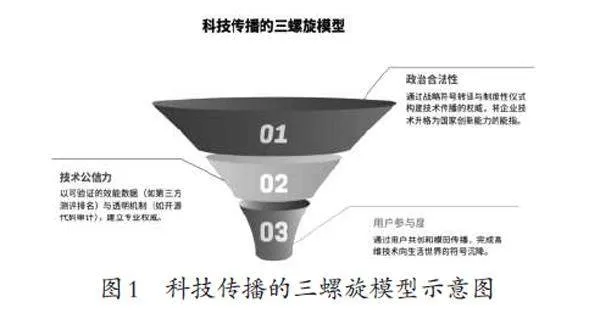【摘要】“技术想象”打开了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未来面向,近年来日益引起国内传播学界的关注。然而,其含义仍显模糊,“社会技术想象”这一被广泛应用于相关研究中的概念工具也面临若干理论困境。预期社会学理论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聚焦于传播活动本身的理论视角,以捕捉技术想象。在这一框架下,“技术预期”概念可以有效连接符号的媒介话语和现实的媒介实践。将“技术预期”引入传播学研究,不但能够拓宽技术想象研究的边界,还是一条经由传播现象捕捉技术想象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技术预期;技术想象;社会技术想象;预期社会学
一、引言
“乐观的年代”是30年前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一书结语的标题,随后它便照进现实,在互联网掀起的全球性技术潮流中拉开序幕。彼时,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社会。30年后,学者们在对互联网的失望中审视和反思先前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的论断,尼葛洛庞帝也写道:“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1]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乐观的年代”虽已落幕,《数字化生存》中对数字社会的许多想象已经成为如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
在技术与社会的交界面上,想象与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是想象先于现实出现,还是现实先于想象发生,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将想象视为一种认知,该研究范式将技术视作具有自身演变逻辑的纯粹事实性领域,默认技术想象随着技术创造的客观现实而不断发生改变。基于此,新兴技术在特定国家和社会中的创新、扩散、使用和影响得以被精确地测量和揭示。与之相比,建构主义的诠释研究多持文化视角,认为技术的现实与想象在社会成员集体编织的意义之网中互相建构。该研究范式将科学技术看作一个社会领域,技术既是“人类劳动、投入、选择和设计的历史产物”[2],也是与政治经济等宏观社会结构相互勾连、对人类生活施加可观影响的社会力量。技术想象是后者的关键面向之一。然而,尽管被广泛提及,“技术想象”仍然是一个相对宽泛和模糊的概念,这不利于我们对相关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检视。一个社会中的技术想象究竟源于何处?内嵌于技术想象中的未来图景何以形成?对技术性未来的想象如何影响当下的技术与社会进程?上述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发问,媒体与技术想象的关系是什么?传播学研究如何捕捉技术想象?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引介“技术预期”(technological expectation)这一预期社会学(sociology of expectations)的核心概念,在加深对技术想象认识的同时,拉近传播学研究与技术想象的距离。
二、何为“想象”:区分“imagination”与“imaginary”
何为“想象”?迄今为止,这一概念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均得到了历时长久的关注与讨论,已有众多学者对现代社会中出现过的多种想象进行了书写。本文并不拟对相关定义进行回顾整理,而是试图沿着科学技术研究的脉络展开回溯,回顾与技术想象直接相关的重要定义。在包括国族想象、文化想象等在内的诸多类型的想象中,社会想象与技术的关联最为密切,原因是科学技术研究所言的技术想象通常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由社会制度所塑造,并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持有。
中文学术讨论中的“社会想象”,在英文语境下对应“social imagination”和“social imaginary”这两个存在细微差异的概念。因此,本文有必要首先对两者作出区分。具体而言,“imagination”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既可以在个体层面发生,成为某个人的想象,也可以在主体之间发生,成为集体想象。当后者连接起社会成员、为共同体所共享时,则成为“social imagination”。与之相比,“imaginary”是一系列社会成员之间共享的观念、思想、价值和规范,它只存在于集体层面。“social imaginary”最早由查尔斯·泰勒提出,并将它定义为:“一个社会中广泛共享的普通人想象他们社会存在和社会环境以理解和建构现实的一种方式”[3],区别于学者们以理论术语表达的社会理论。据此观点,“social imaginary”通常存在于社会大众之间广泛流通的图像、故事、传说之中。可以说,“social imaginary”相关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理解“social imagination”这一社会实践的理论化尝试。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确认,前文所述的技术想象属于“imagination”的范畴。它是技术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一种集体性社会实践,社会成员出于对新兴技术产生认知的需要展开对它的想象。技术想象并非先于人的社会经验发生,它是在人与技术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出来的。同时,技术想象也并不拥有固定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更不是完全由技术特性所决定,它是流动和变化的。在此,想象什么和如何想象,是技术想象研究需要处理的两个核心问题。在西方,此类研究出现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国内传播学界对技术想象的讨论则是在2020年以后,相关研究在“技术想象”“社会技术想象”“技术的社会想象”“社会科技想象”等多个核心概念下进行。其中,“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y)是目前在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发展相对成熟,且在海内外传播学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工具。下文将技术想象实践置于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脉络中进行梳理。
三、想象什么:社会技术想象研究
“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谢拉·贾萨诺夫和韩国汉阳大学的金圣贤于21世纪初提出,并在他们的大力发展下逐渐成为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在最新的定义中,贾萨诺夫将社会技术想象定义为“集体持有的、制度化稳定的、公开表现的、令人向往的未来愿景,它由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所驱动,且这些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提升实现,并进一步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4]。“社会技术想象”属于“imaginary”的范畴,该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理论的发展是对技术想象这一社会实践的理论化尝试。
社会技术想象研究是通过剖析凝结在技术想象实践中的未来愿景,探讨人们在不同历史和社会语境下进行科学技术活动的具体方式,重点观察、评估和审视科学技术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共生(co-production)关系。那么,从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视角看,技术想象中的未来图景源于何处?社会技术想象理论认为,建立新的技术性未来的努力通常根植于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愿景,“令人向往的”是社会技术想象的基本特征。依据上述定义,社会技术想象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所驱动,它“不仅与事情通常如何进行的认识有关,还与事情应该如何进行的理念有关”[5]。也就是说,社会技术想象包含事实性和规范性两个层次,事实性的共同理解主要指对科学技术发展可以在未来实现的种种可能的认识,规范性的共同理解包含对社会生活中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因此,从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视角看,技术想象实践集体持有的未来愿景产生于社会成员对技术能力和社会秩序双重构想的交叉点上。
“制度化稳定”(institutionally stabilized)是社会技术想象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它是指社会技术想象往往经过长时间积淀,在其社会语境下占主导地位,且有能力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也就是说,获得制度保障是形成社会技术想象的关键一步,社会技术想象理论认为,国家和政府在其中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贾萨诺夫将社会技术想象理论置于政治学的国家认同理论和科学技术研究对社会技术系统的研究这两条学术脉络的交会处。延续政治学的研究旨趣,社会技术想象的提出最初被用来分析科学技术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后来延伸到科技创新与政治文化、地缘历史等其他方面的互动上。
互联网进入中国社会已逾30年,尽管许多研究尚未直接使用“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工具,但中国社会对互联网技术的社会技术想象之轮廓在传播学研究中业已浮现。例如,吴靖和云国强两位研究者通过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信息社会”话语的变迁,发现中国社会对互联网技术的想象与国家自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愿景紧密交织在一起[6]。一方面,对互联网技术的社会技术想象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另一方面,在文化和政策共同塑造下的中国互联网技术又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可以说,从社会技术想象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在吸纳互联网技术过程中在不同历史和政策语境下“想象什么”的问题已经在传播学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
四、如何想象:预期社会学与技术预期
“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自身存在诸多局限[7]。首先,“社会技术想象”是一个后验概念,并不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技术潮流,因为依据社会技术想象理论,它的形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者只能在其被某一社会广泛共享并且获得制度支持后进行回溯性分析。其次,“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只适用于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强大影响的技术,并不适用于失败的、被遗忘的、小众的技术,因为这些社会可见度较低的技术往往无法激发社会成员集体持有的社会想象。最后,社会技术想象研究擅长对某一社会在技术想象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未来愿景进行全景式的宏观勾勒,它虽然强调权力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是难以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捕捉其运作的动态、具体的过程。
传播学是一个对新兴技术颇为敏感的领域,特别是传播技术革新所引发的新现象亟待被传播学者系统地揭示。其中,对正在进行的技术潮流的理解、对低社会可见度技术的关注,以及对技术想象实践过程更加细致的观察皆是传播学技术想象研究的重要面向。然而,囿于上述“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自身的局限,不少研究在使用它时不得不对其进行模糊化处理以适应讨论现实问题的需要,从而在经验材料收集、研究对象择取、分析层次设置等方面出现了与原理论程度不一的错位,损失了不少分析的精度与准度。基于此,为了给突破上述技术想象研究的概念困境提供思路,本文引介一条新的概念路径——“技术预期”。
(一)技术预期的内涵
“技术预期”这一概念出自预期社会学,该领域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并在21世纪初获得关注,近些年逐渐发展为科学技术研究的子领域之一。学者尼克·布朗、哈罗·范·伦特、延斯·贝克特是该领域的代表人物。预期社会学关注未来的预期特别是对特定科学技术的预期,如何被创造和发展、获得注意力或快速消失,如何影响当下商业决策、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等等。
预期社会学认为,科技创新创造了不可知的未来,一切对这个未来的看似知晓实际上都是非事实性的预测。正是在看向未来的这一过程中,人们对技术的机遇和风险进行集体性的讨论、认知和想象,以共同面对和尝试处理技术所创造的未来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技术预期”是预期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伦特将预期定义为“以口头或文本形式在社会中流通的对未来的陈述”[8];具体到“技术预期”,马兹·鲍鲁普等学者认为,“虽然一般形式的预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未来的期待状态,技术预期可以更具体地被描述为对特定技术在未来的技术能力和所创造的技术情境的当下呈现”[9]。上述预期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论点和“技术预期”的概念定义表明:技术预期是社会性的,它并非个体想象,而是集体持有;它是被建构的,并非先于人的社会经验存在,而是在现实的社会过程中被创造、传播、发展和调适。这与技术想象研究的理论预设基本一致。
(二)技术预期的产生与建构
技术预期源于何处是预期社会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的理论认为,技术预期产生于特定社会语境下参与到新兴技术创造和发展过程中的多元社会群体的关系和网络之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投资者和商人、国家和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技术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公众也参与到对新兴技术的讨论中。面对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上述社会群体和组织常常持有差异化的技术预期,获取与技术相关的知识和信息能力的差异是造成技术预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差异化分布的关键因素。例如,有学者主张,与技术使用者相比,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在直接参与技术知识生产的人和技术批评者那里更加尖锐[10]。
技术预期的建构存在于它的流通过程之中。首先,预期社会学认为,技术预期具有流通性,它既可以通过口头表达和文本等象征性形式,也可以通过行动、身体、材料、机器等物质性形式在特定群体和组织甚至全社会范围内流通。在符号层面,媒体是其重要的流通渠道和场所之一。其次,这些产生于社会群体和组织内部的技术预期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社会成员共享决定了它的影响力,而这一在更大范围内被共享的能力与其生产者在社会权力结构的位置紧密相关。其中,掌握越多社会资源的生产者越有可能将其所持的技术预期投射至整个社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共享并不等同于接受和相信,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使用。这也就意味着,在同一社会语境下,不同社会行动者持有的对同一技术的预期常常在碰撞、协商和竞争之中争夺在技术想象实践中的优势地位。那么,为什么参与到技术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和组织要建构和推广其所持的技术预期呢?这与技术预期的现实功能有关。预期社会学给出的解释是,技术预期会生成一系列现实中的功能和效应、引导与技术相关的社会活动,比如为特定行动者的技术活动提供合理性、吸引关注和投资、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等。可以说,技术预期是一个“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它不仅仅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表述,更是改变和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它可以通过引导人们的行为使自己成为现实,进而证明其自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不仅如此,技术预期的发展过程还在时间上呈现出了特定模式,并在对于多种技术的想象实践中反复上演。预期社会学在经验研究中发现,技术预期有着从诞生、发展,到完善、蓬勃,再到减退、衰落,最终消逝的完整生命历程。不少技术的预期都出现了“炒作与失望的循环”,即新兴技术面世之初通常伴随着强调其新颖性和革命性的大肆宣传和夸张炒作,往往在它获得了足够的关注、动员了充足的资源、进入社会发展主流议程后,其他更详细和具体的观点和讨论才会浮现。在时间的推移中,随着该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当人们回顾过去对它的期望时,往往会产生由过去的预期与当下的现实大相径庭而引发的失望。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预期中由话语勾勒的未来脚本暂时稳定、持续流动,对于技术本身和发展方向的叙事也相应地随之发生改变。从预期社会学的视角看,前文提及的最初对于互联网技术乐观主义的判断与当下的反思与失望恰好可以用该模式来加以解释。
(三)比较技术预期与社会技术想象
与社会技术想象相似,技术预期也聚焦于技术想象中产生和形成的未来图景,以及它所折射出的生活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下的人们对某一科学技术的意义建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技术预期更侧重于回应技术想象实践中多元社会行动者“如何想象”这一过程性问题。它与“社会技术想象”在概念内涵上存在以下两点差别。
首先,与“制度化稳定”社会技术想象不同,技术预期并不仅仅指被社会制度保障的主导性未来图景。预期社会学认为,技术预期的类型是多样的:它既可以宏观地概括未来蓝图,也可以详细地勾勒单一元素;既可以侧重政治、商业、社会的某一侧面,也可以将它们混合起来;既可以进行不容置疑的预言陈述,也可以对其他预期进行反驳与抵抗。也就是说,技术预期既有稳定成型的也有初现萌芽的,既有暂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有相对边缘的,既有获得制度支持的也有另类和草根的。
其次,与社会技术想象不同,技术预期并不预设技术想象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未来图景都是“令人向往”的。社会技术想象所言的未来图景是愿景,是社会成员出于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种种设想和追求产生的理想化的未来。与之相比,预期社会学并不预设技术预期中包含特定公共价值的追求,而是将未来视为一个“争议性范畴”,它被谁、如何、在什么条件下创造、建构和管理,是分析技术想象中权力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也就是说,技术预期并不包含“社会技术想象”概念所强调的规范性维度,也不涉及技术伦理,更鲜有涉及社会道德,只在泰勒所说的社会想象的事实性层面进行,致力于揭示技术想象实践之中围绕技术性未来展开的真实、具体、动态的社会过程。
上述概念内涵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在作为概念工具时,“技术预期”与“社会技术”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具体而言,早期的社会技术想象研究注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比较分析和长时间跨度的历史分析;之后,从有权力的个体到社区和公共组织,从国家到全球的多层次治理主体才逐渐被纳入此概念的分析范畴之中。相应的,由于技术预期在社会中的共享程度与范围不一,相关研究多以包括实验室、研究社群、公共组织、商业公司、政府机构等规模不一的群体和组织为分析单位,鲜有进入国家和全球的分析层次的。与之相比,技术预期的研究设计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在符号和象征层面进行,旨在考察特定技术预期的符号建构,例如分析其修辞和隐喻;另一种在现实层面进行,旨在考察特定技术预期如何参与并影响产品研发、政策制定、公众认知等具体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两种不同概念路径的研究中,媒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于社会技术想象研究而言,媒体再现着社会技术想象,是技术想象实践中文本的生产者,因而是经验材料的来源之一。然而,出于对科学技术与政治体制这对关系的重视,社会技术想象研究更加关注司法实践及法律条文、政策实践及政策文本,媒介文本通常仅作为补充性来源使用。与之相比,对于预期社会学研究而言,媒体是专业知识转译为大众信息的场所,正是经由媒体转译,技术预期才可被公众消费。此外,媒体也是各群体和组织推广其技术预期的传播渠道,媒体的报道、再现与传播是为特定技术预期积累价值的过程。换言之,在符号和象征层面,媒体是技术预期文本的核心来源;在现实层面,它是参与技术发展过程的社会组织。由此观之,预期社会学理论为传播学研究捕捉技术想象提供了一个聚焦于传播活动本身的理论视角,其中“技术预期”这一概念能够有效地连接起符号的媒介话语和现实的社会行动。
五、结语
在过去的30年中,从赛博空间、万维网到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人们通过技术想象来理解和认识互联网,并基于这些技术想象,在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各个层面展开相关的技术行动。与此同时,新兴的技术潮流不断涌现,在传播学研究中,对于平台想象、算法想象、人工智能想象的研究陆续展开。本文将技术想象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一方面,认识和分析技术想象需要持续的理论化尝试和有力的概念工具;另一方面,目前在传播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社会技术想象面临概念困境:它虽然善于回答“想象什么”这一问题,但是并不善于跃入当下正在进行的技术潮流。不仅如此,媒体并不处于该理论聚焦的核心位置。
那么,立足于目前的研究现状,传播学研究可以如何使用“技术预期”这一概念工具来捕捉当下技术潮流中的社会想象?本文提供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一方面,对于技术想象研究内部而言,预期社会学提供了一个与社会技术想象理论不同的理解技术性未来的社会学视角。沿循“技术预期”这一概念路径,社会技术想象研究所强调的技术观念、思想、价值和规范被淡化,参与到技术想象实践中各个群体和组织之间出于各自动机对新兴技术采取的具体行动得以被照见。不仅如此,技术预期所适用的研究层次和对象十分灵活,无论被探讨的技术预期所共享的范围是大是小,技术本身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主流的还是小众的,皆可作为分析的对象。
另一方面,从外生性角度来看,技术预期还可以在技术想象研究与传播学其他研究主题之间建立关联,本文提供两个相关子领域作为例证。第一个是媒介记忆研究,与技术想象研究关心传播技术的未来类似,媒介记忆研究关注传播技术的过去,两者都穿行在技术与社会交界面的时间轴上。从预期社会的视角看,技术预期的生产和建构涉及其持有者对过去和未来的调用,因而技术预期可以应用于媒介记忆与技术想象两条学术脉络的连接点上,探讨在媒介这个技术预期的建构和流通场域中,特定的技术预期如何“追溯过去想象中的未来”和“展望未来回溯中的过去”。第二个是新闻社会学研究,新兴技术与新闻业的相互形塑一直以来都是新闻社会学的重要关切,科学技术研究的引入业已为该领域作出重要贡献[11]。“技术预期”这一概念工具可以用于分析记者群体对新兴数字技术的感受和认知,以及它如何进一步影响新闻报道的惯习和媒介组织对新技术的采纳和使用,以深入探讨技术与新闻业的互动。
最后想要指出的是,“技术想象”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术概念,它汇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共同探讨技术和社会互动的未来面向,激发着他们无穷的理论创造力。本文并不认为“社会技术想象”和“技术预期”这两个概念存在优劣之分,相反,它们只是在缘起、内涵、侧重和适用条件上存在差异,都是科学技术研究中目前相对成熟且极具潜力的概念工具。不仅如此,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充、弥补彼此的视野盲区,尤其是在分析同一技术时,它们使研究者可以从双重理论视角同时思考“想象什么”和“如何想象”这两个技术想象实践的核心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概念启发我们,技术并不是一个脱离于人类主体性的纯粹客体,人们的技术想象实践深深嵌入在其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之中,其中产生的预期、文化和价值追求又反过来加入人类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这进一步阐明,作为集体的人始终都是技术潮流的真正推动者,技术可以创造的未来从来都不止一个,“另一个未来”始终存在。
参考文献:
[1]胡泳.尼葛洛庞帝之叹:打造“互联网公地”的探索[J].新闻记者,2017(1):56.
[2]Felt U,Fouche R,Miller C A,Smith-Doerr L.Introduction to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Felt U, Fouche R,Miller C A,Smith-Doerr L.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4th ed.London:The MIT Press,2017:1.
[3]Taylor C.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4]Jasanoff S.Imagined and Invented Worlds[M]//Sheila J,Sang-Hyun K.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2015:4.
[5]Taylor C.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24.
[6]Wu J,Yun G.From Modernization to Neoliberalism? How IT Opinion Leaders Imagin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J].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18,80(1):7-29.
[7]陈秋心.“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边界与适用范围辨析[J].新闻记者,2024(4):18-30.
[8]Van Lente H.Navigating Foresight in a Sea of Expectations:Lessons From the Sociology of Expectations[J].Technology Analysis amp; Strategic Management,2012,24(8):769-782.
[9]Borup M,Brown N,Konrad K,Van Lente H.The Sociology of Expect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Technology Analysis amp; Strategic Management,2006,18(3-4):285-298.
[10]Brown N,Michael M.A Sociology of Expectations:Retrospecting Prospects and Prospecting Retrospects[J].Technology Analysis amp; Strategic Management,2003,15(1):3-18.
[11]白红义,程薇.作为“科学标签”的新闻社会学:起源、复兴与巩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3):20-38+126.
作者简介:满子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