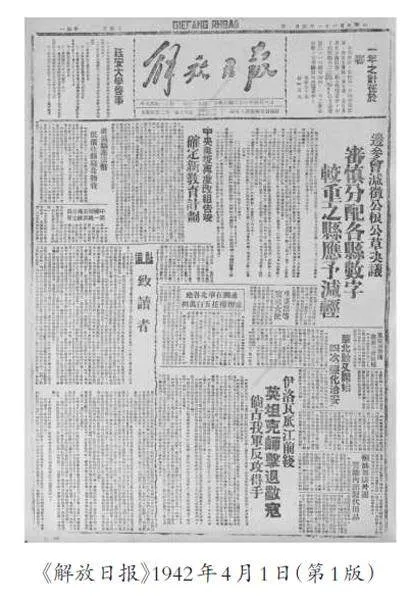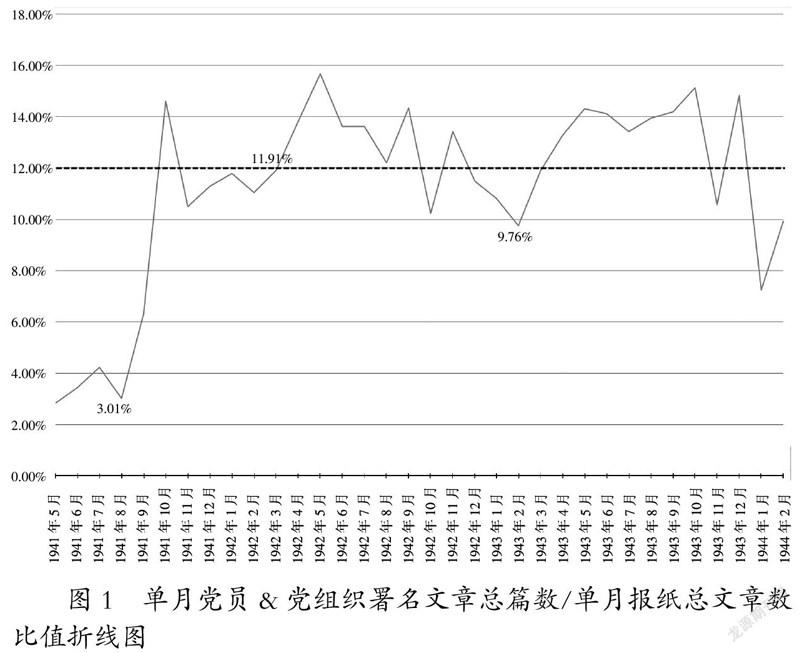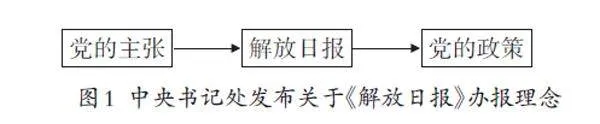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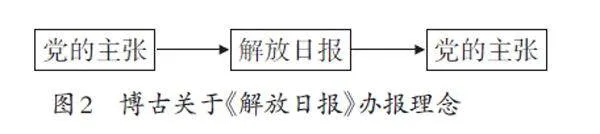
【摘要】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事件为切入点,梳理“党的整体形象”产生所依赖的不同路径。研究认为“党的整体形象”产生于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并由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具象化。虽然“党的整体形象”并非整风运动的直接目的,但是却成为整风运动的客观成果。同时,不具备“党的整体形象”思维的《解放日报》始终无法在工作中真正实践党报“四性”,阻碍整风运动的开展,最终走上改版的道路。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不仅是“党的整体形象”的反映者,更作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投入革命实践中去。
【关键词】党的整体形象;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日报》;致读者
在一些革命战争题材老电影里,总会有“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早就盼着你们来了”“是革命的队伍”这类台词。那么,这里面的“队伍”和“你们”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这些台词背后所反映的是革命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无论是“穷人的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都指向同一个行动主体。这里的形象认知不是分散的,而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党的形象的整体性在今天看来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1941年的初夏,关于党的建设还处在激烈的讨论与学习之中。什么是党的整体形象,党的整体形象概念发端于何处,本研究以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事件——《解放日报》改版为切入点,来对党的整体形象概念的产生进行梳理。
当下对于党的形象的研究往往不会带有“整体”二字,这受到研究对象的历史环境限制,本研究的时间出发点为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此时的党尚未在思想与行动上达成统一,独立性与自由化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以“整体”冠之“党的形象”是受到当时历史语境的影响。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整体形象”的建设思想发源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解放日报》改版的进程中,既是当时整风运动所要建设的党的基本样貌,也是指导《解放日报》改版的具体理念。只有具备了“党的整体形象”的思维,党报的“四性”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得以开展。
一、整顿“三风”:“党的整体形象”产生的政治路径
从政治路径来说,“党的整体形象”并非主动建构,而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对于党的一种整体期望。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思想上可以消除土地革命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余毒,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在行动上通过对“三风”的整顿来肃清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与“山头主义”,使全党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对思想和行为改造的目的,当然是基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所作出的判断,最终是为了推动革命进程向前发展。
解释“党的整体形象”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首先要从“党性”的问题谈起,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延安整风运动中要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同时“党性”问题也始终贯穿于《解放日报》改版的全过程。在《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中,第一条便鲜明地提出了报刊要贯彻保持坚强的党性。而后又对党性作出解释:“不仅要在篇幅上贯彻党的观点,更要与党的方针政策关联。同时,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1]可以看出,直到《解放日报》改版,博古执笔写这篇社论时,仍旧秉持报纸应当反映党的一切观点,认为这是党性的具体表现。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党性呢?在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而在具体的实践中的表现则是要求全体党员同志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2]“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实际上是“党整体形象”存在的前提,是在党组织内部的工作中,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开展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看出,在改版的前一年里,中央政治局已作出过关于党性的讨论,与博古在办《解放日报》时所要坚持的党性并不相同。当然,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关于党性的要求属于党的组织层面,而报刊的党性则属于操作层面,如何实现这两者的转化才是确立真正有党性的报刊的根本。
通过对“党性”的讨论可以看出,从政治路径上来说,《解放日报》改版的原因在于博古对于支撑党报存在的最重要的“党性”概念的理解与中央不符,这也就导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在前期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始终无法成为推动整风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工具。为什么“党的整体形象”与《解放日报》紧密相关,原因在于《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党对外传播的窗口,《解放日报》的传播内在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解放日报》上的文章表达了什么;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日报》表达了什么。可以看出,《解放日报》传播的元传播话语,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表达”这个行为本身,而此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便是《解放日报》,而这也是《解放日报》需要改版的关键:作为当时党报负责人的博古并不具备报纸反映的是“党的整体形象”的思维,导致《解放日报》犯了独立性和自由化的错误,始终不能成为帮助整风运动的战斗的中央机关报。
因此,“党的整体形象”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副产品,整风运动不是为了建立“党的整体形象”,而是通过整风运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统一,而这种统一性又必然会催生“整体的形象”的概念。同时,不能否认,在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整体形象”的思维,如毛泽东所言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党的整体形象”正是整风运动开展的方向性指引,整风运动的完成需要在“党的整体形象”统筹之下来进行。同样,作为党的喉舌的《解放日报》,如果始终无法理解“党性”,无法产生党报所反映的“党的整体形象”,那《解放日报》就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党报。
二、改造党报:“党的整体形象”产生的办报路径
党性如何从组织建设层面转换到报刊层面,首先需要对《解放日报》的定位有清晰的认知。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要利用报纸批掉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办法”。[3]同时要“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4]可以看出在改版后,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期待是希望可以利用《解放日报》来对党内不利于抗战的不良作风进行纠正。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讲话中指出“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同时还需要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5]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要求是希望能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一环,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整齐步调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各自为战。《解放日报》此时作为党的机关报,需要做的是帮助整风运动的开展,这是目的。而同时更需要将党的声音凝聚,以整体的风貌对外界展示,这是前提。而博古负责《解放日报》期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认为一切“都是执行了办报在政治上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社论均没有政治上的错误”。但没有将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整体形象来思维,而是孤立地记载着党的主张,即使“他(博古)本人更是尽心竭力按照党的政策做宣传”,《解放日报》也必须走上改版的道路。[6]这一点,可以从两则通知中反映出来。一则是关于由毛泽东代表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放日报》改版的通知: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7]另一则是由博古负责的《新中华报》所发布的消息:为着更多地反映国内外之一切消息及传达我党中央一切政治主张,满足全国同胞及读者诸君之要求起见,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及《今日新闻》合并,改出中共中央机关日报。定名为《解放日报》。[8]
关于这两则通知,学界更多关注第二则中“为着更多地反映国内外之一切消息”这句话,并认为这是博古大报思想的直接证据。在原本版面拮据的《解放日报》上擅作主张地反映国内外之消息,并在消息前加上“一切”限定词,实乃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极端表现。但笔者认为,两则消息中的另一句话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中央书记处发布的“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与《新中华报》上的“传达我党中央一切政治主张”,这两句话乍看之下似乎是同一个意思,但其实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报理念。
首先,“一切党的政策”是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这说明《解放日报》与新华社所发布的党的信息具有最高权威性,所代表的是党的声音,是一个主动传播的过程。而“传达我党中央一切政治主张”则是一种对党的“有闻必录”,是一种对消息的被动记载。其次,“政策”与“主张”也具有词意上的差异。“政策”在词典上的解释为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9]而“主张”在词典上的解释为见解,是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10]从逻辑顺序上来看,“主张”是“政策”的前提,“政策”是不同“主张”的结果。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政策”是最后的成熟阶段,而“主张”尚处在需要辨明与讨论的阶段。最后,结合对“政策”与“主张”的词义辨析来看,“一切党的政策”与“党中央一切政治主张”同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一切党的政策”中,“一切”位于“党的政策”之前,所修饰的主体是“党的政策”;而“党中央一切政治主张”中,“一切”位于“党中央”之后,位于“政治主张”之前,所修饰的主体是“政治主张”。两句表述中同样都存在着“一切”,但是“一切党的”和“党的一切”话语内涵投射的范围明显不同,“一切党的”所指为党中央所形成的最终所有决策结果,而“党的一切”所指为与党有关的所有成形与未成形的政治主张。
对上述两种不同表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所发布的关于《解放日报》的办报通知内的办报理念如图1所示:
而博古所负责的《新中华报》对即将出版的《解放日报》的办报理念如图2所示:
从上述图示可以看出,在中央书记处发布的办报方针中,《解放日报》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过滤掉一切不符合党的建设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杂音,以统一的声音向外传达党的政策。而博古的办报方针则把《解放日报》当作一个“传声器”,把党的一切主张不加辩证地向外传达,忽略了党报作为党的形象代表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这也难免博古在后来的《致读者》中进行自我检讨,指出“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书记处在起草关于《解放日报》办报的决议时,关于《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的初步计划是能够集中反映党的声音,而不是分散地对党的主张进行收集与传达。
在《解放日报》改版前,毛泽东建构了“社报—党报”的二元对立框架。[11]实际上就是批评在《解放日报》中存在的独立性,指出改版前的《解放日报》不是党报,而是社报,所谓社报,实际上就是报社几个人自以为代表了党,关于《解放日报》的内容“什么都由社内解决”“报社几个人……孤立地办报”。[12]结合毛泽东这段对解放日报的批评可以更加全面理解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党与党报》社论中就党性原则所做出的系统说明,其中“党报工作者应该有公仆意识,不可以自以为是,去做无冕之王”[13],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对同仁“小集体”所自以为的“无冕之王”与党组织“大集体”之间整体形象矛盾的批评。
在今日,回头审视《致读者》中所提出的“党报四性”中的“党性”在当时实乃不算新鲜之物。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成立的文件中就指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不得违背党的原则”“必须受到党的监督”[14]。这段表述与《致读者》中博古所陈述的对于“党性”的理解一般无二,可为何《解放日报》却始终做不到真正的有“党性”的党报呢?尤其是改版酝酿期间博古做了多次自我批评,其思想方法、群众观点和领导作风上有了很大进步。改版确定了新的办报方针、版面模式、报道重心。报社工作人员也都进行了思想整风,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与错误。但是要想使《解放日报》体现“真正的党报”、完全贯彻党的路线和党的政策,却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最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解放日报》问题做出相关决议以及一个月后《解放日报》刊发的《党与党报》社论标志着《解放日报》“党性”建设摸索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博古在《解放日报》工作中的摸索走到了尽头。
从报刊的实践层面来看,博古对于党报是有清晰认识的,但他头脑中的党报与毛泽东心目中的党报是不大相符的。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在《解放日报》改版之际,毛泽东其实也没有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报标准,因为在1942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解放日报》改版所作出的指示为:“根据会议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这样的论述并不准确,对于中央政治局来讲,更看重的是在整体中共革命的背景环境中,党报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对于具体的办报细节,自然应当交由博古来考虑,中央政治局给出的是关于党报整体功能的期待,只不过在后来《解放日报》改版的实践中,博古始终在报刊的操作性层面打转,始终没能领会党中央对于党报的具体期待。
如何理解党中央对于党报的期待,可以根据“就《解放日报》问题作出相关决议”来理解。决议指出:“日常政治必须报告中央。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社内部亦须如此。”同时,“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自由主义在报社是不能存在的”。这就说明,在改版前或是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始终没能解决的是“内容没有报告中央,以及报纸的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问题。这里的“日常政治必须报告中央”与前文提到党报委员会的“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具有明显不同,“接受党的领导”既可以是出版物层面的,也可以是组织机构层面的,而“日常政治必须报告中央”实际上说明《解放日报》上所刊载的内容不能具有“独立性”,内容必须通过党中央审核后方可刊发。
在决议发出一个月后所刊发的《党与党报》社论中提出的“报纸是党的喉舌”[15]的观点实际上是这种观点的形象化表达,作为党的“喉舌”的《解放日报》便有了一个具体的传播主体,这个传播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此时中国共产党应是作为整体的形象出现在《解放日报》上,而不是分散的、独立的。如前文所讲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具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
因此,在办报的实践活动中,《致读者》中所提出的“党报四性”实际上属于党报操作性层面的要求。如果没有一层统摄操作性层面的话语存在,那实际操作中“四性”就很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作为《解放日报》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在亲笔写下这“四性”之后,仍没有促进《解放日报》从“不完全的党报”到“完全的党报”的转变,而《解放日报》党性真正的确立,则是在《致读者》刊发四个月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由于博古始终在报刊的实践层面上打转,按照党报的教条去缘木求鱼,无法理解党中央对党报的总体期待,即“能够反映党的整体形象,反映党团结得像一个人”的党报。
三、集体读报:“党的整体形象”产生的现实路径
第一,集体读报本身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读报小组,指导群众读报的行为本身加深了群众对于作为“整体”的党的形象的认知。《解放日报》改版后所创立的读报小组既是当时延安地区实际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具体形式。如何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政策,知晓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建立“读报小组”进行集体读报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化解了这一难题。在读报的过程中,群众所接收到的信息不仅有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内容,由党员干部带领与指导读报本身就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沟通的过程,在群众感知中,参与读报的党员同志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化身,在这种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中,所传达出的信息也不局限于报纸上的内容,而是读报与解读的秩序中,“生产”与“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16]
第二,集体读报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能动的传播者,进而与群众共同成为消息的阐释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参与到读报过程中,并加深群众对党的认识。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就不会步调一致,没有《解放日报》的改版,作为整体形象的党就无法进行对内和对外传播工作。而在读报实践中,作为整体形象传播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读报活动中帮助党的政策与指示传达,同时还在读报过程中与群众共同成为消息的阐释者,进一步加深了对群众的了解,同时也产生了“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话语。
可以看出,现实的环境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主动的传播者参与到解放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在《解放日报》改版之前,报纸上分散罗列的党的消息既不能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政策,也无益于指导生产生活实践。同时,“独立性”与“自由化”的问题也借由改版前《解放日报》的窗口向外传播,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形象的认知。而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思想和行动上形成统一,在实践上以党的喉舌向外发出一致的声音,建构了作为“整体”存在的党的形象,并通过这一整体形象来进一步展开革命工作。
四、总结
通过对上述“政治路径”“办报路径”以及“现实路径”的分析,《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实际上是“党的整体形象”话语生产的过程。“党的整体形象”并非在延安整风运动与《解放日报》改版的进程中明确提出,但这两个工作的顺利开展显然无法离开建设“党的整体形象”的思维。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最终的结果是形成思想上和行动上统一的“整体的党”,《解放日报》改版则是将这一“整体的党”具象化,而当时的现实环境也给这一具象化的形象以具体的实践环境,只有在具有“党的整体形象”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话语建构,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延安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和改造党内当时的错误思想,使中国革命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一环,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才真正作为党的机关报达到服务群众的目的。
对于《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来说,博古作为前期负责人始终没有跳出孤立理解党性的限制,始终认为如实反映党的声音就是报刊的党性,最终导致党内“独立性”与“自由化”的错误思想通过《解放日报》传达给外界,但是改造党报不仅要从具体的操作性步骤做起,更要先确立起报刊所对外反映的是“党的整体形象”的思维,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环境中只有团结得像一个人才能够完成革命任务,而博古显然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解放日报》是党的喉舌,对外传达的应该是一种声音,但博古理解的党性显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认为反映与党有关的声音就是党性。这种认识是消极的,更是没有将“党的整体形象”与《解放日报》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关联考察。
因此,没有“党的整体形象”思维的形成,就无法在办报实践中考虑到《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所传达的信息中可能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更无法通过整体思维来对报道活动进行规划。这使得《解放日报》始终徘徊在对“党的声音”有闻必录的消极阶段,始终无法作为一个主动的传播者投入整风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中。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传播话语体系变迁研究(1919-2018)”(批准号:18ZDA315)]
参考文献:
[1]致读者[N].解放日报,1942-04-0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档案馆,2011:44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9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91.
[6]李金锉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9.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54.
[8]李金锉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5.
[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74.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12.
[11]贾梦梦,周光明.作为话语的“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解读[J].国际新闻界,2020,42(05):153-175.
[1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45.
[13]党与党报[N].解放日报,1942-09-22.
[1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5.
[15]党与党报[N].解放日报,1942-09-22.
[16]刘驰,柏一兰.抗战时期党报“群众办报”话语生成逻辑及内涵表达:以《解放日报》为文本的考察[J].中国出版,2021(13):30-34.
作者简介:王子丰,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72);周宇豪,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072)。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