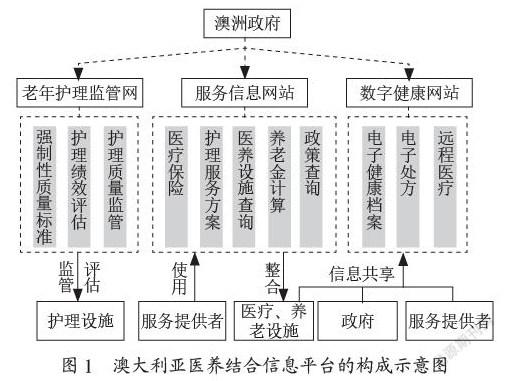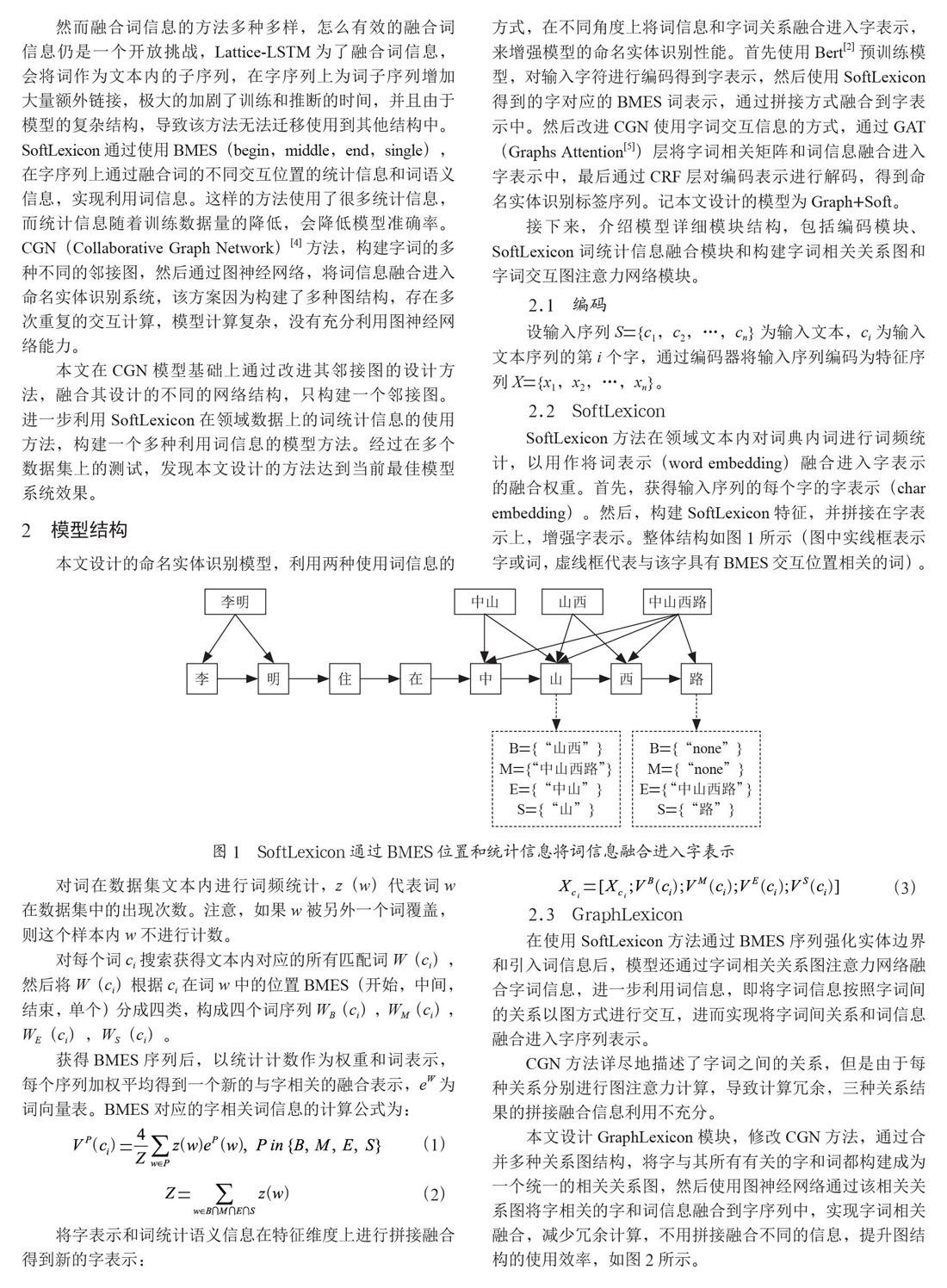【摘要】在国际舆论战中,武器化传播已渗透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带来“一切皆可武器化”的想象与实践。武器化传播通过技术、平台和政策操控公众认知,体现了权力分配与文化博弈的复杂互动。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推动下,认知操控、社会分裂、情感极化、数字监控、信息殖民已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新型手段,这不仅加剧了信息强国与弱国间的竞争,也为信息弱国提供了通过灵活策略和技术创新实现逆转的机会。在全球非对称传播格局下,如何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战略目标与社会平衡间找到契合点和平衡点,将是影响未来国际舆论格局的关键要素。
【关键词】舆论战;武器化传播;信息操纵;非对称传播;信息安全
如果说“宣传是对现代世界的理性认可”[1],那么武器化传播则是对现代技术手段的理性应用。在舆论战中,各参与主体通过不同传播手段实现战略目标,做到表面合理且隐蔽。与传统军事冲突不同,现代战争不仅涉及物理对抗,还涵盖信息、经济、心理及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竞争。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推动,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物理对抗逐渐转向多维度、多领域的综合作战。在这一过程中,武器化传播作为一种现代战争形式,成为通过控制、引导和操纵舆论,影响敌对方或目标受众的心理、情感与行为,进而实现政治、军事或战略目的的隐形暴力手段。《战争论》认为,战争是让敌人无力抵抗,且屈从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2]在现代战争中,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对抗,更需要信息、网络与心理战等非传统领域的支持。第六代战争(Sixth Generation Warfare)预示战争形态的进一步转变,强调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系统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以及信息、网络、心理和认知领域的全面博弈。现代战争的“前线”已扩展到社交媒体、经济制裁和网络攻击等层面,要求参与者具备更强的信息控制与舆论引导能力。
当前,武器化传播已渗透到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带来“一切皆可武器化”的忧虑。在战争社会学中,传播被视为权力的延伸工具,信息战争深刻渗透并伴随传统战争。武器化传播正是在信息控制的框架下,通过塑造公众认知与情感,巩固或削弱国家、政权或非国家行为者的权力。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战时,也在非战斗状态下影响着国家内外的权力关系。在国际政治传播中,信息操控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工具,各国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发动网络攻击等手段,试图影响全球舆论和国际决策。舆论战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手段,更涉及国家间权力博弈与外交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国际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权力格局。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武器化传播的概念流变,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心态,阐述具体的技术手段及所带来的风险,并从国家层面提出多维应对策略。
一、从传播武器化到武器化传播:概念流变及隐喻
武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战争的象征和工具,战争则是人类社会中最极端、暴力的冲突形式。因此,“被武器化”是指将某些工具用于战争中的对抗、操控或破坏,强调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武器化”(weaponize)译为“使得使用某些东西攻击个人或团体成为可能”。1957年,“武器化”一词作为军事术语被提出,V-2弹道导弹团队的领导者沃纳·冯·布劳恩表示,他的主要工作是“将军方的弹道导弹技术武器化”[3]。
“武器化”最早出现在太空领域,时值美苏军备竞赛时期,两个大国力图争夺外太空主导权。“太空武器化”是指将太空用于发展、部署或使用军事武器系统的过程,包括卫星、反卫星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等,目的是进行战略、战术或防御性行动。1959年至1962年,美苏提出了一系列倡议,禁止将外太空用于军事目的,尤其是禁止在外层空间轨道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空间政策指令-3》,启动“太空军”建设,将太空视为与陆地、空中、海洋同等的重要作战领域。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倡议“禁止在外空放置任何类型武器”[4]。
除太空领域的武器化外,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也显现武器化趋势。“军事武器化”是将资源(如无人机、核武器等)用于军事目的、部署武器系统或发展军事能力。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乌克兰每月因俄罗斯干扰站的影响,损失约10000架无人机。[5]“武器化”也常出现在“金融战争”“外交战场”等表述中。在经济领域,武器化通常指国家或组织对全球金融系统中的共享资源或机制的利用;外交武器化则表现为国家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舆论操控等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并对他国施加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器化”概念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尤其在信息领域,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舆论操纵已成为政治斗争的普遍工具。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曾在国家战略研究所会议上表示,“万物武器化”(the weaponization of everything)的时代已经来临。[6]
作为一种隐喻,“武器化”不仅指实际物理工具的使用,还象征着对抗性和攻击性行为的转化,强调“武器”这一概念如何渗透至日常生活、文化生产和政治策略中,展现社会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工具达成战略目的。时下,许多本应保持中立的领域,如媒体、法律和政府机构,常被描述为“武器化”,用以批判它们的过度政治化和被不正当利用,突出其非法性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通过这一隐喻,人们无意识地将当前的政治环境与理想化的、看似更温和的过去进行对比,使人们认为过去的政治氛围更加理性和文明,而现今则显得过于极端和对立。[7]因此,“武器化”的实质是政治中介化的过程,是政治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影响或控制本应保持中立的领域,使其成为政治目的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信息领域,传播武器化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战略手段。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就广泛使用了宣传和舆论战,传播手段被作为一种心理战术使用。武器化传播是传播武器化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体现,其利用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地控制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进而操控舆论和情感,反映了技术、平台和策略的结合,使得政治力量可以更加精准和高效地操控公众认知与舆论环境。信息作为舆论的本体,被“武器化”并用于影响社会认知和群体行为,“战争”的概念也随之变化,不再只是传统的军事对抗,还包括通过信息传播和舆论操控实现的心理战和认知战。这种转变促生了一系列新术语,例如无限制战争(unrestricted warfare)、新一代战争(new generation warfare)、非对称战争(asymmetric warfare)和非常规战争(irregular warfare)等。这些术语几乎都借用“战争”(warfare)强调信息领域中的多样化冲突,信息成为被“武器化”的核心内容。
尽管有部分观点认为“战争”一词不适用于未正式宣布敌对行动的情况[8],但武器化传播通过弱化战争的传统政治属性,将各领域的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和形式笼统地视作传播行为,从而扩展了“战争”这一概念的外延。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术语中“武器化”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weaponized noun(名词)”,即表示某物已经“被武器化”,具备武器功能或用途;另一种是“weaponization of noun”,指将某物转化为武器或具有武器性质的过程。在学术领域,尽管weaponized communication和weaponization of communication尚未严格区分,但中文翻译有所区别。“武器化传播”更侧重于传播手段或信息本身“被武器化”,以实现某种战略目标;“传播武器化”则强调传播过程本身作为武器的转化过程。在讨论具体技术手段时,多数学术论文采用weaponed或weaponizing作为前缀,以修饰具体的传播手段。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国际舆论战中的具体传播策略,着重描述已经发生的武器化现象,故统一使用“武器化传播”,其是一种利用传播手段、技术工具和信息平台,通过精确操控信息流动、公众认知与情感反应,达到特定军事、政治或社会目的的策略性传播方式。武器化传播也并非单纯的战争或战时状态,而是一种持续的传播现象,它反映了各主体间的互动与博弈,是信息共享和意义空间的流动。
二、武器化传播的应用场景及实施策略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信息领域的武器化仍是一个“死话题”,各国主要追逐导弹、无人机等实体武器的升级竞赛,那么步入21世纪,网络战争则真正冲进了公众视野,并深刻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由社交媒体和智能设备,公众不可避免地卷入舆论战争,不自觉地成为参与者或传播节点。随着技术的普及,武器化手段逐渐从国家主导的战争工具扩展到社会化和政治化领域,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从显性的国家机器转向更隐蔽的观念操控。棱镜计划(PRISM)的曝光引发了全球对隐私泄露的强烈担忧,凸显了国家利用先进技术进行监视和控制的潜力,这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武器化。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社交机器人等信息武器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全球政治博弈中的常见现象。信息作战——包括电子战、计算机网络作战、心理战和军事欺骗——被广泛用于操控信息流动,影响舆论格局。这些手段不仅在军事战争和政治选举中发挥作用,还逐渐渗透到文化冲突、社会运动及跨国博弈之中,传统的信息作战逻辑得以延续。如今,武器化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工具,深刻影响着舆论生态、国际关系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
(一)军事领域的信息操纵战
信息流能够直接影响军事冲突的走向,塑造公众和军队的认知与决策,进而影响士气、战略判断和社会稳定。在现代战争中,信息不再是单纯的辅助工具,信息领域已成为核心战场。通过操控信息流向,敌方的形势评估可能被误导,战斗意志被削弱,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被动摇,进而影响战争的决策过程与持续性。
海湾战争(Gulf War)被视为现代信息战的开端。在这场战争中,美国通过高科技手段——包括电子战、空中打击和信息操作——实施了对伊拉克的系统性打击。美军利用卫星和AWACS预警机实时监控战场态势,通过空投传单和广播电台向伊拉克士兵传递美军优势及投降后的优待政策,从心理层面诱使伊军投降。这场战争标志着信息控制在军事冲突中的关键地位,展示了信息战在现代战争中的潜力。进入21世纪,网络战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战不仅涉及信息的传播和操控,还包括通过攻击关键基础设施实现对敌方社会功能的控制。2007年爱沙尼亚遭遇大规模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攻击,展示了信息操纵与网络攻击融合的趋势。2017年在WannaCry勒索软件事件中,攻击者利用Windows系统漏洞(EternalBlue)加密全球150个国家约20万台计算机文件,要求支付赎金,严重影响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体系(NHS),导致急诊服务中断和医院系统瘫痪,进一步揭示了网络战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此外,在长期冲突中,基础设施控制因能够直接决定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方向,被广泛用于削弱对手的战略能力,争夺公共信息空间。以色列通过限制无线电频谱使用、控制互联网带宽和破坏通信设施,有效削弱了巴勒斯坦的通信能力。同时,以色列还通过经济制裁和法律框架限制巴勒斯坦电信市场的发展,压制巴勒斯坦在信息流动中的竞争力,巩固自身在冲突中的战略优势[9],以维持信息的不平等流动。
社交媒体为信息操纵提供了即时、广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其能够跨越国界,影响全球公众情绪和政治局势,也使战争焦点从单纯的物理破坏转向舆论操控。俄乌战争期间,深度伪造技术作为视觉武器,对公众认知和战争舆论产生了显著干扰。2022年3月1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伪造视频在Twitter上传播,视频中他“呼吁”乌克兰士兵放下武器,引发了短时间内的舆论混乱。同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伪造视频也被用以混淆视听。尽管这些视频被平台迅速标注“Stay informed”(等待了解情况)的说明,但其在短时间内仍然对公众情绪和认知造成明显干扰。这些事件凸显了社交媒体在现代信息战中的关键作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虚假信息、情感操控等手段对军事冲突施加干扰。
信息操纵战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双重特性上——既是攻击工具,也是防御的手段。在军事领域,各国通过防御和反击网络攻击来确保国家安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维护军事机密,并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对手的战斗力与决策。2015年和2017年,俄罗斯黑客发起了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如BlackEnergy和NotPetya),乌克兰通过迅速升级网络防御系统,成功抵御部分攻击并采取反制措施,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瘫痪。此外,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和英国第77旅等单位专注研究和平时期的舆论塑造[10],利用战略传播、心理战和社交媒体监控等手段,扩大信息领域的战略控制,并强化了防御与舆论塑造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信息战的战略高度。
如今,信息操纵战已经成为现代军事冲突中的关键环节。通过信息技术与心理操控的高度结合,它不仅改变了传统战争的规则,也深刻影响着公众认知和全球安全格局。国家、跨国公司或其他行为体通过掌控关键基础设施和社交媒体平台,限制信息流动、操控传播路径,从而在全球信息生态中获得战略优势。
(二)政治选举的舆论干预战
政治选举是民主政治中最直接的权力竞争场域,信息传播在此过程中对选民决策具有重要影响。通过计算宣传等手段,外部势力或政治团体能够操纵选民情绪、误导公众认知,从而左右选举结果、破坏政治稳定或削弱民主进程,选举因此成为武器化传播最具效果的应用场景。
近年来,全球政治选举呈现极化趋势,持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极化导致公众选择性接受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同时排斥其他信息,这种“回音室效应”加剧了公众对立场的片面认知,为舆论干预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计算宣传的兴起,使外部势力能够更加精准地操控舆论和影响选民决策。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指利用计算技术、算法和自动化系统操控信息流动,以传播政治信息、干预选举结果和影响舆论,其核心特征在于算法驱动的精准性和自动化传播的规模化,通过突破传统人工传播的限制,显著增强了舆论操控的效果。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团队通过剑桥分析公司分析Facebook用户数据,为选民定向推送定制化的政治广告,精准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意向[11]。这一事件被视为计算宣传干预选举的典型案例,也为其他政客提供了操作模板,推动了计算宣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团队遭遇黑客攻击,内部邮件被窃取并公开,内容称马克龙在海外拥有秘密账户并涉及逃税,企图抹黑其形象。2018年巴西总统选举期间,候选人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团队利用WhatsApp群组传播煽动性政治内容,定向推送大量图像、视频和煽动性消息以影响选民情绪。据统计,自2017年至2019年,全球采用计算宣传的国家由28个增加至70个,2020年这一数量上升至81个。这表明,计算宣传正通过技术手段和传播策略,重新定义全球选举中的舆论规则。
计算宣传也是国家行为者在舆论干预战中的重要工具。2011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在中东地区开展“欧内斯特之声”行动,通过建立和管理多个虚假身份(sockpuppets),扭曲阿拉伯语社交媒体的对话。俄罗斯也频繁利用计算宣传实施干预,在加拿大操作约20万个社交媒体账户,借助极右翼和极左翼运动散布亲俄言论,制造虚假的社会热点,试图破坏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支持[12]。作为计算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机器人通过自动化和规模化手段制造舆论热度,借由特定标签在社交平台上增加信息的曝光率,操控议题的优先级。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利用社交机器人发布支持普京和攻击反对派的内容,通过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掩盖反对派声音,强化亲普京的舆论氛围。[13]2017年海湾危机期间,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通过Twitter机器人制造反卡塔尔标签#AlJazeeraInsultsKingSalman的热度,使其成为热门话题,虚构了反卡塔尔情绪的高峰,进而影响了全球范围内对卡塔尔的舆论态度。[14]深度伪造技术则进一步提升了计算宣传的精准性与隐蔽性。2024年,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伪造视频在X(原Twitter)上迅速传播,视频显示其在椭圆形办公室使用攻击性语言,引发舆论争议并影响选民情绪。据网络安全公司McAfee调查,63%的受访者在两个月内观看过政治深度伪造视频,近半数表示这些内容影响了他们的投票决定。[15]
在全球范围内,计算宣传已渗透各国舆论战中,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数字武器对巴勒斯坦展开舆论战,土耳其培养了“爱国巨魔军队”操控国内外舆论,墨西哥政府利用僵尸网络影响舆论。作为现代舆论干预战的重要手段,计算宣传正在改变全球政治传播的格局。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计算宣传还可能通过更隐蔽和高效的方式干预选举流程,甚至直接威胁民主制度的核心运行逻辑。
(三)文化领域的符号认同战
武器化传播通过操控信息、符号和价值观,试图影响公众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进而塑造或改变社会的集体认知与文化认同。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在于信息的传递,更通过特定的叙事框架、文化符号和情感共鸣,推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的传播与认同。通过操纵文化符号、社会情感和集体记忆,武器化传播在文化领域干扰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成为符号认同战的核心手段。
模因(Meme)作为一种集视觉元素和简洁文字于一体的文化符号,以幽默、讽刺或挑衅的方式激发观众的情感反应,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佩佩模因(Pepe the Frog)起初是一个无害的漫画角色,被极右翼群体重新利用并武器化,用以传播仇恨言论,逐渐演变为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的象征。模因将复杂的政治情绪转化为便于传播的视觉符号,迅速激起公众对政策的不信任和愤怒,被视为“武器化的偶像破坏主义”(Iconoclastic Weaponization)。这一过程通过操控文化符号,以达到政治或社会斗争的目的[16],加剧了公众对社会和政治的分裂。例如,在英国脱欧期间,带有“Take Back Control”(夺回控制权)字样的模因迅速传播,强化了民族主义情绪。
除了文化符号的制造外,符号的筛选和屏蔽同样能够塑造或加深某种文化认同或政治立场。审查制度自古以来就是权力控制信息的重要手段,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政府就对公共演讲和文学作品进行审查,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权力稳定。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推动了审查制度的现代化,平台审查逐渐取代传统的审查方式,成为当代信息控制和舆论引导的核心工具。算法审查通过人工智能检测敏感话题、关键词和用户行为数据,自动删除或屏蔽被视为“违规”的内容,社交媒体的审核团队会对用户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筛选,确保其符合平台政策和法律法规。平台审查的作用不仅是限制某些内容的传播,更是通过推送、删除和屏蔽等方式引导舆论,塑造公众认知框架。尽管主流社交平台通过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控制信息传播,但一些边缘平台,如Gab、Gettr、Bitchute等因缺乏有效审查,成为极端言论和恶意信息的温床。这些平台未对内容发布做出足够限制,极端观点和虚假信息得以肆意扩散,例如,Gab因极端主义内容屡遭批评,被指助长暴力和仇恨。在回声室中,用户只能接触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这种信息环境更强化了极端思想,导致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加剧。[17]
语言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和工具,能够通过情感操控、符号政治和社会动员等方式,深刻影响群体行为和文化认同。语言武器化聚焦于语言形式和文化语境如何影响信息的接收方式,强调语言如何被用来操控、引导或改变人们的认知与行为。这不仅涉及特定词汇和修辞手法的使用,更包括通过语言表述建构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框架。作为符号认同战的另一重要工具,语言塑造了“敌我对立”的叙事框架。大翻译运动(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通过选择性翻译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言论,将其传播到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这种语言操控通过情绪化表达放大了争议性内容,加深了国际社会的文化偏见。
语言武器化的深层逻辑在于情绪化和煽动性的语言形式。西方国家常以“人权”与“民主”等正义化标签为干预行为辩护,合法化政治或军事行动。白人至上主义者使用“另类右翼”等模糊标签重塑意识形态,将传统的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白人至上主义”转化为一个较为中立的概念,降低了该词汇的社会抵抗力,用宽泛的“伞式”身份扩大其支持者的基础。通过对世俗话语的渗透,仇恨政治和极端言论被正当化,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常态。当公众将这种政治日常化后,语言实现了真正的武器化。[18]在尼日利亚,煽动仇恨的内容通过种族、宗教和地区话题扩散,深刻恶化了社会关系。[19]语言的模糊性和合理否认策略也成为传播者规避责任的有力工具,在被简化的叙事中传播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议题。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通过否定性标签和情绪化话语,以反对全球化、质疑气候变化科学、抨击传统盟友等方式,故意提出与主流意见相对立的观点,激发公众对全球化的不信任,重塑国家利益优先的文化认同。[20]
三、武器化传播的风险与挑战:正当性与破坏性
尽管武器化传播给国际舆论格局带来了巨大风险,但特定情形下,其可能会被某些国家或团体通过法律、政治或道德框架赋予一定的正当性。如“9·11”事件后,美国通过《爱国法案》扩大了情报部门的监控权限,以“反恐”为名实施广泛的信息控制,这种“正当性”常被批评为破坏公民自由,侵蚀了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武器化传播更常被视为“灰色区域”(Gray Zone)的手段。国家间的对抗不再局限于经济制裁或外交压力,而是通过信息操控、社交媒体干预等非传统方式展开。部分国家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借口传播虚假信息,辩称其行为是合规的,尽管这些行为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争议,但往往被合理化为“反制外部威胁”的必要手段。在一些信息监管缺乏严格法律框架的国家,选举的干预行为往往被容忍,甚至被视为一种“正当”的政治活动。在文化层面,某些国家通过传播特定的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自身的文化影响力。西方国家常以“文化共享”和“文明传播”为名,推动其价值观的传播,而在实际操作中,却通过操控文化符号和叙事框架,削弱其他文化的认同感,导致全球文化生态的不平衡。法律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武器化传播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持。一些国家以“反恐”和“反对极端主义”为名,通过信息审查、内容过滤等手段限制所谓“有害信息”的传播。然而,这种正当性往往突破了道德边界,导致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信息治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内部认可,却为武器化传播的泛滥提供了空间。
相较于正当性,武器化传播的破坏性尤为显著。目前,武器化传播已成为权力结构操控舆论的重要工具,其不仅扭曲了信息内容,还通过隐私侵犯、情感动员和文化渗透等方式,深刻影响了公众认知、社会情绪以及国际关系。
(一)信息失真与认知操控
信息失真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故意或无意扭曲,导致公众接收到的内容与原始信息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和误导性内容的传播日益猖獗,人工智能模型(如GPT)的生成内容,可能因训练数据的偏见而加剧这一问题。性别、种族或社会偏见可能被反映在自动生成的文本中,放大信息失真的风险。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特性也使传统的事实核查机制难以跟上虚假信息的扩散速度。虚假信息在短时间内往往占据舆论主导地位,跨平台传播和匿名性使得澄清与纠正变得更加复杂。传播的不对称性削弱了传统新闻机构的权威性,公众更倾向于相信即时更新的社交平台信息,而非传统新闻机构的深入报道,这进一步削弱了新闻机构在抵制虚假信息中的作用。
除了信息本身的失真,武器化传播还深刻利用了认知失调的心理机制。认知失调指个体接触到与其已有信念或态度相冲突的信息时产生的心理不适感。传播者通过制造认知失调,动摇目标受众的既有态度,甚至诱导其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在政治选举中,定向传播负面信息常迫使选民重新审视政治立场,甚至改变投票倾向。武器化传播通过选择性暴露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的形成,让受众倾向于接触与自身信念一致的信息,忽视或排斥相反观点。这不仅强化了个体的认知偏见,也让虚假信息在群体内部快速扩散,难以被外界的事实和理性声音打破,最终形成高度同质化的舆论生态。
(二)隐私泄露与数字监控
近年来,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加剧了隐私侵权问题。2019年,“ZAO”换脸软件因默认用户同意肖像权而被下架,揭示了生物特征数据的过度采集风险。用户上传的照片经深度学习处理后,既可能生成精确的换脸视频,也可能成为隐私泄露的源头。更严重的是,深度伪造等技术被滥用于性别暴力,多名欧美女演员的面孔被非法植入虚假性视频并广泛传播,尽管平台在部分情况下会删除这些内容,但开源程序的普及让恶意用户能够轻松复制和分享伪造内容。此外,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往往默认授权平台访问其设备的照片、相机、麦克风等应用权限。通过这些权限,平台不仅收集了大量个人数据,还能够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的行为特征、兴趣偏好和社交关系,进而精准投放广告、内容推荐甚至实施信息操控。这种大规模数据采集推动了对隐私保护的全球讨论。在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试图通过严格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规定,加强个人隐私权保障。然而,由于“隐性同意”或复杂的用户协议,平台常常绕过相关规定,使数据处理过程缺乏透明度,导致普通用户难以了解数据的实际用途。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无需为用户生成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规定推动了平台内容审核的发展,但也使其在应对隐私侵权时缺乏动力。平台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往往滞后处理虚假信息和隐私问题,导致审核责任被持续搁置。
在数字监控方面,社交平台与政府的合作使用户数据成为“监控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通过电话记录、互联网通信和社交媒体数据,实施大规模监控,并与Google、Facebook等大型企业合作,获取用户的在线行为数据,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情报收集和行为分析。跨国监控技术的滥用更是将隐私侵犯推向国际层面。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NSO开发的Pegasus间谍软件,通过“零点击攻击”入侵目标设备,可实时窃取私人信息和通信记录。2018年,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一案中,沙特政府通过Pegasus监听其通信,揭示了这种技术对个体隐私和国际政治的深远威胁。
(三)情感极化与社会分裂
情感在影响个体认知与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武器化传播通过煽动恐惧、愤怒、同情等情绪,影响理性判断,推动公众在情绪驱动下做出非理性反应。战争、暴力和民族主义常成为情感动员的主要内容,传播者通过精心设计的议题,将爱国主义、宗教信仰等元素植入信息传播,迅速引发公众情感共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进一步放大了情感极化的风险。虚假信息与极端言论在平台上的快速传播,不仅来自普通用户的分享行为,更受到算法的驱动。平台倾向优先推送情绪化和互动性高的内容,这些内容常包含煽动性语言和极端观点,从而加剧了仇恨言论和偏激观点的传播。
社交媒体标签和算法推荐在情感极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查理周刊事件后,#StopIslam标签成为仇恨言论的传播工具,用户借助该标签发布仇视和暴力倾向的信息。在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社交平台上的极端政治言论和错误信息也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被放大。通过精确的情感操控,武器化传播不仅撕裂了公共对话,还极大影响了社会的民主进程。另一种特殊的极端主义动员策略是“武器化自闭症”(Weaponized Autism),即极右翼团体利用自闭症个体的技术专长,实施情感操控。这些团体招募技术能力较强但有社交障碍的个体,通过赋予虚假的归属感,将其转化为信息战的执行者。这些个体在极端组织的指引下,被用于传播仇恨言论、执行网络攻击和推动极端主义。这种现象不仅揭示了情感操控的深层机制,也表明技术如何被极端团体利用来服务于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议程。[21]
(四)信息殖民与文化渗透
“武器化相互依赖”理论(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Theory)揭示了国家如何利用政治、经济和信息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22]特别是在信息领域,发达国家通过控制信息流实施“信息殖民”,进一步巩固其文化和政治优势。数字平台成为这一殖民过程的载体,全球南方国家在信息传播中高度依赖西方主导的技术平台和社交网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Facebook已成为“互联网”的代名词。这种依赖不仅为西方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收入,还通过算法推荐对非洲本土文化和价值观,尤其是在性别、家庭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文化渗透成为常态。
数字不平等是信息殖民的另一表现。发达国家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上的主导地位,使南方国家在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日益边缘化。巴勒斯坦因基础设施不足和技术封锁,难以有效融入全球数字经济,既限制了本地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话语权。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信息强国通过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限制他国获取关键技术与创新资源,这不仅阻碍了目标国的科技发展,也加剧了全球技术与创新生态的断裂。自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导致其在半导体和5G领域发展受阻,技术与创新的不对称拉大了全球技术生态的差距,使许多国家在信息竞争中处于劣势。
四、反思与讨论:非对称传播格局中的话语权争夺
在国际非对称传播(Asymmetric Communication)竞争格局下,强势方常常通过主流媒体和国际新闻机构等渠道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而弱势方则需要借助创新传播技术和手段来弥补劣势,争夺话语权。这一传播格局的核心在于信息地缘政治(Information Geopolitics),即国家之间的权力较量不仅仅取决于地理位置、军事力量或经济资源,更取决于对信息、数据和技术的控制。大国间的博弈已不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控制,而扩展至舆论空间的争夺。这些“信息景观”涉及全球传播生态中的话语权、信息流通和媒体影响力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不断制造景观,以影响国际舆论、塑造全球认知框架,进而实现其战略目标。非对称传播的策略不仅关乎信息内容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如何借助各种传播技术、平台和手段弥补资源与能力上的差距,信息传播的核心不再局限于内容本身,而围绕着话语权的争夺展开。随着信息战和认知战的兴起,谁掌握了信息,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
(一)后发优势下的技术赶超
传统的大国或强势传播者掌控着全球舆论的主导权,相比之下,弱势国家往往缺乏与这些大国抗衡的传播渠道。后发优势理论主张后发国家能够通过跳跃式发展,绕过传统的技术路径,引进现有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从而迅速崛起并规避早期技术创新中的低效和过时环节。在武器化传播的背景下,这一理论为信息弱国提供了通过新兴科技突破大国传播壁垒的路径,有助于其在技术层面上实现赶超。传统媒体往往受到资源、影响力和审查机制的限制,信息传播速度慢、覆盖面有限,且容易受到特定国家或集团的操控。数字媒体的崛起使信息传播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弱势国家能够借助全球化的互联网平台,直接面向国际受众,而不必依赖传统的新闻机构和主流媒体。通过新兴技术,弱势国家不仅能更精准地传递信息,还能通过定向传播和情感引导,迅速扩大其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5G网络等)实现精准的信息传播,打造高效的传播渠道。以大数据分析为例,后发国家可以深入了解受众需求和舆情趋势,快速识别全球舆论脉搏,实施定向传播,快速扩大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预测舆论发展方向,还能实时优化传播策略。5G网络的普及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覆盖范围,使后发国家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突破传统传播模式的局限,形成独特的传播优势。
通过跨国合作,后发国家可以整合更多的传播资源,扩大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例如,阿根廷与拉美其他国家共同建立了“拉美新闻网络”,通过新闻内容共享,推动拉美国家在国际舆论中发出统一的声音,反击西方媒体的单一叙事。在非洲,南非与华为合作推动“智慧南非”项目,建设现代化信息基础设施,促进数字化转型和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后发国家政府应加大对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投入,鼓励本土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文化输出和媒体产业建设,通过全球化合作和去中心化传播模式提升国家在国际信息空间中的话语权。政府可以资助数字文化创作,支持本地社交媒体平台的成长,并通过国际合作框架整合更多传播资源。
(二)信息反制中的壁垒构建
与军事行动可能引发的全面冲突,或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同,武器化传播能够在不触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实现战略目标,基于成本和战略考量,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由于武器化传播具备低成本、高回报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选择通过操控信息来达到战略目标。这种传播手段的普及,使得国家在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信息攻击时,面临更加复杂和多变的威胁。随着信息战争的日益激烈,单纯的传统军事防御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相反,构建强有力的信息防御体系,成为国家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社会认同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策略。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外部信息干扰和舆论操控,并进行信息反制,已成为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善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用以防范敏感信息不被外部操控或篡改。以欧盟为例,欧盟通过“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推动成员国加强网络安全建设,要求互联网公司更积极地应对虚假信息和外部干预。欧盟的网络安全指令还规定各成员国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保护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免受网络攻击。此外,欧盟还与社交平台公司,如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建立合作,通过提供反虚假信息工具和数据分析技术来打击假新闻传播。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自动化技术正在成为信息防御的重要工具,被用以实时监控信息传播路径,识别潜在的虚假信息和抵御舆论操控。在网络安全领域,大数据分析帮助决策者识别和预警恶意攻击,并优化反制策略。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在国内层面增强信息防御能力,还能提高国家在国际信息空间中的主动性和竞争力。
反制机制是信息防御体系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实时监控外部信息传播并及时纠正虚假信息成为维护舆论主动权的关键。乌克兰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通过与北约和美国合作,建立了颇具规模的网络防御体系。乌克兰的国家网络安全局为应对网络威胁设立了“信息反制小组”,利用社交媒体和新闻发布平台实时驳斥俄罗斯的虚假报道,这一策略显著提升了乌克兰在国际舆论中的声誉和信任度。
(三)舆论引导中的议程设置
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全球竞争格局中,舆论引导不仅涉及信息传播内容,更关键的是如何设置议程并聚焦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议程设置理论表明,谁能掌控信息流通的议题,谁就能引导舆论的方向。议程设置通过控制话题的讨论范围和焦点,影响公众对事件的关注与评价,社交媒体的兴起为信息弱势国提供了突破口,使其可以通过多平台联动来争夺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以乌克兰为例,其在俄乌战争中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战争实况,不仅发布战斗实况,还融入民众的情感诉求,借助平民遭遇和城市破坏的悲情叙事,激发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关注。在抵御外部信息干扰的同时,国家还需要主动传播正面叙事,讲述能够引发国际社会共鸣的文化故事。故事应该符合国际舆论的情感需求,同时展现国家的独特性,强化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我国的“一带一路”共建为例,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我国投资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帮助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基础条件,也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责任担当,更为文化合作和交流活动提供了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为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责任感。
但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往往面临资源、技术与国际传播平台的限制,难以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因此它们依赖更加灵活、创新的传播手段来参与全球议程的设置。例如,巴西在应对环保和气候变化议题上,尤其是亚马逊森林的砍伐问题,面临来自西方媒体的负面舆论压力。为此,巴西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关于亚马逊保护的最新数据和成功案例,积极塑造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形象。同时,巴西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推动南南合作,增强了在气候问题上的话语权。大型国际事件、人道主义活动和制作文化产品等,也是讲述国家故事的有效方式。国际体育赛事如世界杯、奥运会等,不仅是体育竞技的展示平台,更是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场所,通过承办或积极参与这些全球性事件,国家能够向世界展示其实力、价值和文化魅力,推动积极的舆论议程。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23]。这一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论断在武器化传播的语境下得到了现代化的诠释。武器化传播突破了传统战争的物理边界,成为一种融合信息战、认知战和心理战的现代战略手段。它以非暴力的形式操控信息流向和公众认知,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无须依赖直接军事行动即可实现政治目标,体现出极强的战略性和目标性。通过操控信息、情绪和价值观,武器化传播能够在避免全面战争的同时达成战略目的,在全球竞争和冲突中,已成为强国对弱国进行政治压制的重要手段。
武器化传播的核心在于通过信息操控削弱敌方的决策力与行动能力,但其复杂性使得传播效果难以完全预测。尽管信息强国通过技术优势和传播渠道压制信息弱国,传播效果却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流动的边界和效果愈加难以控制。这种复杂性为弱国提供了突破话语霸权的机会,推动信息传播的反向博弈。弱国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发起对抗,挑战强国的信息操控,在全球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非对称性博弈反映了国际舆论的动态平衡,传播不再是单向的控制,而是更为复杂的交互和对话,赋予弱者影响舆论的可能性。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仍以信息强国对信息弱国的单向压制为主,但这一局面并非不可打破。信息战争具有高度的不对称性,信息弱国可以凭借技术创新、灵活策略和跨国合作逐步反制。通过发挥“非对称优势”,弱国不仅能够影响全球舆论,还能借助联合行动和信息共享提升话语权。跨国合作与地区联盟的建立,为弱国提供了反制强国的有力工具,使其能够在国际舆论上形成合力,挑战信息强国的主导地位。在战争框架下,各国可以灵活调整策略,主动塑造信息传播格局,而非被动接受强国的信息操控。
战争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和群体行为在战争中的作用。武器化传播不仅是军事或政治行为的延续,更深刻影响社会心理、群体情感和文化认同。强国利用信息传播塑造他国的认知与态度,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然而,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武器化传播并非单向的压制,而是复杂的社会互动和文化反应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弱国并非完全处于弱势,相反,它们可以借助文化传播、社会动员和全球舆论的动态对抗,以“软实力”反击外部操控,塑造新的集体认同,展示“弱者武器”的正当性。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研究”(项目编号:24ZDA084)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Lasswell H D.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Clausewitz C V. 战争论:第一卷[M].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3]Herrman J. If everything can be weaponized, what should we fear? [EB/OL]. (2017-03-14)[2024-12-20].https://www.nytimes.com/2017/03/14/magazine/if-everything-can-be-weaponized-what-should-we-fear.html.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全文)[EB/OL].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906/t20190606_7947892.shtml.
[5]Mazarr M J, Casey A, Demus A, et al. Hostile social manipulation: present realities and emerging trends[M]. Santa Monica, CA USA: Rand Corporation, 2019.
[6]Bob Y J. Ex-CIA director Petraeus: Everything can be hijacked, weaponized[EB/OL].(2018-01-30)[2024-12-20].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ex-cia-director-petraeus-everything-can-be-hijacked-weaponized-540235.
[7]Mattson G. Weaponization: Metaphorical Ubiqu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Rejection of Politics[EB/OL].OSF(2019-01-08)[2024-12-20].osf.io/5efrw.
[8]Robinson L, Helmus T C, Cohen R S, et al. Modern political warfare[J]. Current practise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2018.
[9]Kreitem H M. Weaponization of Access, Communication Inequalities as a Form of Control: Case of Israel/Palestine[J]. Digital Inequalities in the Global South, 2020: 137-157.
[10]Laity M. The birth and coming of age of NATO StratCom: a personal history[J]. 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2021, 10(10): 21-70.
[11]Confessore N. Cambridge Analytica and Facebook: The scandal and the fallout so far[J]. The New York Times, 2018(4).
[12]McQuinn B, Kolga M, Buntain C, et al. Russia Weaponization of Canadas far Right and far Left to Undermine Support for Ukraine[J]. International Journal,(Toronto,Ont),2024,79(2):297-311.
[13]Stukal D, Sanovich S, Bonneau R, et al. Why botter: how pro-government bots fight opposition in Russia[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2, 116(3): 843-857.
[14]Jones M O. The gulf information war propaganda, fake news, and fake trends: The weaponization of twitter bots in the gulf cri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3(2019):27.
[15]Genovese D. Nearly 50% of voters said deepfakes had some influence on election decision. [EB/OL].(2024-10-30)[2024-12-20].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nearly-50-voters-said-deepfakes-had-some-influence-election-decision.
[16]Peters C, Allan S. Weaponizing memes: The journalistic mediation of visual politicization[J]. Digital Journalism, 2022, 10(02):217-229.
[17]Gorissen S. Weathering and weaponizing the# TwitterPurge: digital content moderation and the dimensions of deplatforming[J].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2024, 58(01): 1-26.
[18]Pascale C M. The weaponization of language: Discourses of rising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J]. Current Sociology, 2019, 67(06): 898-917.
[19]Ridwa1ah A O, Sule S Y, Usman B, et al. Politicization of Hate and Weaponization of Twitter/X in a Polarized Digital Space in Nigeria[J].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24.
[20]Mercieca J R. Dangerous demagogues and weaponized communication[J].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019, 49(03): 264-279.
[21]Welch C, Senman L, Loftin R,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the term “Weaponized autism” in an alt-right social media platform[J].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23, 53(10): 4035-4046.
[22]Farrell H, Newman A L.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J].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9,44(01):42-79.
[23]Clausewitz C V. 战争论:第一卷[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作者简介: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智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重庆 400044);康如诗,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重庆 400044)。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