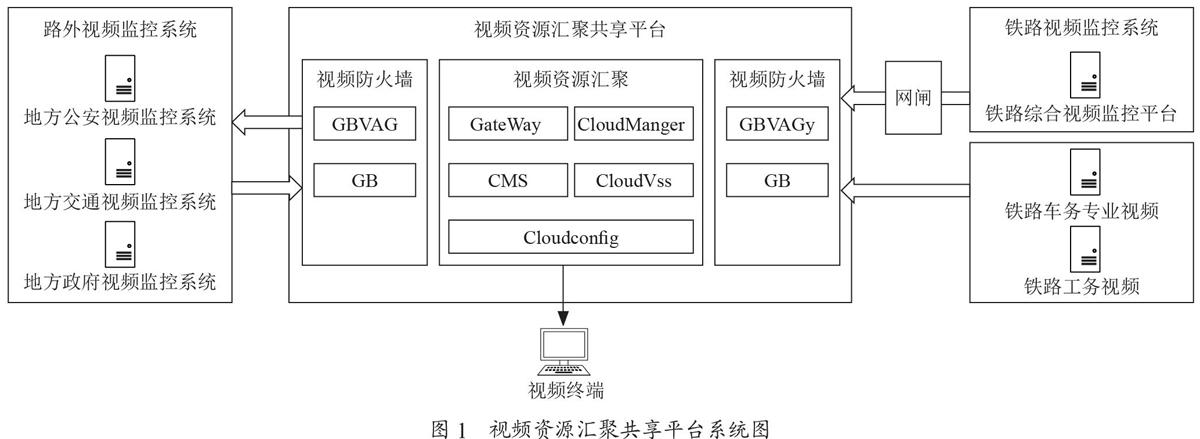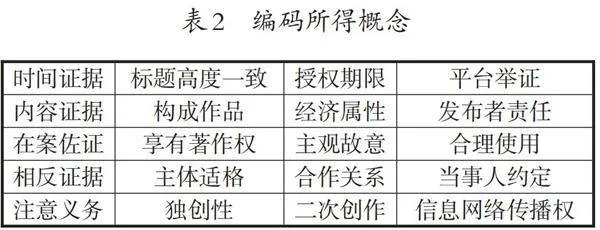【摘要】在视觉图像与移动设备的强力渗透下,短视频已然成为“景观社会”的主导性媒介装置。在短视频的视觉景观建构中,用户的沉迷问题日渐凸显。短视频沉迷的“景观表征”主要借由日常化的图像弥散、碎片化的景观积聚与娱乐化的视觉狂欢等进行体现。长期沉迷于短视频,容易导致用户主体虚置、观看行为畸变、媒介生态失衡以及社会审美错位等“景观异化”问题产生,需通过摆脱唯资本论、抵制算法黑箱、关注本真情境等治理路径拨开视觉的迷雾,形塑出理性化媒介实践范式。
【关键词】景观社会;短视频沉迷;治理路径;视觉文化;视觉媒介
在图像/影像技术不断浸润传播领域的日常实践中,人们业已形成的媒介体验日渐被视觉产品所主导。正如阿莱斯·艾尔雅维茨(AlesErjavec)所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自身在当今都已处于视觉(visuality)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1]从电影奇观到电视叙事,再到短视频狂欢,视觉性媒介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创构了一种流行的文化样态,尤其是在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裹挟之下,短视频凭借其精准化的信息推送和沉浸式的便捷体验,在大众媒介实践中占据一席之地。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50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5%”[2]。显然,短视频已成为视觉文化时代的重要产物和标志[3],并借由其独特叙事逻辑形塑人们的日常生活。
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Debord)曾用“景观社会”来描述以影像技术所主导视觉文化日渐凸显的社会形态。在德波看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推进,一个新的景观社会正在形成。在景观的价值认知中,视觉表象代替物质实在篡位为社会本体,从而通过视觉经验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认知与行为。[4]如今,短视频凭借其强大的视觉文化建构力将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经验,塑造成为诠释景观社会的新注脚。在短视频的媒介实践中,人们长时间沉浸于视觉景观的物体系话语之中,自我的身体感知与短视频的媒介经验产生了一种“胶合式”作用,从而诱发“短视频沉迷”问题。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移动端视听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3小时,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51分钟。[5]可见,刷短视频已成为“杀时间第一利器”,并引发沉迷问题。究其本质而言,短视频沉迷是媒介景观对视觉感官的隐性征服。
作为景观社会的重要视觉媒介形式,短视频凭借精彩的情节、声音和画面紧紧抓住受众的眼球,使其逐渐沉湎于浅层次的视觉消费与感官刺激,从而陷入一种奇幻缥缈的“沉迷之态”,无形之中破坏了人的主体性建构,对此需进行理性反思。然而,当前短视频沉迷的研究成果多从统计学、心理学等层面,考察环境、平台、技术等要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景观逻辑。基于此,本文立足视觉文化主导的景观社会,深入剖析短视频沉迷的表征形态、问题征候与治理路径,既为引导人们健康使用短视频提供可行方案,又对当代视觉媒介文化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一、景观生产:短视频沉迷的表征形态
用户沉迷于短视频,实质上就是沉迷在一个个相似的媒介景观中。[6]一方面,短视频平台庞杂的内容使用户沉浸在视觉消费盛宴之中;另一方面,用户的“主动”实践又助推了景观的进一步增值。当代社会短视频沉迷的景观表象主要通过日常化、碎片化和娱乐化等三个方面进行体现。
(一)日常化的图像沉浸
随着短视频沉迷现象的不断泛化,其中的景观生产表现出持续的视觉依赖性与弥散化特征。当代移动传输技术的便捷特性促使用户持续沉浸于短视频制造的图像刺激之中,形成深度的视觉依赖;受众的沉迷实践也与固定的空间场所逐渐解绑,收看变得经久不息、随处可见密切相关。
一方面,视觉刺激的过度依赖。短视频沉迷本质上是一种视觉消费活动,是视听符号层面的表意实践,这与景观社会的现实表象达成一致。用户置身于当代高度视觉化的媒介环境中,逐渐习惯于通过图像而非文字来获取信息。用户在观看短视频时,视觉注意力被高度激活,从而难以从连续、快速切换的图像流中抽离,导致对视觉刺激的强烈依赖。不仅如此,为了满足图像“需求”阈值,沉迷者往往追求更加刺激、新颖、独特的视觉体验,不断浏览、搜索新的短视频内容,以满足对视觉刺激的渴望,从而与景观社会的“视觉控制”产生深度勾连。
另一方面,沉迷场景的随处泛化。随着视觉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机屏幕上的内容已经不再限定于特定的节目产品,短视频沉迷现象已然充斥在大众日常的生活程式之中。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Mirzoeff)曾言:“现代生活就发生在荧屏上。图像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日常生活本身。”[7]在视觉主导的布展逻辑下,日常时间的一切存在都可以通过短视频媒介进行“还原”[8]与“再现”。与此同时,移动终端的易用性也使“刷短视频”的行为日渐摆脱空间桎梏,用户在公交、地铁,或是饭桌、沙发上,沉浸于指尖上划、双击点赞的身影都变得随处可见,如此一来,短视频沉迷现象凸显出随处弥散的景观化态势。
(二)碎片化的景观积聚
在这个快节奏的视觉消费时代,短视频所具备的短时限、轻量化等特点决定了用户沉迷实践碎片化的景观表征。用户一旦陷入了长时间的沉迷困境,那么资本则会悄然利用平台的技术黑箱,在支离破碎的视觉景观掩护下,使受众的媒介实践全盘搁置于其所搭建的意识形态框架中。长时间沉浸于短视频提供的浅层刺激和娱乐表象中,用户的自主意识与行为受到抑制,此时智能媒介默默地将碎片化的景象进行巧妙地拼贴与重组,并聚合为更大体量的视觉景观。具体来说,在用户的持续性沉迷实践中,短视频平台内部的智能算法打着为用户降低时间成本的旗号,实则为大众建造了一个个技术陷阱。通过对“用户画像”的不断细分,平台对受众进行了有效的分离,它以“兴趣”为轴心,将四面八方的碎片化内容重新打理、整合,源源不断地推送到受众眼前,最终使用户个体在“个性化”的“信息茧房”中积聚起独一无二的庞大视觉景观。在智能算法与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短视频平台中的碎片化景观被强力整合,为大众拼贴了一个“超现实”世界,在无尽的“个性化”景观推送中,用户对短视频的沉迷程度进一步加深。
(三)娱乐化的视觉狂欢
娱乐既是短视频沉迷的逻辑起点,也是其突出的景观化表征方式。美国媒介文化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曾言:“在多媒体文化的影响下,奇观现象变得更有诱惑力了,它把我们这些生活在媒体和消费社会的子民们带进了一个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9]“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10]美国媒介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对娱乐文化鞭辟入里的描述在短视频沉迷中更是得到充分体现。在当今的泛娱乐化时代,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充满戏谑意味的娱乐方式所表征,短视频沉迷自然难逃例外。当前,短视频沉迷的泛娱乐化趋势已经蔚然成风,商业化的平台逻辑为大众构筑了一个个富含娱乐元素的媒体奇观。在短视频沉迷的内容建构中,充斥着娱乐意味的配音、情节、特效等占据突出地位,其背后一方面体现出大众审美趣味和消费品位滑向短暂、娱乐化的流变趋势,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资本以及平台对公众娱乐化体验的培育和迎合,目的则是为了使用户沉迷在短视频景观中不能自拔。由此,通俗、轻松、娱乐、八卦等词汇开始成为最适宜释义当下短视频沉迷的修辞方式。用户不仅接收娱乐化的内容以满足“需求”,也旷日持久地投身娱乐化的互动实践中来。他们通过各种搞怪的特效、变形的配音来表达自我、获取认同,享受参与其中的愉悦感。在短视频的评论互动中,玩笑刻奇成为主流,沉浸其中的用户乐此不疲,共同构筑了短视频沉迷的娱乐化景观。
二、景观异化:短视频沉迷的存在征候
德波曾说过:“社会中的景观对应于一种异化的具体制造。”[11]短视频沉迷的景观生存境况之中隐藏了一种异化性话语,其引发的问题远不止对个体性的用户所造成的身心影响,而是在集聚到一定规模后渗透并影响社会的运转结构,导致社会稳定运行所依靠的伦理范式出现错位与失序。
(一)用户主体虚置:表象感召下的自我迷失
在景观社会的话语建构中,视觉表象成为资本与权力主体的代言人,其通过视觉途径制造的虚假意识形态将大众询唤为被动掌控的理想化客体,导致大众主体性的遮蔽。作为一种非理性化的媒介实践,短视频沉迷看似体现了用户的积极主动性,但究其实质,则是资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制造的无止境的接收模式。长期沉浸于短视频的视觉景观之中,受众逐渐迷失了资本的价值意识和技术的驯化逻辑,从而丧失主体建构的能力。
短视频平台借助社会背景中的视觉文化转向,不断向短视频的使用逻辑注入利益叙事,并在技术的深度伪装之下,在无形中塑造了受众无限被动接受的媒介实践情景。同时,短视频交互界面的配置方式也创造了无缝接续的娱乐体验,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使用便利[12],这种无感的交互模式促使用户沉浸到“无限滑动”的简单操作中,致使其在不经意间沉溺于平台所搭建的短视频景观中无法自拔,并一步步深陷短视频沉迷境地。
鲍德里亚曾发出警言:“我们被技术操纵简单化了,进入数字操纵阶段之后,这一简单化进程变得疯狂起来。”[13]当前碎片化、娱乐化的短视频沉迷导致用户出现认知不完整、知识接收能力下降等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其本身也陷入资本构造的技术陷阱无法逃离,造成对价值观念和自我认知的模糊与混淆。
“今天,不可避免的情形是,景观的强大吸引力已经把我们这一时代的大多数人变为了空想家。”[14]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本应是能够理性思考、做出理性决策,并追求智慧和真理的状态,而一旦长时间沉迷于短视频景观的生产与消费中,用户的价值观念便开始被资本营造的意识形态所驱使,最终成为资本为了压榨剩余价值而主观改造的无意识主体。
(二)观看行为畸变:价值剥削下的免费劳动
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经济类型,短视频平台追逐利益的商业手段本身无可厚非,但随着平台竞争的不断加剧,短视频这一影像媒介也逐渐显露出资本之间相互竞争的终极目的:将资本方以利益为主导的话语模式注入自身所形塑的视觉景观之中。
短视频景观对用户主体的无声感召旨在全面占有其闲暇时间,实现对用户时间序列的全方位剥削,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短视频不仅会要求用户长久地驻足观看,甚至会对观看这一行为本身也进行剥削。沉醉于景观体验中,人们对短视频的观看行为不再是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是为了填补资本培植出的虚假欲望。与此同时,用户拍摄的短视频内容也相应被资本作为营销和广告植入的原料,使其媒介实践异化为资本的免费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生产的视频内容则被无条件地吸纳至平台所掌控的后台数据库,并通过商品植入和广告推送等商业化整合手段,将被浸染了利益叙事的影像景观推送给更多受众。而平台则以几乎为零的原材料成本获取了巨额的经济收益,与之相对,用户却仅得到了少量的“流量激励”或“创作补贴”。如此一来,平台资本对用户的剥削也由观看行为延伸到生产过程中,个人的视频上传举动成为资本增值的有力方式。两者结合之下,“沉迷”超越了时间向度,使得用户的观看与上传行为异化为资本的免费劳动。
(三)媒介生态失衡:图像崇拜下的理性缺失
在传统的哲学认知中,视觉被视为能够提供有关对象的“客观”信息,并且视觉所传达的信息有助于人们进行反思和抽象,并由此形成对世界的深刻认知。视觉经验是一种不会引致欲望放纵的经验,相反,它会在对对象的距离性沉思中净化人的灵魂,把人从对对象的占有或依附状态引向纯理智的静观,引向德行的实践。[15]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当前短视频沉迷的景观生产中却充满了欲求快感体验与浅层的视觉沟通,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评价技术与感官的关系时所说,“工具延伸了人哪一方面的能力,人的那些方面就必然会变得麻木”,短视频的沉迷使用泛化了视觉感官的调用,视觉传输技术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距离,图像合成技术更是使观看对象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此,当代关于视觉支配的批评多数假定:一种视觉支配的文化必定是贫乏的或者是精神分裂的。[16]在短视频的沉迷实践中,用户所追求的并非理性认知,而是贯穿于表象与浅层的感官体验,专注于瞬时刺激和即时快感的心理欲望。短视频平台通过提供视觉上的引人入胜、娱乐碎片化的内容,成功地引导用户对于瞬间感官刺激的追求,形成了一种感性驱动的沉迷模式,这与传统视觉体验中的理性追求大相径庭。
(四)社会审美错位:文化工业中的内容同质
在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所提出的文化工业中,媒介技术为当代社会制造了大批量、同质化、覆盖广的文化,并且这种千篇一律的文化样态会使审美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当前短视频沉迷中的景观同质化特征愈加凸显,用户所沉迷的内容看似花样繁多,但本质上都是千篇一律的景观生产模式。这种精心策划的技术逻辑与商业结构,背后正是文化工业大批量、同质化的生产过程体现。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用户黏性,短视频平台倾向于向用户推送符合当前流行趋势的内容,这使得审美标准不断受到平台主导的影响,造成了审美趋同的后果。此外,平台还通过运作明星、网红等资源,将独特的审美标准转变为营销手段,使特定审美趋势成为社会热点,用户在追逐这些热点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模仿,从而进一步导致审美标准的统一化。
三、重返本真:短视频沉迷的治理路径
在视觉景观日渐凸显的当下,短视频沉迷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短视频沉迷治理需通过剥离景观的掩饰外衣,深入剖析沉迷现象的核心症结,有效对短视频沉迷过度视觉化的景观进行解构,从而促使个体回归至短视频实践的本质与初衷状态。
(一)摆脱唯资本论,释放平台活力
在资本逐利席卷数字空间的浪潮下,短视频也未能逃离其侵蚀与掌控。在市场逻辑的框架布展中,充斥着娱乐、刺激、快感的内容会在短时间完成裂变式渗透传播,获得较大的经济价值。[17]当下短视频平台的各个运行环节逐渐被资本所渗透,处处显现出商业逐利的话语模式。对此,短视频平台迫切需要超越经济效益至上的生态桎梏,以释放平台内生的无限活力。
一方面,关注多元需求要素。资本逻辑运作下的短视频沉迷表面上扩大了观看的总时长,然而实质上,这一趋势将用户与平台内在的多样活跃性削减至一种单一化的产销模式,使得短视频平台内在的活力与价值遭受显著削减。因此,短视频平台不应仅将流量和收益作为唯一发展指标,而是更为全面地关注用户的文化感知、社交互动等多方面的需求要素。短视频平台可通过采纳更为多元化的经营策略,引入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选择,从而减轻对短时刺激性内容的过度依赖。
另一方面,注重社会责任引领。在当前社交媒体格局中,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引领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和文化表达方式,为了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短视频平台必须从纯粹追逐经济利益的角度转向更为全面的社会责任视角,充分认识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其不仅应被视为一种商业工具,更应在文化媒介和社交媒介的多元属性中找到其根本存在的意义,从而摆脱单纯资本逐利的工具化取向。由此观之,短视频平台急需调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打破沉迷式的景观构境,释放平台与广泛用户群体内在的无限活力。
(二)抵制算法黑箱,打破虚假构境
算法在短视频沉迷的景观生产中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信息科学领域中的“黑箱”概念常用于描述人们无法洞悉内部结构和相互作用的系统或领域。类似的,短视频沉迷所依赖的算法也呈现出“黑箱化”特征,其内部运作机制和决策过程对用户并非透明可见,数字时代的算法规制愈加高度复杂化、精细化和隐蔽化。[18]唯有远离技术使用中的黑箱效应,才能打破技术所构建的虚假场景,缓解用户对短视频的沉迷程度。
首先,纳入公共价值。短视频应校正算法的价值导向,充分纳入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观念与公共意涵,以确保算法的运作与推荐过程不仅仅服务于个体用户的偏好,更要积极促进社会利益与公共服务。平台应通过算法对于短视频中的信息进行提取和分类,优先推送具有教育意义、文化传承、社会公益等属性的内容。同时,通过算法分析受众对内容的反馈和评价,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内容推荐,拓展算法的应用场景,识别并推送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短视频作品,从而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强化其理性的视觉实践。
其次,保障用户权利。景观社会中的短视频沉迷是一种被动建构的结果,此时平台应在运行逻辑与交互界面方面追求更高程度的用户参与和选择权。例如设定个性化的偏好与兴趣标签,以及选择不同的浏览模式,从而赋予其更加个性化、灵活的使用体验。进一步,平台应提供过滤和屏蔽功能,使用户能够主动管理和控制其观看体验,避免被动沉溺于虚拟的视觉景观之中。
最后,提升审美追求。在面对技术本身所具备的工具理性时,“审美现代性”或许可以调和其对于商业利益的追求。当前短视频景观背后的算法生态唯有增加对用户使用体验的关注,提升对内容审美的追求,才能打破无限循环的虚假构境。对此平台则应建立完善的视频审核机制,确保上传的视频内容符合审美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并通过内置算法推广、引领用户对高质量内容的追求,不断提升短视频的视觉审美水平,为观众带来更加美好的观看体验。
(三)关注本真情境,破除影像壁垒
解除短视频沉迷景观化的蒙蔽状态,亦需公众自身的主动实践。德波倡导公众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入手,关注本真的生活情境,以此来打破传媒所塑造的景观壁垒。用户如果能够正确遵循德波的理念,现在仍不失为一种对抗沉迷景观的有效方法。
一方面,提高真伪辨别能力。短视频所呈现的内容实质上是一种拟态化的影像壁垒,其与真实生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分隔,短视频内容并非直接反映实际生活的全貌,而是经过编辑、压缩和美化后的艺术化再现。因此,用户应当意识到短视频所呈现的景象并非直接等同于真实生活,而是一种经过筛选和构建的虚构表达。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用户有必要及时切断与短视频内容的过度联结,防止沉溺其中而无法摆脱。同时,大众应积极关注实际生活,将日常生活纳入对抗短视频平台虚构影响的实践之中,保持对真实社交、现实事件、个人成就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积极参与,以确保在面对虚构的内容时,仍能够保持辨识真假的敏感性。
另一方面,重视现实情境再现。在短视频内容的生产实践中,创作者要关注真实的生活情境,通过再现日常生活的本真情境,来打破资本与技术构筑起的景观伪世界。在短视频创作领域的生产实践中,用户与创作者应抗拒虚拟情境、虚构情节以及夸张动效的泛滥趋势,其过程既是一种审美追求,亦是对文化媒介伦理的审视。广大创作者要通过精心建构日常生活的本真情境,扭转由资本与技术合谋塑造的虚构景观,以实质性手段重塑观众的视听体验。这种努力不仅仅是对技术和资本逻辑的反叛,更是对社会虚拟化与同质化的审美抗衡。借助于真实情境的还原,短视频创作者能够再现一个更为深刻、真实且有意义的视觉文化空间,为观众提供更为丰富的审美层次与娱乐体验,如此方能有利于解构短视频沉迷所构筑的强大景观壁垒。
四、结语
随着图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渗透,短视频以碎片化、虚拟化以及泛娱乐化的内容形成对大众视觉感官的吸引,致使大多数用户都沉迷在视觉盛宴的景观消费体系之中。短视频景观化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拨开景观化的表象,其背后对用户心理与行为的掌控才是更深刻的问题。毋庸置疑,在移动互联和视觉图像的技术驱动下,短视频媒介所创构的景观文化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进行普泛化渗透,并在技术、资本等多重物体系的逻辑建构中对用户进行了一种隐形的感知操控,从而导致沉迷问题发生。在短视频沉迷的景观逻辑中,可视化图像的致密程度不断增加,流通于社会中的视觉信息日渐呈现出一种“生产过剩”的状态,无形之中破坏了信息生态的平衡稳定,诱发社会大众媒介实践行为的盲目性,因此“有克制”的理性化媒介使用行为才是这个时代所推崇和期待的实践方式。简言之,短视频所形塑的视觉景观社会比任何一个视觉产物主导的时代都更加期盼秩序与理性的复归。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青少年的短视频沉迷与治理研究”(编号:23BXW09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阿莱斯·艾尔雅维获茨.图像时代[M].胡菊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3]刘海明,何晓琴.观看的向度:短视频景观下个体视觉消费行为的伦理审视[J].新闻爱好者,2022(7):11-14.
[4]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5]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2024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EB/OL].(2024-03-28)[2024-12-10].http://www.cnsa.cn/art/2024/3/28/art_1977_43660.html.
[6]聂艳梅,吴晨玥.短视频景观的成因透视与文化反思[J].云南社会科学,2020(05):164-171+189.
[7]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
[8]赵红勋,宋文凯.时间的媒介化:短视频对时间话语的重塑[J].新闻爱好者,2024(11):35-38.
[9]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
[1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2.
[11]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2]晏青,陈柯伶.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短视频成瘾的媒介可供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90-101.
[13]让·鲍德里亚.为何一切尚未消失[M].张晓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88.
[14]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M].梁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
[15]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J].文艺研究,2006(01):84-96+159.
[1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0.
[17]赵红勋.从“变形计”看青少年的媒介形象及其对价值观的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18(04):88-94+101.
[18]刘河庆,梁玉成.透视算法黑箱:数字平台的算法规制与信息推送异质性[J].社会学研究,2023(02):49-71+227.
作者简介:赵红勋,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郑州 450046);郭锦涛,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郑州 450046)。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