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
新媒体与我国出版业的四个变动
□王鹏飞
转企改制之后,我国出版业完成了内部体制上的变革。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则改变了出版业的外部环境,引起了不小的变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资本领域,互联网巨头的进入与众筹的问世;产品开发领域,由单一出版形态转变为IP策略的全版权模式;阅读形态领域,电子阅读终端在兴盛几年之后,引起了纸质图书的回潮;发行领域,全球市场的拓展。
新媒体;出版业;众筹;IP模式
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在体制上面临的最大变革莫过于转企改制。201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明确了“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进行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的改制目标,对发轫于2003年6月的出版业改制发出了最后的冲锋令。此后两年时间之内,除人民出版社等两三家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外,我国出版社全部注册为企业法人。如果说转企改制属于出版业内部体制更新的话,那么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则使出版业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引起了我国出版业从资本到内容、从渠道到产品等多方面的变革。
一、资本:跨界联合与众筹的诞生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之后,资本问题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头等大事。为了能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长袖善舞,不少出版机构都在资本上做文章。早在2008年11月18日,安徽出版集团组建的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A股借壳上市,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主业第一家整体上市的出版企业。此后几年间,江苏的凤凰传媒集团、湖北的长江传媒集团、河南的大地传媒集团等诸多出版企业相继上市。如果算上2007年就带着编辑业务试水IPO的北方传媒集团,可以说,当前的出版企业寻求上市获取资本成为业内的一个常态。诸多上市出版企业的共同特征在于大都具有深厚的政府背景。虽然从事业单位变为企业单位,进入的却是国企行列。因此,在上市之后,诸多出版企业全方位开展各种业务,譬如凤凰传媒集团涉足房地产等,但都是在国企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业务拓展和运作。偶尔也有一些如江苏可一文化这样的民营文化企业,因为没有掌握书号资源,只具有一些图书工作室或者发行商的特征。而新媒体的诞生,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出版业的资本运营提供了新的借鉴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线上网络巨头的强强联合。这些网络公司不仅进入出版或阅读市场,而且还向线下渗透。2015年1月,腾讯公司宣布成立阅文集团,3月16日正式挂牌。阅文集团的成立,基于腾讯与盛大文学联合的背景。合并之前,盛大文学已经耕耘国内在线阅读和创作平台多年,占据了我国网络原创文学市场七成以上的份额,运营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小说阅读网、榕树下、潇湘书院、言情小说吧等原创文学网站,还拥有华文天下、中智博文和聚石文华三家图书策划出版公司。腾讯的优势在于数量惊人的用户群体以及用户黏合度。腾讯与盛大的联姻引起了大众的一片惊呼:今后中国看书也要“企鹅”了吗?惊呼未了,仅不到半月时间,2015年1月27日,网络三强BAT之一的百度,依托百度文学旗下的“熊猫看书”,携手苏宁云商旗下的数字阅读品牌“苏宁阅读”,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百度与苏宁在数字阅读方面的合作是两家互联网巨头通盘合作的一个延续,不一定是针对腾讯与盛大合作的即时反应,但互联网巨头之间的跨界联合,却开创了出版业资本联合的新样态。一方面是腾讯和百度侧身数字出版领域时,很容易依托巨大的用户群体取得压倒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互联网线上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线下渗透。腾讯联手的盛大文学,有三家影响甚大的图书策划出版公司,已经征战出版业多年。百度牵手数字出版新秀苏宁数字阅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中了苏宁线下1600多家门店资源,不啻为另一类型的“新华书店”。就此而言,相较于传统出版集团借助上市募集资金而言,腾讯、百度与出版业的联合早已超越了单纯资金流的层次,进入了读者群体和渠道合作的新阶段。
第二种模式是线上众筹。面对网络巨头动辄数亿元的资本联合,中小出版商缺乏这种多钱善贾的豪气,尤其是某些阅读群体细分明显的图书,想获得前期的出版资金,哪怕只有几万元,好像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新媒体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为小额度的资本众筹带来了可能。所谓众筹,即crowdfunding,是来源于美国Kickstarter网站的资本募集方式。与前面所说的出版企业上市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依靠大众的力量。但众筹与上市公司的区别就是,众筹依靠网络平台进行募集,是个体化或私人化的行为。
2014年11月18日,河北教育出版社对《陈超诗文珍藏版》上线众筹,30天的众筹期结束时,获得了5.8万元,圆满成功。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众筹举动,是出版机构涉足众筹的先驱。此前的众筹,主要是作者或出版代理人的个体行为。2014年7月,腾讯徐志斌的《社交红利》,2014年8月360董事长周鸿祎的《周鸿祎自述》,都已经在试验众筹模式。而2015年4月上市的《微信营销108招》,还未出版即已众筹128万元,号称国内草根众筹第一书。就此而言,新媒体带来的众
筹模式对于小众化的出版物,提供了可行的出版资金解决方案。譬如陈超先生的诗文,固然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但若由行政命令不计成本地出版,一方面违背了出版业市场化后成本核算的初衷,另一方面以传统的销售模式,也未必能精准地找到应有的读者,发挥其社会价值。这两个问题在众筹面前迎刃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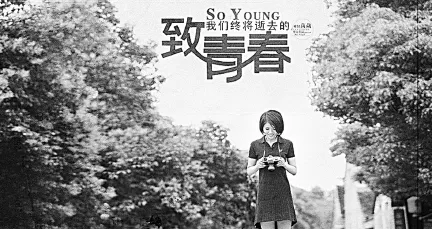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二、产品:单一出版与IP热潮出版业所指的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即知识产权或所有权。就此而言,IP不是一个新潮词语,但近两年新媒体的发展,却让IP模式借助不同媒介,进行系统的全版权运营和开发的模式,成为出版业的一个新亮点。
此前的出版行业内,一部图书效益最大化的办法,是尽力使其销量最大化,在边际成本递减之后,通过不停地重印,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因此十年前的作家富豪榜,很多是以码洋来计算的。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虽然曾改编成电视剧,但触电后的显性效应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纸质图书销量提升上面,从电视剧改编上获得的效益寥寥无几。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兄弟单位四川文艺出版社提起诉讼,也是因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销量达十余万册,影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的效益。这种围绕着某个纸质图书进行大力开发的策略,成为新媒体之前大多出版社运营的主要思路。
新媒体的兴盛,使出版商看到了一部作品跨界的可能性。2003年底,《手机》上映,与此同时,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纸质版的长篇小说《手机》,被视为影视同期书出版模式的尝新之作。2005年年底,电影《无极》上映,此后郭敬明根据电影改编了小说《无极》。2008年12月,《非诚勿扰》上映,与此同时,小说《非诚勿扰》以传统图书、互联网、电子书、手机阅读等四种形式同步出版,第一次试行了全媒体出版战略,可以说是当前出版界IP出版模式的排头兵。到了当下,出版业的IP模式,无论是在出版意识上还是在跨界范围上,都有了质的改变。
新媒体带来的IP模式,主要体现在青春题材的网络文学上。2010年,笔者曾提及当时青春文学兴起的特点,“一是阅读群体的青春化”,“二是作品内容的青春化”,“三是写作队伍的青春化”。[1]五年之后,以青春阅读群体为基础的青春文学,成为出版业内IP模式的领头羊。随意翻检近两年的出版业作品,就发现自《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开始,《岁月无声》《同桌的你》《小时代》《匆匆那年》《后会无期》等电影相继问世。2015年前五个月,已有《万物生长》《左耳》《何以笙箫默》《年少轻狂》《重生爱人》等影视作品纷纷上映。接踵而来的《至少还有你》《我是愤青》《栀子花开》等已经进入院线的档期,其余如《谁的青春不迷茫》《沙漏》《泡沫之夏》《夏有乔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青春小说都已走在影视开发的路上。如果说青春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还只是十年前冯小刚等影视同期书的路子,那么当前青春读物的IP出版,则是在影视改编之外,进一步延伸到了游戏、动漫、音乐、玩具等各产业领域。以《小时代》为例,这部曾经风靡一时的小说,如今已经成功跨越电影、电视剧、网络剧、音乐剧,并大有开发周边商品的势头,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已成为当下最有品牌价值的IP之一。也就是说,青春文学的IP打造的是文学出版立体化的产业链。
IP模式在青春出版物上尝试和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的青年读者群体。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的读者群,青年读者对于新媒体的接受和使用具有天然优势。因此,当出版内容溢出纸媒,向影视、游戏、动漫、音乐等周边产业延伸的时候,青年读者群体是最容易接受的。或许正是因为青年读者群体对于跨界的天然喜爱,促进了IP出版模式在青春文学上的率先成功。这种成功的意义,不仅为出版业试验了全版权或全媒体出版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试验了纸媒之外其他文化产品之间的相互延伸。比如以音乐为基础改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生有你》,以游戏为基础改编的《诛仙》《龙卫白典》《我叫MT》等系列游戏视频,还有《洛克王国》《龙之谷:破晓奇兵》《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等电影,以及动漫、周边开发等联动,都为今后的IP出版探索了一条出路。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对IP出版的应用更多的是郭敬明这样的年轻导演或者民营影视机构和图书工作室,或许这也意味着,对于新媒体的“新”这个特点而言,传统出版集团还应增强自己的敏锐性。
三、阅读形态:Kind le与纸质图书的升温说起读书,无论是春秋时期孔子“韦编三绝”的描述,还是唐代杜甫“读书破万卷”的感慨,抑或清末民初叶德辉对“书之称叶”“书之称本”“书之称卷”等的考辨,都意味着图书是一种可以感知并摩挲的实体形态,除填补玄远的精神空间之外,还要有实体空间的存在感。但这一切,随着新媒体的到来,都发生了改变。
2007年11月19日,第一代Kindle正式发布。2010年3月,第一代iPad正式发布。此后的日子,以Kindle为代表的阅读终端和以iPad为代表的平板电脑一起拉开了风生水起的电子书阅读时代。再加上越来越大的手机屏幕,一时之间,满城尽带“大平板”,众人皆为“低头族”,这一切成了当前阅读的流行景象。电子书在短时间内攻城略地带来的压迫感,使纸媒已死的论调很快成为出版业内普遍的担忧。
然而对于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纸质图书而言,面对近十年新媒体的冲击,似乎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脆弱。经历了短期的兴奋之后,一块电子屏幕带来的阅读体验与散发着油墨气息、装帧各异的纸质图书带来的阅读快感的差异,令读者有了更深的感受。曾有一幅流传于网络的漫画,从侧面展示了纸质图书的某些优点。漫画中,一本打开后扣在桌子上的图书,对着一个电子阅读器叫板:怎么样,你能像我这样劈叉吗?面对纸质图书的叫嚣,阅读器害羞而颤抖的身影代表了数字阅读的“心虚”。面对着历经沧桑的纸质图书,Kindle们恐怕还只是通往下一个阅读时代的“过渡产品”。
关于电子书与纸质书的对比,美国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的报告显示,在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电子书的市场份额相较于前两季度的23%下滑到21%。此前的调查也显示,虽然2007年Kindle面市以来电子书在美国增长极快,然而近年来电子书急剧扩张的势头逐渐减弱,2013年,其销量增长率从之前的三位数骤降至一位数,2014年继续滑落。即便Kindle推出新款阅读器仍无力回天。与此同时,美国纸质书市场2014年则增长2.4%。作为世界第一出版强国,美国的电子书与纸质书的对比数据,彰显着纸质书已经站稳脚跟,并开始回暖。[2]这一点,我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数据,诸如《被高估了的电子书》[3]等都反映了这个问题。与纸质图书的升温相呼应的则是实体书店的转型。自从网络开始售书之后,我国的图书发行转变为实体市场与网络市场的纷争。网络图书市场中,京东网、当当网、亚马逊中国占据着前三名。2012年6月上线的天猫书城,则在京东等三巨头的B2C书城模式之外,开创了平台书城的模式。网商巨头的举措促进了图书销售的发展,但对于实体书店而言,却越发感受到空间的挤压,不少实体书店纷纷倒闭。为了谋求生存,一些实体书店开始从单一的售书功能进行转型。2014年4月23日,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正式营业,一年之后,在清华大学东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增开了第二家24小时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举措,与其说是全天候售书的尝试,不如说是以李克强总理的回信来定位更加准确,即“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让更多的人从知识中汲取力量”[4]。与此相似,不少城市近来不惜以政府之力支持实体书店,更大程度上还将书店打造成为一个文化地标,而不仅仅是挽救其作为售书渠道的功能。
就此来看,新媒体对于出版业的阅读形态而言,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激进式的参照。使出版业看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数字阅读之后,温润厚重的纸质图书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至少相较于虚拟形态的电子图书,纸质图书借助个体的装帧美感,更有利于打造一个文化空间,使之成为当前安抚社会浮躁心灵更好的载体。这一点,恐怕是纸质书与电子书之间的一个最大差别。

《消失的地域》
四、发行:全球市场的拓展1985年,媒介环境学家约书亚·梅罗维茨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消失的地域》一书,论述了电子媒介的使用及其为我们带来的新社会环境。对于电子媒介,梅罗维茨认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密切的联系”[5]。如果抛却梅氏使用的场景理论,将新媒体的影响用于出版业的发行来说,“消失的地域”或许是非常恰当的一个定位。
对全球化的拓展,出版业已经有了诸多尝试。2014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images公司),借助其品牌价值和固有的海外销售渠道,重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2015年5月27日开幕的纽约书展上,中国宣告中国出版集团美国出版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出版集团在海外成立的第一家独资出版公司。这些举措都预示着我国出版业为走出去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而对于图书发行区域的全球市场拓展,依托新媒体,国内电商很早便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
一是网络电商提供的全球网购平台。在网上售书平台的分类中,亚马逊中国和京东基本被分为B2C的模式,但二者除自售图书之外,也都建立了平台提供功能。以亚马逊为例,依托于全球连锁的商业模式,推出了“亚马逊全球开店”计划,宣称借助其世界领先的物流服务,能接触到全球2.6亿的活跃用户。对于中国出版业的发行来说,网络电商最大的功绩是提供了全球范围内接触中文图书的渠道。对于任何一本中文图书而言,全球读者都可及时在京东或天猫上找到目标图书。借助全球化的快递服务,目标图书也可较快到达读者手中,打破了实体书店地域的限制。
二是电子图书的全球发行。2013年8月28日,在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国际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易阅通”启动运营。“易阅通”在中国数字出版资源的全球发行方面,凭借60多年构建的国际化营销渠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易阅通”已聚合国内外数字资源130多万种,依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资源优势,“易阅通”与中华书局等签署了内容合作协议,积极打造中国古籍、法律、文学等多种专业图书数据库。同时通过与Overdrive、Dawson Books等国际数字集成商签订的双向合作协议,打通了中国数字资源销往国外的4万多家图书馆等机构用户和100多万个人用户的渠道。与此相类似的百度阅读是一个更为便捷的全球图书销售平台。在它的首页上,显示着与国内数百家主流出版机构合作的宣传词,有着多平台畅读与全网最低价的承诺。相对纸质书全球销售路途遥远的缺陷来说,即购即得的电子书销售模式,成为新媒体时代中文图书走出去最便捷的路径。在这种条件之下,我国出版业的走出去战略,所需要的就是在内容上如何获得海外读者的青睐了。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孤岛文学期刊研究”(13YJC751056);江苏省博士后项目“英美数字出版法规研究”(1301009C)的成果之一]
[1]王鹏飞.跨媒介时代的文学出版之变及其趋势[J].出版广角,2010(4).
[2]钱好.美国电子书销量出现回落[N].文汇报,2015-01-13.
[3]宋雯.被高估了的电子书[N].文汇报,2014-08-17.
[4]储信艳.李克强给三联书店回信[N].新京报,2014-04-23.
[5]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6.
(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