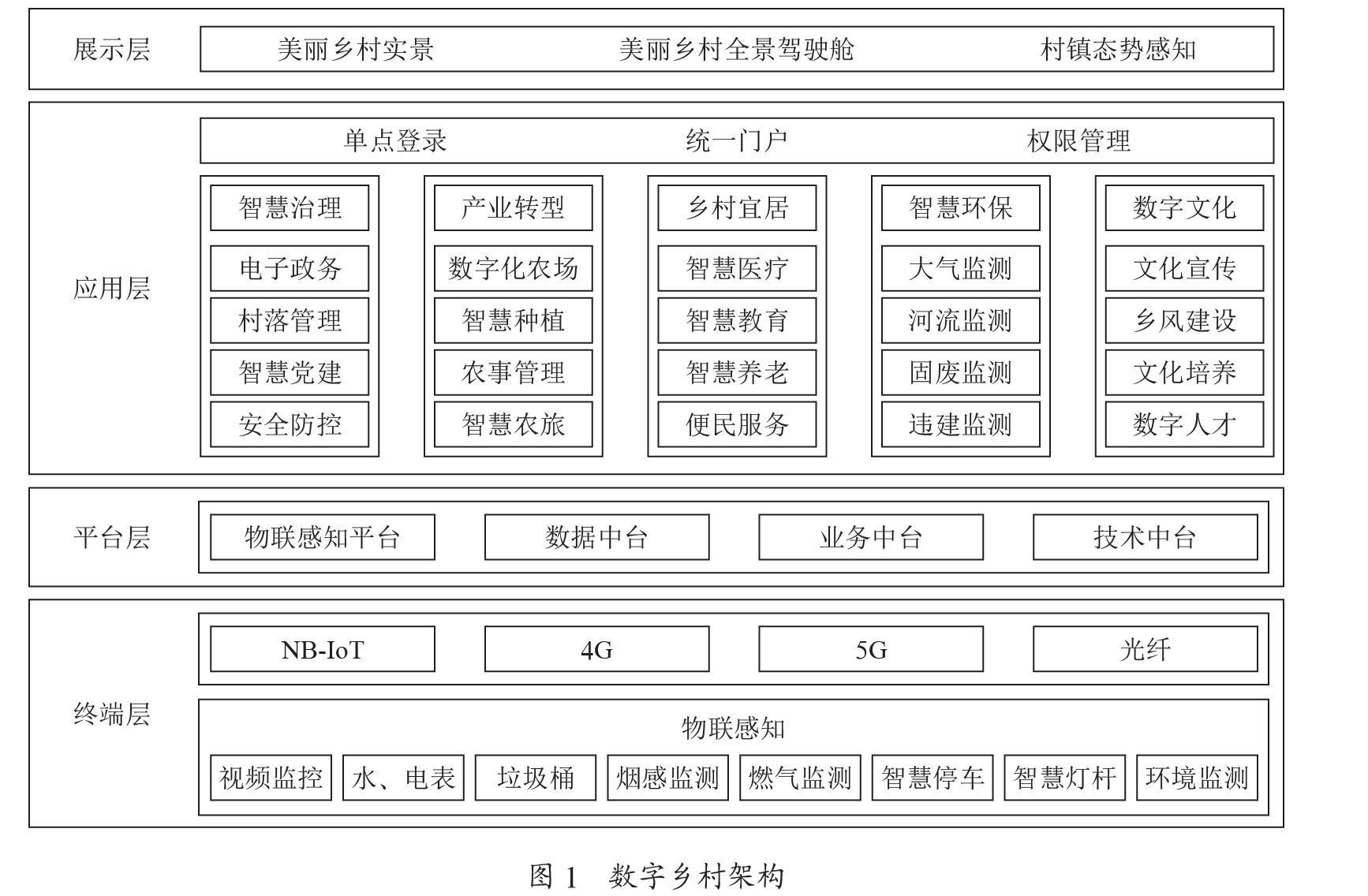【摘要】在融媒体时代,乡村题材综艺节目运用多元化的叙事元素和叙事技巧展现了中国农村形象和当代农民生活图景。乡村题材综艺节目的叙事模式体现出主题时代性、情节开放性、人物主体性,在叙事话语方面呈现出并置与延展的叙事时间、仪式与符号的叙事空间、平视与散点的叙事视角。未来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应该通过明星素人共建、深耕乡村人文,破除商业化对文化主题的消解;情怀情感交织、纪实抒情相融,应对泛化情感稀释深层叙事;以乡村实践引领、从乡土生活出发,避免虚拟景观替代乡村原貌,以影视艺术的独特活力和动力,讲好乡村故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融媒体;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叙事模式;叙事策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缩影。以乡村为题材的综艺节目紧跟融合时代浪潮,利用影像艺术的独特优势构建起中国农村形象和当代农民生活图景,成为认识乡村、了解乡村的窗口。乡村题材综艺节目以农业发展和农村生活为焦点,展示农业发展和农村生活,表现农村人民的精神面貌,描绘出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迁的中国乡村形象和乡土记忆。然而,当前乡村题材综艺节目也出现过度商业化和情感表达泛化的倾向。关注乡村题材综艺叙事策略,不仅有助于探索更适合融媒体语境下影视助力乡村发展、驱动产业建设的节目生产方式,也能够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指引乡村题材综艺节目未来可持续发展。
一、融媒体语境下乡村题材综艺节目的叙事模式
(一)叙事主题:彰显时代性
乡村题材综艺的叙事主题作为节目叙事故事的核心,受到农村发展和政策的影响,积极承担着文艺节目的社会责任,呼应时代召唤。一方面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向引导下,乡村题材综艺节目挖掘农村发展中的现实话题,有意识地将政策宣传、农村干部、新农村新风貌、农村产业发展、农村文化、田园风光等主题逐步纳入叙事;另一方面,从农村实际出发,沿着乡村振兴的路标引导,采用纪实的手法,探索将宏伟时代主题具象化为贴近乡村人民生活主题的最佳路径。
如果说文旅类乡村综艺节目如《美丽乡村中国行》还只是停留在浮光掠影式的自然风光欣赏和田园牧歌式的文化想象,体验竞技类的乡村综艺节目则已经开始主动表现城乡差距,《变形记》探讨农村教育、留守儿童,《囍从天降》表现代际冲突,《爸爸去哪儿》和《奔跑吧兄弟》呈现乡村丰富的精神文明。而纪实类慢综艺节目则以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在散文式的生活流程中串联起农业生产、家庭分工、村庄社会这一系列场景,从中自然显露出乡村风情的美好和农事劳动的艰辛,血缘纽带的温情和家庭代际的传承,人情社会的淳朴与集体发展的困境,组成形散而神不散的全景式新农村时代画卷。《奔跑吧·共同富裕篇》立足于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共同富裕奋进的时代节点,用嘉宾“奔跑”的形式串联起浙江、福建两省乡村的纪实性镜头,为观众展现现代化“三农”新气象,展示农村文化、生态和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新时代农民奋斗的精神风貌。
乡村综艺节目的叙事主题牢牢抓住时代脉搏。节目通过对乡村自然风光的描绘,展现了乡村的美丽宜居;通过对乡村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呈现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和新时代农民的奋斗故事,展现了乡村在新时代的巨大变革和发展成果,以及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创造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样层层递进、逐渐深入的主题呈现,为观众娓娓讲述了中国式的当代乡村故事。
(二)叙事情节:保留开放性
叙事学将情节定义为由故事中通过一系列话语组合起来的事件。以功能为依据,情节可以分为解决性情节与揭示性情节。早期的乡村题材综艺中大量使用解决性情节,由节目组设置既定的任务,嘉宾设法完成任务,并应对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在文旅类综艺节目《乡村合伙人》中,嘉宾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所旅游的村落开发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产品,而在体验竞技节目《漂亮的房子》中则是对村落中的房屋进行改建,以方便村庄开发文旅产业。类似的任务还出现在纪实类慢综艺节目《哈哈农夫》中,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什么”的基本问题成为这些节目的叙事动因,而受到乡村条件的限制,产生的问题往往是类似的,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嘉宾和节目组的共同努力下得到解决,任务由此得以完成。
在传统媒体时代,解决性情节能够凭借问题是否成功解决的悬念感而获得观众青睐,而进入融媒体时代后,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使得受众倾向于选择更加丰富多义、有更多参与感和更多互动性的表意情节。[1]揭示性情节通过为观众提供揭示事件状态的开放性话语,淡化节目流程中的冲突与对抗,充分利用融媒体的优势,采用“大屏+小屏”全面展示人物生活和乡村背景的细节。《极限挑战·宝藏季》一改竞技游戏类节目以游戏任务冲突为核心情节事件的传统,采用“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跟随着嘉宾探寻“宝藏”的脚步深入到祖国各地,展现时代转折之际的乡村一方和历史一隅,对抗元素进一步弱化。乡村的种种问题和现状并没有被“解决”,而是由镜头如实记录呈现,在节目记录的乡村场景和现实之外,是给观众想象和反思的“留白”。
(三)叙事人物:凸显主体性
乡村题材综艺节目主要人物从以自然景物为主不注重人物塑造,到利用明星制造热点话题吸引观众观看,再到以明星为线索,积极邀请素人参与节目共同完成内容叙事的转变,完成了去中心化和凸显个性的理念更迭。
早期乡村题材文旅类节目重点在于呈现地域旅游资源,人物并不是叙事的主角。体验和竞技元素加入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后,节目镜头几乎全部对准明星,满足了观众的窥私欲和追求紧张刺激体验的需求。《明星到我家》选取四位女明星为主角作为“媳妇”到云南普洱体验农村生活。节目通过一系列生活习惯和观念的冲突,塑造出长期生活在城市不事劳作的都市女性形象,并凭借由此产生的城乡差异碰撞来推动情节发展、引发观众讨论。
而纪实慢综艺节目坚持走基层路线,一般选取“明星+素人”“固定嘉宾+飞行嘉宾”的组合作为节目主角。人物成为自主性存在体,其“整体”和“个性”都是通过纪实性镜头中日常细节的流露来体现的,对他们的塑造是开放的、全面的、立体的。《云上的小店》通过村民顾客串联起山林守护者、留守儿童、留在乡村发展的年轻人等各种各样的平凡人,从中发掘普通人的人性光辉和当代乡村的切实问题;《向往的生活》邀请到武大靖、刘国梁、惠若琪等体坛明星分享成长故事和乡村记忆,为观众树立奋斗幸福观;《亲爱的客栈》将客人和明星主角的人生故事结合叙述,探讨当代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普遍症结。更为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也使得节目主题更加多元、深刻,为乡村题材拓展了表意空间。
二、融媒体语境下乡村题材综艺节目的叙事话语
(一)叙事时间:并置与延展
传统的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叙事以顺序叙事为主,将倒叙、插叙修饰其中,形成较为流畅的线性叙事结构。一方面综艺节目选取最有戏剧效果、最典型化的事件展开,进行详细叙述,按照古典戏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结构来组织情节。《爸爸去哪儿》每站故事基本按照“嘉宾到达现场—参观当地风光和特色欢迎仪式—游戏选房—游戏选食物—当地特色游戏—回忆总结”的时间顺序,故事时间显然聚焦于更具有看点的游戏时间,以保证节目流程的流畅性和观众的观看体验。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线性叙事带来的审美疲劳,节目会在叙事流程中插入倒叙和插叙,如《爸爸去哪儿》经常在游戏环节插入嘉宾事后采访和回忆,借助插入段落来设置悬念、引发观众思考。这种修饰性的叙事段落持续时间往往较短,能够从侧面补充主线叙事的故事,调节叙事节奏。
在非线性叙事占据主导的融媒体时代,乡村题材综艺节目的叙事时间开始朝复线叙事转向,追求一种近乎写实的风格,使用多机位、互动直播、沉浸式衍生节目等方式,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故事并置讲述,力求跨媒介全方位展示乡村的原始风貌,现实生活的情味蕴含其中。在《向往的生活》中,叙事常常通过田间的嘉宾劳作换取物资和蘑菇屋内做饭、生活的日常两条并行的时间线展开并相互影响,戏剧式高潮迭起的封闭结构被开放的生活流程所取代,飞行嘉宾到来、体验农村劳作和生活、离开并分享感悟的段落不断重复,在蘑菇屋经历乡村生活后又归于平静,只留下阵阵情感的涟漪。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结构不存在明确的结局和终点,同一时间节点上不同空间的叙事也延展了叙事时间的表意结构,一个更加真实、丰富、广阔的乡村形象在日常化的时间结构中慢慢显露。
(二)叙事空间:仪式与符号
以乡村为题材的综艺节目的空间塑造经历了从固定空间到“固定+流动”空间组合叙事的转变,从中国过去的落后农村文化转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蓬勃发展的新农村生活图景;从传统媒体的封闭式叙事空间转换为更加开放的、多义的空间。早期的乡村题材综艺为了突出乡村形象,选取具有典型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乡村地点作为固定的故事发生空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时代步伐,综艺节目中塑造的农村空间开始逐渐改变。
首先,故事空间的选取更为广泛,固定的故事空间如《向往的生活》中的蘑菇屋、《青春旅社》中嘉宾需要经营的客栈作为主要空间成为容纳人物仪式化乡村生活的场景,而流动的空间叙事则将更广阔的乡村故事空间纳入节目话语中。《山水间的家》通过农村当地的特产串联起大山深处的四川省绵阳市石椅村和江南水乡里的江苏省太仓市的东林村,将两个地理环境差异极大的村庄的乡土风貌、特色产业、农民收入对比展示,多条叙事脉络相互交错,最终收束于新农村、新生活、新风貌的主题之下。农耕文化和乡村风情在现代媒介的牵引下,重新回到当代的叙事空间中。
其次,以诗情画意般的影像符码和仪式化活动重构共同的乡村记忆空间,通过公众记忆里老家的旧房子、村里的小动物、生态优美的农田、热情的乡邻等共性的记忆符码连接第二记忆与第三记忆。农田劳作、畜养家禽、以物易物、赶集做饭、欢度地域性节日等节目中的固定环节会形成一种仪式化进程,集体记忆引发集体情感,集体情感询唤身份认同。在田园牧歌式的空间构筑中,中华民族农耕文化中自给自足、自强奋斗、共创幸福生活等深层集体心理得到呼应,消除绝对贫困、共筑乡村振兴等崭新的时代命题也得以写入其中。
(三)叙事视角:平视与散点
在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发展过程中,田园乡村逐渐由陌生化的他者形象演变为诗意栖居生活的主体,叙事视角的主体逐渐由旁观者移向乡村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实际参与者、传承者,从被动地观察他者、体验乡村生活转向主动地对归园田居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受到融媒体环境大众文化的影响,乡村题材节目聚焦从精英式俯视视角转向平民的平视视角,固定单一的叙事角度则由自中国传统诗画中习得的散点式多视角取代。通过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乡村题材的综艺节目勾勒了一幅民族传统美学所追求的“气韵生动”的自然田园风光[2],进而折射出新时代乡村的新鲜面貌,将宏大的“乡村振兴”政治议题落实为直观的人民崭新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
乡村题材综艺节目从现实生活内部去透视真实乡村日常,采取平民化的视角感受农村独有的恬静怡然的生活氛围,观察时代巨变影响下乡村的精神风貌和发展困境,感受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化所蕴含的对天人合一、超然物外、自然意境的追求,让观众产生身虽不行而梦绕山川式的沉浸式情感体验。《云上的小店》在讲述村庄里乡民故事时都会采用配乐、特效字幕和主观镜头的组合,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回忆和观点看法。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将善于传达情绪的“内聚焦”视角、观察视角的“外聚焦”、全知的“零聚焦”结合起来,形成了多重复杂的叙事视角,增强了观众的视听体验。叙事视角的多元组合使得乡村题材综艺节目绘制的田园乡村长卷成为一种中国画般开放的表意空间,丰富的视角组成了散点透视式的时代构图,随着观众的观看视角变化而展现出多彩的新农村生活即景,拥有乡村记忆的观众能够在节目富有情感的视线里找回记忆产生的共鸣。
三、融媒体语境下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叙事策略优化
(一)明星素人共建、深耕乡村人文,破除商业化对文化主题的消解
大众文化时代以影视声像为中心,在为受众提供娱乐消遣空间的同时,也将影视艺术纳入商品的范畴。乡村题材综艺节目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在追逐经济利益的目标指引下,乡村综艺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类型范式,大多数节目都围绕着“美食”元素,加入少量农耕劳作体验活动,主人公在体验与城市不同的生活仪式的同时回忆起曾经的人生经历,或被这种超然物质之外的质朴所感染,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模式化的创作流程保证了节目能够满足特定受众的期待视野,但也使得同一题材的综艺节目失去了新鲜活力。此外,明星效应助长了窥私行为,层出不穷的商业植入也会打断节目的叙事进程。尽管许多节目都响应“星素结合”(明星和素人搭配)的政策号召在节目中加入了素人嘉宾,但大多数镜头还是将注意力放在明星嘉宾身上,《亲爱的客栈》借助嘉宾阚清子、陈翔的婚恋问题引发观众热议,《你好生活》打出“央视boys”的组合提升节目话题度。在受众“狂欢”过程中,乡村综艺节目的文化主题被泛娱乐化的潮流淹没,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为了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乡村题材综艺节目需要挖掘更多适宜表现的农村生活和文化元素,包括乡村生态、方言文化、非遗技术等,坚持内容至上原则,呈现村民们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用好“星素结合”的人物描写策略,选取值得讲述的普通人生活故事,兼顾节目内容的故事性与纪实感,观照他们的乡村成长记忆,让农村人民成为乡村节目真正的主角。此外,合理利用明星优势,结合粉丝经济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文创周边、线下文旅等产业,使明星嘉宾成为节目的“助力”而非绝对的主导。这种由明星带来的热度是具有时效性的,因而短暂的关注之后,节目内容如何与农村当地结合形成更为长期可行的发展途径是真正需要深耕的课题。
(二)情怀情感交织、纪实抒情相融,应对泛化情感稀释深层叙事
在现代都市人普遍焦虑和快节奏生活的背景下,乡村综艺题材的节目通过塑造“异托邦”式的乡村怀旧空间引发情感共鸣,容纳现代人的精神寄托,相似情绪的快速扩散传播能增加节目受众并扩大传播效果。越来越多的乡村综艺节目重视“煽情”,注重构造形式化的煽情段落,在缺乏足够充实的节目内容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纯粹的情感抒发容易陷入无病呻吟般形式的窠臼。作为“情感共同体”,受众视线聚焦于表层化的情感认知,情绪的发泄代替了情节叙事,乡村综艺节目真正希望表现的农村生活纪实、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切实变化和问题,被即时的感情渲染和当下的心情体验所取代,短暂的情感体验过后,节目无法形成有效的长尾效应为乡村发展切实助力。而过度频繁地调动集体情感会使得观众对情感感受产生疲乏,反而削弱了情感传播的影响力。
因此,乡村题材的综艺节目在叙事结构中应当平衡好情感和情节,将情感的渲染落到具体实在的普通乡村人民和他们真实可感的乡村生活中,让情感在纪实的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同时,设置更加贴近乡村发展的公共议题,如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农业产业发展、乡村素质教育等,在实际问题的探讨过程里自然吸引受众加入节目构建的共情场域中。此外,加强仪式化的活动建设,不仅能够通过具体的共同行为引发情感互通,更可以借此支持乡村产业建设。《乡村合伙人》第二期节目创办的“白鳞洲漂浮市场”在节目结束后开始试营业,观众在观看过节目之后更可以到达活动现场进一步感受节目中所塑造的“桃源”式生活,线上线下联动,将节目的影响力变为实实在在的乡村发展的新动力。
(三)以乡村实践引领、从乡土生活出发,避免虚拟景观替代乡村原貌
乡村题材的综艺节目使用符码化的影像展现出的安静、恬淡、远离喧嚣的农村生活一度成为现代人摆脱现实社会压力的方式,缅怀过去的精神栖居场所,乡村形象逐渐远离了其现实本体而成为一种表象化的诗意象征。由陌生化叙事构建出的乡村空间显然成为这种解决都市人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之间冲突的奇观,融媒体强大的覆盖穿透力更是为其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途径。而这种奇观化叙事又被乡村节目中无处不在的明星代言、广告等符号消费带入一个悖论,在本该远离物欲的地方引导消费,在应当贴近现实生活的叙事中远离乡村现实。
居依·德波认为,“要真正地摧毁景观社会,就必须有将实践力量付诸行动的人们”[3]。综艺节目应当形塑自身的价值引领,加强行业自律,坚持正确的观念导向,以现实为依据,选取契合乡村现实生活和发展背景的叙事主题,拒绝刻意的美化或丑化叙事,讲述真实的乡村故事。在运营传播上应当充分利用融合媒体的优势,打造精品节目内容集群以形成品牌效应,拓展更为健康的节目收益方式。主流媒体和受众也应当积极发挥监督评述作用,形成良好的节目反馈正循环。
四、结语
乡村题材综艺节目利用多线并行的叙事时间、符号化和仪式化的怀旧空间及平民化全方位的叙事视角,以多元化的人物塑造引导开放的叙事结构,从而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多重主题有机统一,不仅能发挥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功能,更承担着传承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助力乡村文化和产业振兴,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因此,乡村综艺节目应与时俱进,结合5G、VR等前沿影视技术,拓展节目视野,寻找差异化乡村元素;充分利用融媒体跨媒介叙事的优势,建立全平台的乡村文化传播矩阵,以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助力农村文化产业建设;立足文化,观照现实,深挖农耕文明中优秀的精神基因和情感共鸣,将抽象的文化概念具体化为切实易感的影像,以影视艺术的独特活力和动力,讲好乡村故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基金项目: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短视频参与社会治理研究”(XW22106)]
参考文献:
[1]吕伟毅.媒介整合与集体智慧:探索“跨媒介叙事”的创作可能性[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12):76-83.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80.
[3]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28.
作者简介:陈世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昌 330031);汤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科研助理(南昌 330031)。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