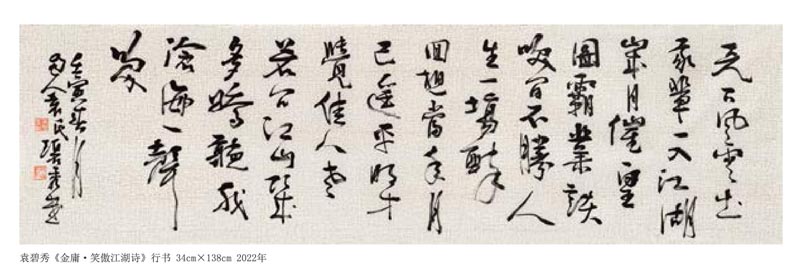罗佳连 周毅
里尔克曾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不要写爱情诗。”因为爱情诗太“流行”也太“普通”了,“那里聚有大量好的或是一部分精美的流传下来的作品,从中再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则需要一种巨大而熟练的力量”。无数珠玉在前,最日常的“爱情诗”写作反倒成了“最难的”。即便如此,爱情诗在时间之流中却从未停止生长,诗人们向内挖掘自己,小心翼翼捧献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渴望,四川女诗人银莲也是如此。
银莲的爱情诗有着温暖与希望的底色。她在《走进桂圆林》中写道:“想要走进你/却迷失了通往你的道路/一次次回头/原来你就在身后”。同样是“迷失在通往你的道路上”,诗人张枣的处理却是“不要击溃我,让汝中止在向着我的途中/丢失一句话,也可能丢失一个人”(张枣《维昂纳尔:追忆似水年华》),相比张枣“自我抗拒”式的、看似冷硬的情感,银莲诗中的“你”则常常是处在“回头”“就在身后”的位置,永远给人安全感,给人温暖和希望。所以当她在《你的行踪》中说:“我站在原地/等你说过的那句话/回过头来找我”时,作为读者的我们会心一笑,在情感上默认趋向“你”自然会“回过头来找我”,并且,“我”终究会发现“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原来你也在这里”(银莲《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的暖意,让人想到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我想和你一起生活》:“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同样是对幸福的渴求,不同的是,茨更偏向于“渴求”(“想”)本身,而银莲则常常处于抵达“幸福”的状态,这大概是她的爱情诗常带温暖希望底色的缘故吧。
“爱情”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词汇,如果功力不足,对它进行繁杂的修饰或堆砌反倒容易弄巧成拙,不如“清水出芙蓉”,还原它最干净本质且天真热烈的模样。曹顺庆评她的爱情诗“写得尤为动人。原始、激情,能够读到《诗经》的风味”,确是恰如其分。银莲的诗歌语言少假修饰,质朴动人,如《把自己快递给你》:“如果风来敲门/请开门签收/这来路不明的邮件/再一层一层解开/我的青涩与饱满/当你目光微醺/游走我的高山河谷/百合花开/我就是你梦中的新娘”,女性的温婉与激情巧妙地融为一体,下文更是大胆:“亲爱的,请绕道身后/用力抱紧我/穿过我黑色的长发/像星夜赶考的书生/翻阅《诗经》字里行间/枝叶初生的蒹葭”,如此原始的情欲横生场景,却表达得干净曼妙。异曲同工的质朴热烈在《我是雨夜怀揣火焰的桃花》《一叶小船在疯狂的血液里航行》《夜色淹没了整个世界》等诗中亦可见得。在银莲的爱情诗中,你几乎看不到“怀疑”“不安”“怠倦”等异质因素,而这样的因素在当代爱情诗的写作中却极为常见,女诗人翟永明和海男都写过同题组诗《女人》,个中无不充满“伤害”与“危险”,而银莲的《天下女人》,纯洁轻盈、和谐美好,一如她干净温暖的底色,所以曹顺庆还说:“银莲的诗还特别适合孩子读”,这样的诗,可以让儿童们“建构生活中基础的美的经验”。
当然最要紧的是,银莲的爱情诗,有着属于她自己的不落窠臼的“语言”和“表达”。试看她的《早恋的桃花开了》:“这些情窦初开的女子/乱花迷人眼/美得如此张扬/仿佛从来没有/在爱情里受过伤”。我们知道,以花喻女子或以女子喻花古已有之,如“梨花一枝春带雨”,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如“人面桃花相映红”,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短诗《百合花》中也自然地将“百合花”喻为“纯洁的少女”。因此,如果银莲只不过是将“桃花”比作“女子”,就极容易掉进滥调陈词里,但她却轻盈捕捉到了更具体细腻的点:“情窦初开的女子”“美得如此张扬/仿佛从来没有/在爱情里受过伤”,这“张扬”的譬喻跳脱寻常思维猛地宕开一笔——桃花美得有多“张扬”呢?张扬得“仿佛从来没有/在爱情里受过伤”——却显得格外恰切、举重若轻,再一细思,更是充满柔情。而诗人银莲本身天真浪漫的气质,也仿佛她诗中所写“没有/在爱情里受过伤”一般,张扬、热烈,追求着简单短暂然而最为真实的“此时此刻”:“佛祖呵,请收回/你赐给我的前世和来生/那些炫目的浮华/终究被风吹散/我只要今生今世/和幸福结缘”,“我只要你给我的现在/相守的每一分每一秒”(银莲《我只要你给我的现在》),这让人想到舒婷《神女峰》中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示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同样的对真实此刻的向往与渴求,风格则各自独立美丽。再如 “落叶起身/返回三月的枝头/把天空举过头顶”(银莲《我是雨夜怀揣火焰的桃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诗意反溯表达;“一棵树开一千朵花/也不觉得重复/一句话听你说一千遍/也不觉得多余”(银莲《一棵树开一千朵花也不觉得重复》)是独树一帜的烂漫类比;“冬天的空房子/搬进来一个春天”(银莲《冬天的空房子搬进来一个春天》)、“雪被之下/另一个春天拔地而起”(银莲《立冬》)则充溢着温暖轻盈的想象。
此外,银莲的爱情小诗也充满灵气。“小诗”是日本短歌、俳句及泰戈尔《飞鸟集》引入我国后产生的一种诗歌样式,篇幅短小文字简约,一般三五行为一首,常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予哲理或情思。试看银莲的《秋分》:“用一段细雨/剪裁秋天/在黑夜与白昼之间/何必在意/谁爱谁多一点/秋分之后/想你的夜长过从前。”一则简单质朴的爱情小诗,却注满了行云流水的柔情与思念,“细雨/剪裁秋天”是形意相契的清新想象,“何必在意”则是从容心境的呈现,“秋分之后/想你的夜长过从前”,抓住了“秋分”的节气特点,巧妙结合女性的思恋之情,于是表达就显得流畅绵长。这让人想到泰戈尔的“你在月亮上寄给我情书,夜晚告诉太阳/我用泪水答在草叶上”(泰戈尔《飞鸟集·124》),简单的语言与对话,饱含着同样深切的爱恋与思念。再看银莲的《落叶放下了整个秋天》:“选择走远/意味着我对你/不再迷恋/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正如落叶/放下了整个秋天。” “落叶/放下了整个秋天”具化了“我”对“你”爱情的“放下”,诗句充满动感与灵思,而“落叶”“放下”“秋天”的表达同样使人想起卞之琳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卞之琳《断章》),想起泰戈尔的“静寂盛了你的声音/鸟巢盛了睡着的鸟”(泰戈尔《飞鸟集·155》),都是将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巧妙表达。而爱情小诗之外,银莲其他小诗也同样干净澄澈,看得人心旷神怡,如《中秋月》:“天空/在挥金如土之后/懂得了节俭/用极少的版面/画了一个圆”。银莲同样用“极少的版面”,“节俭”地为我们画出了一个干净简约的“中秋节”。
银莲在她的诗集《在月亮上醒来》的后记中写道:“如果说亲人、朋友是生命里的太阳,爱情就是生命里的月亮。生活纵使有万般无奈,对爱情的向往丰满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这大抵算是我不同时期的写作,绕不过爱情诗的缘故吧。”而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中评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时说:“是有穷对无穷的眷念,而不是真实的感情纠葛,导致了爱情主题在阿赫马托娃诗歌中的频繁出现。”这话的内在逻辑实则与银莲异曲同工。在沟壑恒生的生活中,女诗人银莲始终怀揣着一颗浪漫质朴的澄澈诗心,书写她对爱、对爱情的理解与追寻。而对爱的言说,对爱情的言说,实则就是对所有情感的言说,对世界的言说,是面向万事万物的敞开,而这些,都一字一句写在了她的诗里,写在《爱在成都》和《在月亮上醒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