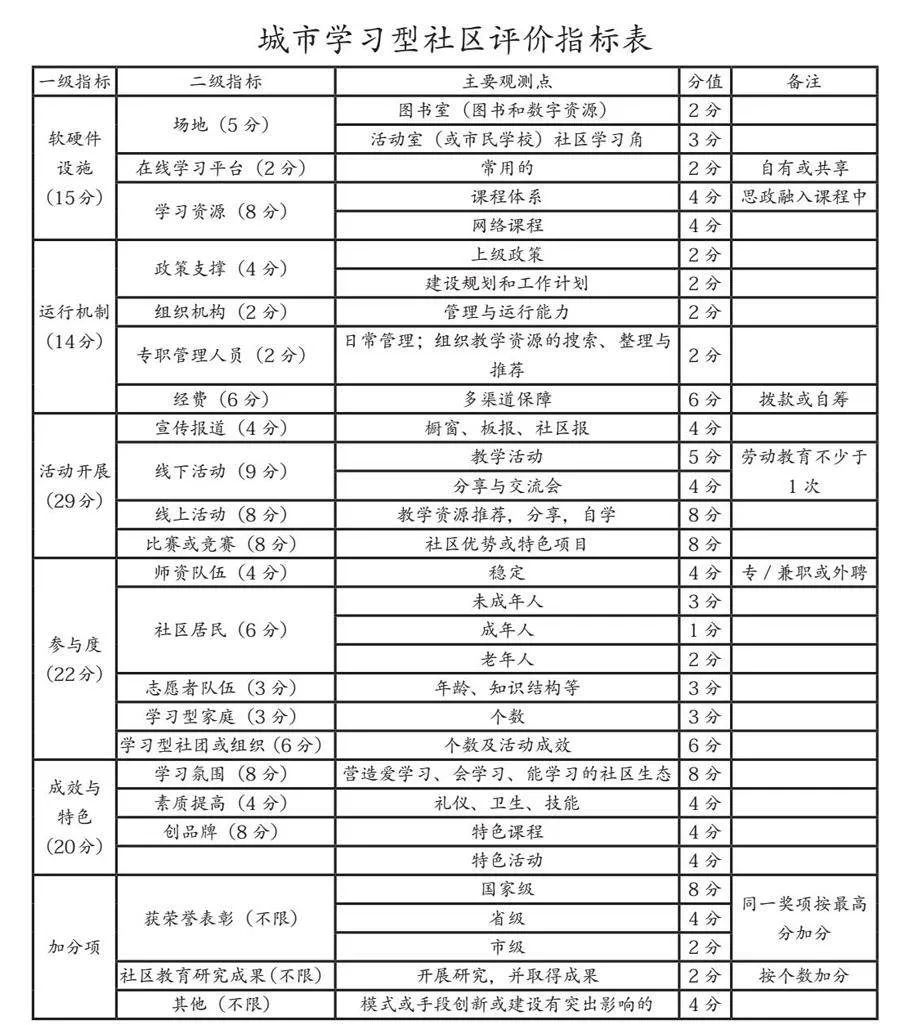路阳 郝一民
【摘要】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以商业住宅为居民单位的社区遍地开花,而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基层管理正逐步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街道办这种家长式管理模式向社区自治化方向发展。而且,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民主进程的推进,社区自治化势必会越来越普及和向纵深发展。这种自治化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求有相匹配的媒体平台和公共空间的建设,因而社区媒体在这一层面的意义极为重要。其在社区治理自治化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社区传媒所能发挥的信息、服务和公共领域建构的媒体作用;二是增强认同感、归属感和作为社区自治平台的社区管理作用。
【关键词】社区;社区传媒;社区自治
社区传媒最早出现于美国,已经有大约300年的历史。如今在北美地区,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两国,以社区报为代表的社区媒体发展已近于成熟,成为报业普遍亏损局面中的一枝独秀。在我国,社区传媒起步相对较晚,而且发展也出现曲折,不过社区传媒特别是社区报顺应了报纸“下沉”、受众细分的趋势,在利润与效果上也越来越受瞩目。如今,我国面临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治改革的大局,社区治理也成为基层政治改革的重中之重。社区传媒在社区自治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它是群众自治的发声筒,是社区公共领域的建构者,也是沟通意见的重要桥梁。
一、社区与社区传媒
社区最早出现于社会学,英文为Community,直译为社区、群落、团体、共同体等。“社区”一词最早为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所提出,其后帕克又将该词引入社会学,基本意思都是在强调社区是一个共同体。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腾飞,城市化的速度可谓迅猛,一时间各地城市涌现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社区。事实上,我国的社区与西方的社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社区”这一概念本身也在逐渐中国化。也正是由于中西方“社区”的不同,社区媒体在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价值才更加值得探讨。
社区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是其只针对特定区域的对象发行,不追求最大多数关注,在传播思路上与其他媒体迥然不同。按照社区媒体的类型来看,社区传媒包括社区报纸、网站、广播电视等媒体形态,不过一般而言社区传媒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发展最完备的仍然是社区报。社区传媒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1690年第一份社区报诞生于美国,其后的发展不温不火,而且多为周报,甚至扎根于乡村,与现在的社区报差别巨大。事实上,直到二战后,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的城市社区报才慢慢超过乡村社区报并占据主流,社区报也才逐渐有了现在所谓的社区报的色彩。
社区传媒虽然在国外起步早、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我国发展却并不顺畅。总体而言我国社区报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摸索阶段(2001年至2005年),其间大多数社区报都以失败告终。这一阶段的代表为号称我国第一份社区报的深圳《南山日报》和号称中国第一张全面市场化的社区报长春《巷报》。二是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其代表为《新民晚报社区版》及《北京日报》旗下的《北京社区报》等。[1]我国社区传媒就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大型房地产公司或是其他商业资本支撑,背靠大城市,围绕重要商圈周围的社区传媒,其存在的原因在于商业资本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开发,这部分媒体往往无正式刊号,属于内部刊物。另一种是都市传媒集团为促进媒体发展的战略部署或是市场挖掘,这部分以《新民晚报社区版》《北京社区报》等报纸为代表,有刊号,有背景。目前,国际上社区传媒盈利势头稳健,如在美国社区报盈利率大约是大报的8倍,加拿大也被称为“社区报王国”。不过在我国,由于社区建设的相对落后以及社区传媒与都市报的交叉导致社区传媒发展优势不明显,加上自身采编力量薄弱,社区传媒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社区治理的自治化
一般而言,社区治理指的是在社区范围内由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促进基层社区和谐稳定的治理方式。[2]这里强调的是社区力量的共同治理,但事实上社区治理正在向社区自治方向发展,而且社区自治也更符合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根据学者魏娜的研究,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脉络可以按照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为主导的行政治理模式,第二个阶段是由政府与社区力量联合的合作治理模式,第三个阶段是社区自治型的治理模式。[3]这三个阶段、三种模式在时间上相继,在发展程度上相迭。
社区治理向自治化转变是社会转型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会建设中的新课题。就其背景而言,首先是城市化水平加快,城市人口数量骤增,社区遍地开花,以往的基层管理模式已然不适应新的局面。其次,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语境下的基层民主改革深入的要求。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基层治理模式释放人才、资源等活力。具体而言,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位制,一种是街道办和居民委员会制。[2]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两种模式在发挥人员管控和资源分配方面作用巨大,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这两种模式对资源、人才的自由流动严重束缚,也因此社区管理正在逐步替代这两种模式。在这种背景下,社区自治就是要让社区替代以往的家长制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协商民主下的基层民主文明程度,从而满足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事实上,社区治理不光是一种管理,还是一种凝聚,特别是在社区治理的第三个阶段,即社区自治阶段,居民的齐抓共管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多层面的,无论是管理还是沟通,都需要一个平台建设,而这更加离不开社区传媒。总之,社区自治的发展是顺应“小政府,大社会”和“小政府,大服务”的社会结构转型,顺应协商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而这一过程势必离不开媒体的作用,社区媒体在社区治理中不仅有信息服务平台的媒介作用,更发挥着提出、讨论问题,监督促进落实的政治治理作用。
三、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与价值
社区管理中存在着五种力量,它们分别是政府、居委会、社团组织、社区精英(或曰意见领袖)和普通居民,说到底社区治理就是要实现五种力量的均衡并尽量降低一家独大(特别是政府力量)的局面。五种力量由于现实的原因,在信息的获取量上、管理的实际权力上和话语权上存在着较大差别,实际情况是政府、居委会等直接管理者在制定一些政策时并不能兼顾不同意见,甚至造成与居民关系紧张的状况。这种状况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公共平台建设不力所致。而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首先作为一种媒体,社区传媒最明显的就是其媒体功能,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领域架构等;其次从更广泛的政治治理角度看,它可以帮助建构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平台,并通过民众参与度的提高从而增强民众认同感、参与度并促进民主化程度,而且这对于平常居民话语权的尊重和对社区事务的监督管理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具体而言,其媒体价值体现在:
(一)信息和服务价值。社区传媒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其信息和服务价值,一般而言这种价值可以体现在社区传媒会及时地刊登天气、票务、演出、福利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服务类信息。正是由于社区传媒的针对性和及时性,它才会慢慢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阅读需求,进而产生一种很强的阅读黏性,促进读者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而且这种信息是深入百姓的,并且以社区居民为报道对象。例如报道社区内幼儿园、小学的文艺比赛,刊登某人出生的喜报等,其信息是非常可亲的。
具体而言,社区传媒的信息服务价值可以以一份老牌美国社区报《斯塔藤岛前进报》为例,辜晓进曾详细考察此报并将结果写成《走进美国大报》一书,书中介绍该报以本地社区新闻为主,每期常能占到四五个版面,而且其中又细分为要闻、评论、天气、副刊等板块,甚至专门为当地的少年儿童设立儿童版,专门报道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新闻。该报在扮演本地服务者的角色上不遗余力,例如评论版会专门开辟读者评论板块、副刊则有很多本地红白喜事内容。尤其深入居民生活的是其发布的大量招聘、交易信息,以及商家只针对本地居民的促销优惠政策,以至于很多居民手拿该报去往指定商场的指定货架购物消费。[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份成功的社区报纸,其信息的贴近性和服务意识的面面俱到对自身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意义所在。
(二)公共领域建构作用。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有关政治模式的重要理论,哈氏认为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描述,它强调一种公共舆论形成的机制,强调公民能够通过大众媒介自由平等独立地进行公开而理智的讨论,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提出解决。[5]他强调公共领域是通过大众传媒建构而成,同样的,具体到社区而言,社区传媒在社区公共领域的建构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就社区治理而言,社区传媒在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在促成一种公共领域的建设,这一领域独立于政府、居委会管理,为意见的公开表达和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特别是社区治理发展日益趋于自治的态势下,一个适当的社区机制或曰公共领域能为居民自治提供最基本的传声筒作用。另外,在社区自治语境下,居民在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时必须是不受干涉的,能反映出每个人民主诉求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社区传媒在这种治理中能够作为一种独立于居民和相关政府单位的第三方,能够最大限度地汇聚公共意见并促成民主商议,从而保证社区自治的真正民主、独立。
社区传媒的政治管理价值:
(一)构建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居民对所居住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在这种认识下,居民才能真正谈得上是自治,才能以较高的主动性来处理本小区内的事务。简而言之,就是让小区居民感觉自己小区的事情就像自己家的事情一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认识到社区治理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安居。民进中央副主席蔡达峰在社区调研时也强调,社区自治的灵魂便是居民社区共识的养成,社区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居民生活有赖于此、情感有赖于此,对此有归属感。[6]
社区传媒的一大特点或者说相比大报的优势就是专注本地新闻、本社区新闻。就美国社区报而言,这种深入社区的特性可以表现在社区报会刊登社区居民的婚丧嫁娶、比赛、通知等信息,而且在报道时常常采用小区居民的真实姓名,从而赋予其荣耀感,并增强其认同感与归属感。另外,在报道方式上,社区报惯常采用亲近性的、故事性的话语报道方式,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对社区内的大小事务进行报道,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可以说社区报在内容和方式上都深入人心,易于被小区居民接受和领悟,读者会慢慢形成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能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小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从而促进社区管理的良性发展。
(二)作为社区自治平台的价值。如上所述,社区存在着五种力量,社区治理就是要均衡这五种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社区治理缺乏一个开放的平台,在社区信息公示,社区决策制定、执行、监督等方面存在瑕疵。普通居民对社区治理热情度不高,往往处于被动局面,等到出现问题时又往往因为木已成舟而显得被动。而且,社区治理在朝向社区自治的方向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求社区能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去承载这一制度。这一平台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信息、意见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在于政策制定、执行的商议、监督。
在政治管理层面上,这一平台并不同于其媒介意义的公共领域价值,因为公共领域侧重于媒介自身所体现的意义,而其政治管理平台作用则体现其政治管理工具意义。作为一种自治平台,社区传媒可以是网络、报纸、广播等信息平台。与传统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互动性和参与性,极大地降低了社区居民间的沟通成本,并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必要的矛盾。社区传媒的亲近性决定了其读者可以就社区建设和社区生活中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而透明的交流,促进问题解决,从而使社区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广泛的、相互沟通的平台,一个公共管理监督的论坛。
四、结 语
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传媒,特别是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下,单位制弱化,社区也将逐步替代居委会的功能。社区自治的强化将极大地促进基层自治的科学民主化,从而促进基层政治建设。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既是传声筒,又是公共平台的建构者。社区治理在利用社区传媒实现良性发展方面应该继续推进。首先,在利用社区媒体的媒介作用上,应继续强化社区传媒的信息服务功能,促进信息的贴近性和实用性,树立服务意识。其次,在政治治理层面,社区传媒应该强化公共管理平台建设,努力打造一个有着充分话语权而且能够保证居民独立自主的民主管理平台。这一平台的建设需要开放透明的舆论环境,并且赋予每一个居民以自由平等的参与权和管理权。
总之,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传声筒和平台建构者的重要角色,目前在我国社区建设如火如荼,社区治理改革日益深入的情况下,社区传媒必然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都市类报纸日趋衰落的大背景下,社区传媒这种能在小处着眼、在小处大做文章的发展路径也对报业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序文,李先宏,孔文莹.我国社区报发展态势浅析[J].新闻前哨,2011(10).
[2]冯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社区治理为例[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1.
[3]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4]李瑞芬.社区报——都市报新的突围模式[J].新闻知识,2004(7).
[5]张学标,严利华.大众传播媒介、公共领域与政治认同[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1).
[6]蔡达峰.对社区自治要深化认识[EB/OL].上海统一战线网,www.shtzb.org.cn/shtzw/node264/node269/node271/u1a1762686.html
(路阳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郝一民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