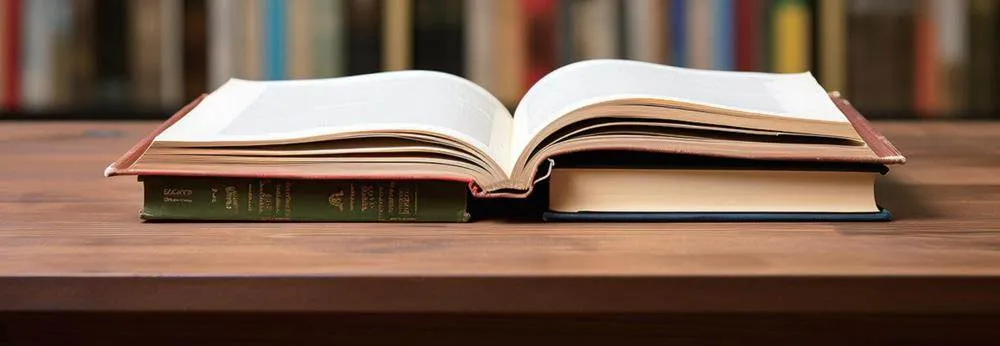摘 要:通过培育数据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保险业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保险收入、密度和深度研究数字经济与保险业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地区保险收入和提高保险密度。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保险业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通过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且处于中高门槛时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处于低门槛时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保险发展;门槛效应;保险密度;保险深度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2(b)--07
经过长足的发展,保险业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定器”角色,其通过风险转移功能,有效地抑制经济大幅波动[1]。我国保险收入规模2018—2022年连续五年居全球第二,2022年我国保费收入已攀升至4.7万亿元。但同年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为3.88%和3326元/人,与发达市场差距较大,保险理念尚未深刻融入我国经济体系,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仍待深入挖掘。同时,随着传统要素的推动力逐渐减弱,保险业发展亦如此,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推动保险业从“初级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在新旧动能转换后劲不足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凭借其包容性和普惠性的特征被认为是实现“双赢”的最优选择[2]。《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9.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并且,《“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占GDP比重为10%,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金融覆盖面得以提升[3],保险业无疑也享受着数字红利。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对保险业发展影响的文献,可分为三个角度。一是数字经济可提高保险供给侧的质量,多是从数字技术赋能保险业务环节角度阐述,多为定性研究。二是数字经济能够刺激保险需求的释放,多基于微观个体的商业保险配置角度进行研究。三是数字经济缓解供需不匹配问题。鲜有文献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保险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且往往将研究局限于一个整体时间段,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经济对保险业的差异化影响。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各省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再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自身不同发展阶段对保险业影响的差异,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期望能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更有效地利用其驱动力,为保险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促进保险业发展的直接效应
数字经济对于保险业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三点:
(1)供给侧。一方面,数字经济助力背景下,金融覆盖面得到了极大拓展[3],保险业无疑也享受着数字红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保险业对风险的识别和度量等能力,将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扩大可保范围[4]。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促进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极大改变了保险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模式,提高了保险业务的开展效率[5]。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5G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产品开发与定价[24]、业务的承保与核保、理赔[6]等各项经营环节,重塑保险公司商业模式、提高经营效率、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7]。
(2)需求侧。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微观个体的商业保险配置,进而推动保险业的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一系列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与普及,社交媒体、广播等多元化传播媒介日渐丰富,居民之间的线上社会互动增加,促使风险事件可以被快速、广泛地传播,大幅提高了消费者的风险意识[25]。魏金龙等(2019)[8]利用中国家庭的调查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提高社会互动水平,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从而促进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和程度。并且发现对于那些低收入、低教育以及农村地区的家庭群体,互联网促进效果更加明显[9]。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张芳洁和辛思潜(2024)[4]利用DID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以保险密度衡量的保险业发展。王莉和王国军(2023)[10]利用省级层面的数据发现,一地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促进当地人身险行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人身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聚焦于农业保险,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11]。
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保险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保险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会抑制个体的金融市场参与度[10]。基于数字技术搭建的互联网化平台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水准的服务。一方面,数字化使保险产品的精准推送得以实现,保险企业通过物联网、互联网等收集来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绘制精准的客户脸谱,洞察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基于情景”的精准服务[12],提高销售转化率。另一方面,随着保险业的承保自动化比率以及核保自动化得以逐步应用,降低了保险企业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险服务的普惠性,数字技术发展有效改善保险市场“长尾”客群覆盖不足的现状[1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对保险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2 数字经济推动保险业发展的门槛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正逐步加深、日益紧密,已成为推动传统行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然而,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并非一蹴而就。数字经济的非线性作用在各领域已有研究证明。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共享的关系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存在门槛效应,互联网普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14],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也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15]。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关系研究中,发现不同类型和强度的环境规制下,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门槛效应[16],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经济集聚对碳生产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非线性影响[17]。
具体到保险业,已有学者指出在推动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存在短暂的滞后效应[4]。一般而言,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座与核心,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外溢作用连接传统保险企业,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取所需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促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能够为保险业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保险供给体系[18]和增强消费者的保险意识[10],刺激保险需求的释放,使得保险市场呈现非线性提升。而当数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继续增加对数字技术的投资能够给保险业的持续性高发展带来的红利将略微有所减弱,由此引发保险业发展的动态演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数字经济对保险业的赋能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
2.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保险业发展指数(Ins)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于保险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方法主要包括保险收入法、保险深度法和保险密度法三种[19]。保险收入法作为被普遍采用的方法,以地区当年原保费收入作为衡量指标,直观反映了该地保险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记为InsP。然而,由于总体保费收入易受当地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本文在采用保险收入法的基础上,结合保险密度法和保险深度法。具体而言,保险密度法,采用人均保费指标衡量,记为Dens。而保险深度法则通过保费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体现了保险业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记为Dep。
2.1.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变量选取上,本文借鉴王莉和王国军(2019)[8]的研究,选取域名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软件业务收入、移动电话普及率、快递业务量、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6个变量,对其进行抽样适合性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08,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说明适合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累积贡献率超过85%的标准,本文选取前3个因子来刻画主成分,并通过线性转化使所有值均大于0。最终,得到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指数,记为Dige。
2.1.3 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与保险业发展息息相关,本文纳入以下3个反映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情况的变量:①城镇人口占比(X1);②人均GDP指标(X4);③受教育水平(X3),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风险保障意识越强,更能促进商业保险的购买[20];④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X9),地区的产业转型影响着保险行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本文参考张芳洁等(2024)[4]的研究纳入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2)家庭的内部特征,如人口规模和平均年龄等[21],会影响家庭商业保险的配置,进而影响行业的发展,因此,本文选取下列可能影响居民保险配置的人口结构变量:⑤少儿抚养比(X2);⑥65岁以上人口(X5),用65岁以上人口数进行衡量。(3)保险供给的便利性以及社会保险的发展水平与保险业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2]故本文加入:⑦保险中介机构数量(X8);⑧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X6),用地区年末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衡量;⑨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X7)。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2.2 实证模型
2.2.1 基准回归
本文参考王莉和王国军(2019)[8]的研究,构建平衡面板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模型如下:
Insit=β0+β1*Digeit+β2*Xit+μi+θt+εit(1)
其中,Insit表示i省份t年时的保险业发展水平,依次代表保险收入(InsPit)、保险密度(Densit)和保险深度(Depit),Digeit表示i省份t年时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程度;向量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ui为省级层面个体固定效应;θ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2.2.2 门槛效应模型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可能因为其自身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呈现出差异性,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采用Wang,Q(2015)[26]的方法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分别探究数字经济对保险收入、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从而设定如下模型:
Insit=α0+β1Digeit∙I(Thit≤θ1)+…+βnDigeit∙I(θn-1<Thit≤θn)+βn+1Digeit∙I(Thit>θn)+βcXit+μi+εit(2)
其中,Thit表示门槛变量,θ1…θn表示门槛值;Insit同上文;I(∙)表示性函数,当括号内为真时,取值为1,反之为0;β1…βn+1表示相应门槛区间的回归系数。
2.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级层面(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数据),2012—2022年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iFnD数据库、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式(1)的基础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进行回归前,先对主要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应拒绝原假设,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第(1)和(2)列反映了数字经济对于保险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仅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数字经济对保险收入的作用不显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和显著性均提高,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每增加一个单位,保险收入提高8.57%,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人均GDP和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促进保险收入的增加,表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险的普及对保险业有积极影响。假设1得以验证。
第(3)和(4)列反映了数字经济对保险密度的影响,添加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增强且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11.49%。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和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促进保险密度的提高,说明社会保险的普及对居民商业保险消费有拉动作用。
但对于保险深度,第(5)和(6)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会抑制其发展。纳入控制变量后,系数变为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保险深度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一地的资源是有限的,当数字经济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时,“虹吸”了对于保险业的投入,导致资金挤出效应与投资挤出效应,因此降低了保险收入在当地GDP的占比,抑制了保险深度的增加。实证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降低保险消费,该结果与杨斯童和李守伟(2023)[23]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原因是,保险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匹配,也可能是随着财富量的增加,居民倾向于将更多资源配置到风险资产上。
3.2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3.2.1 内生性检验
在基准模型中,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减少了部分遗漏变量的偏误,但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借鉴王莉(2023)[10]的做法,采用历史数字基础设施指标生成的交互项作为变量。具体为2006年各省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量与当年全国数字化水平(除本省外)生成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在重新回归之前,工具变量均通过了弱IV检验及不可识别检验,分别以F统计量为387.15和Anderson LM统计量P值为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和不可识别的原假设。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如表4列(1)、列(2)和列(3)所示,IV系数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3.2.2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可信性,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对样本数据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结果见表4列(4)、(5)和(6)。第二,鉴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和政策偏向性可能会使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被高估,因此将4个直辖市样本删除,重新回归,结果见表4列(7)、(8)和(9)。表4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 数字经济发展对保险行业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保险业发展之间具体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自身作为门槛变量,对式(2)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对门槛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得到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保险收入、密度和深度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双门槛检验,但均未通过三重门槛检验。因此,本文选择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数字经济在促进保险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展现出非线性特征,对保险收入和深度呈现出“倒U形”结构影响,对保险密度则呈现持续上升的拉动作用。
具体而言,当将保险收入和保险深度作为衡量保险发展水平的指标时,在数字经济未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即小于0.9061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0.2547和1.0349,说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时,其发展对于保险收入增加和保险深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已显现,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红利,但受限于自身较低的发展水平,这种促进作用尚未完全释放。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崛起离不开资本要素的投入。孟彦菊等(2023)[24]使用SDA模型,发现在2012—2017年期间,资本对于数字产业的贡献率高达42.16%。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资本要素的投入[26]。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以实现快速崛起,与同时期的保险业在资金、劳动力等方面可能形成了竞争关系,导致资金挤出效应与投资挤出效应,从而削弱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于保险业的促进作用。
在数字经济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中门槛区间时,其对保险收入和保险深度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估计系数分别增长至0.4258和1.8045,说明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为保险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助力保险企业自身发展,并且加强了数据、技术成果的交流与学习,实现了保险业的共建、共治、共享,增强数字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技术溢出效应、资源共享效应、专业化分工等正外部效应,为保险业的持续进步提供了外生动力。在跨过第二门槛值后,估计系数依然为正,但略有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在数字经济高水平发展下,其不断与传统行业融合,既推动了保险业的发展,又会促进其他行业的转型和升级,使得地区的产业间结构优化、升级[25],导致产业间竞争加剧,从而削弱了数字经济对保险业的单一促进作用。当以保险密度衡量时,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逐渐递增。具体而言,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中、高门槛区间时,估计系数分别为0.4837、0.5617和0.6664,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综上可知,无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处于何区间,均显著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体现在保险收入增长、保险密度优化以及保险深度提升三个方面。并且,当处于中高门槛区间时,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2012—2022年30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于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通过基准模型的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地区保险收入的增加和保险密度的提高,但对保险深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以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其对保险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通过门槛模型的回归发现,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高门槛时,其对保险收入、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促进作用均大于其处于低门槛时。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鉴于数字经济对保险业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保险业应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浪潮,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赋能,激发保险业发展的新动能,从而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2)关注数字经济推动作用的非线性特征,鼓励保险企业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发展策略。具体而言,在数字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企业应充分利用其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优势,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保险业务的融合创新,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而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则应把握发展的转折点,深入挖掘并发挥后发优势,通过精准施策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保险业发展差距,促进全国保险市场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初立苹, 粟芳. 经济“助推器”还是“稳定器”: 保险功能的理论与实证[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5(7): 49-63.
张蕊, 余进韬.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7): 1-9.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 54(8): 71-86.
张芳洁, 辛思潜. 数字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 保险研究, 2024(1): 21-35.
战明华, 孙晓珂, 张琰. 数字金融背景下保险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 保险研究, 2023(4): 3-14.
张瑞纲, 吴叶莹. 数字经济背景下现代保险业发展研究[J]. 西南金融, 2022(7): 91-102.
王媛媛. 保险科技如何重塑保险业发展[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9, 34(6): 29-41.
魏金龙, 郑苏沂, 于寄语. 家庭异质性、互联网使用与商业保险参保: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J]. 南方金融, 2019(9): 51-62.
杨碧云, 吴熙, 易行健.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 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J]. 保险研究, 2019(12): 30-47.
王莉, 王国军. 数字经济与人身保险行业发展: 基于消费者培育视角[J]. 保险研究, 2023(3): 11-24.
义旭东, 吕琪琳. 数字经济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影响[J]. 现代农业研究, 2024, 30(4): 8-15.
苗力. 保险企业数字化战略转型路径研究[J]. 保险研究, 2019(4): 57-65.
刘冬姣, 庄朋涛.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J]. 消费经济, 2021, 37(2): 67-78.
程名望, 张家平. 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7): 22-41.
胡长玉, 赵启程. 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 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7): 10-15.
李柏桐, 李健, 唐燕, 等. 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异质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J/OL]. 中国环境科学, 2024,44(9): 5263-5274.
叶娟惠. 门槛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集聚对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J]. 福建商学院学报, 2024(1): 18-26.
陈卿, 向立力. 数字经济丰富多元化保险供给[J]. 中国金融, 2023(11): 38-39.
陈华, 周倩. 保险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综述[J]. 保险研究, 2018(5): 113-127.
蒲成毅, 潘小军. 保险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金融机理研究[J]. 经济研究, 2012, 47(S1): 139-147.
徐敬惠, 李鹏. 商业保险在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的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J]. 保险研究, 2020(8): 15-29.
赵桂芹, 陈莹, 孔祥钊. 医疗保险、农业信贷与精准扶贫[J].经济学, 2023, 23(2): 712-730.
杨斯童, 李守伟. 气候风险对我国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J]. 金融评论, 2023, 15(02): 91-117+126.
孟彦菊,陈思年,陈蕾.基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数字产业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23):89-94.
刘家旗,薛飞,付雅梅.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 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J].统计与决策,2023,39(18):125-128.
刘继光,吴陈锐.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源泉及动力转换: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的分析[J].保险研究,2019,(05):3-30.
Ansari,Nixdorf S,Sihn W.Insurability of Cyber 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s:How Does Digital Twin Improve Predictability of Failure Risk?[J].IFAC-Papers On Line,2020,53(3): 295-300.
Gao L F,Guan J,Wang G J.Does Media-based Health Risk Communication Affect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Demand?Evidence from China[J].Applied economics,2021,54: 2122-2134.
Wang,Q.Fixed-Effect Panel Threshold Model using Stata[J].The Stata Journal,2015,15(1): 12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