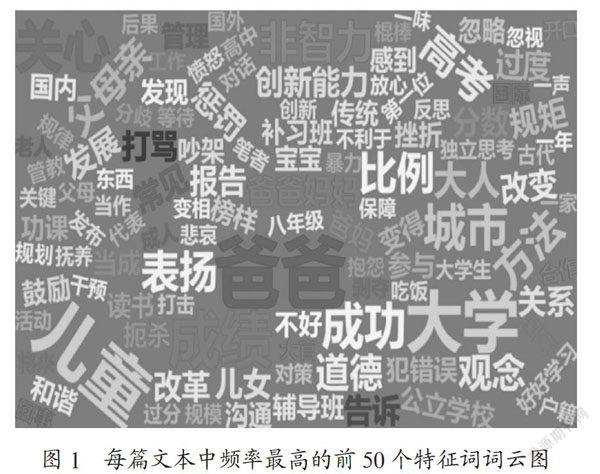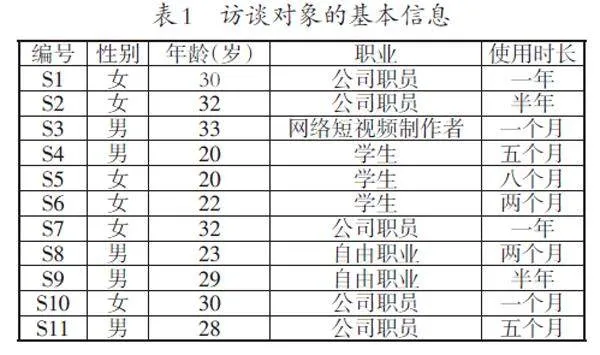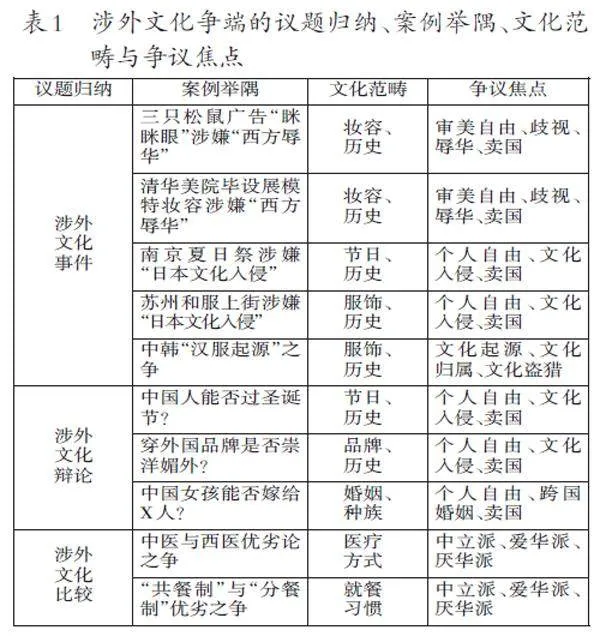【摘要】“勿忘人民”是穆青新闻思想的高度结晶和集中体现,也是他新闻实践的经验准则。已有研究通常将“勿忘人民”从职业操作的方法论来阐释。穆青的记者生涯与新闻报道中蕴含了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但在客观性主导的新闻业中,情感被拦在门外,“勿忘人民”新闻思想还未充分从情感的认识论角度去解释。在情感已然成为当前新闻世界的重要因素,基于“勿忘人民”新闻思想的“人民性”内涵和新闻实践中的“人民”情感,当前对“勿忘人民”新闻思想的阐释需回归到情感的认识论角度,作为情感的“人民性”是解读“勿忘人民”新闻思想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情感;人民性;穆青;勿忘人民
在中国特色新闻学和新闻事业中,“人民性”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思想是“人民性”具象化的体现。穆青对人民的情感贯穿了他的新闻实践,这也成为理解“勿忘人民”新闻思想的重要维度。当前,如何认识情感与新闻的关系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也是新闻实践的徘徊之地。本文从作为情感的“人民性”出发,旨在从情感的认识论角度更深阐释“勿忘人民”新闻思想,进而从穆青新闻思想中找到理解情感与新闻之间关系的钥匙。
一、党的新闻事业中“人民性”的情感内涵
“人民性”是我国新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话语及方法论在我国新闻实践中经历了多重深化发展,其中蕴含了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它是指新闻事业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运用新闻手段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一种特性。[1]
在党的新闻事业历史上,“人民性”最早使用于1947年。《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时刊发的《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写道:“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2]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突出了依靠人民办报、办报为了人民的重要原则,“人民性”也进一步发展成为党在新闻工作中的方法论。
随着党的新闻工作不断发展,“人民性”作为新闻实践的方法论不断具体化。从“三贴近”到“走转改”,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人民性”已是新闻工作的重要理念与实践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3]“人民性”的传统是贯穿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的,其情感意蕴集合了对人民的厚爱之情、对人民的敬重之情、对人民的仁爱之情。[4]
本文认为,“人民性”作为新闻事业中的重要理念和实践原则,在更深层次是作为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而存在的。穆青“勿忘人民”新闻思想最重要的是融入其报道理念与方法的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诚然,方法论层面是对“勿忘人民”新闻思想的阐释路径之一,但还需从情感的认识论角度准确理解“勿忘人民”的底层情感逻辑,才能在方法论上有更深刻的实践遵循。
二、穆青报道中“勿忘人民”的情感实践
穆青写有多篇感人至深的报道,“勿忘人民”不仅是他厚植于心的情感观念,还是融入报道的情感实践,这成为他与人民群众建立深情厚谊的重要方式。“勿忘人民”的情感实践在于他如何对待和处理作为情感的报道客体、作为情感的报道主体以及作为情感的报道方法。
(一)作为情感的报道客体
我国新闻报道具备情感基因,但将客观性视为情感对立面的认知导致情感被遮蔽。《新华日报》曾指出:“既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就应该以全体人民为对象,反映全体人民的情况和情绪。”[5]明确将人民的情感作为报道客体。
穆青特别善于挖掘采访对象的情感,将大量的情感作为报道客体,但在作品中却读不出与客观性脱轨的意味。穆青将真实发生的情感如实反映在报道中,并以情感线索再现人物思想与行为。如呈现焦裕禄对兰考的深厚情感:“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穆青非常重视人民的呼声、愿望以及人民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和情感。但在客观性之下就存在一个问题:作为情感的报道客体如何保证真实?从他的报道中可见,他对于报道中呈现的情感是否真实多有佐证,最重要的是他对报道中任何情感的发生都是自己亲眼所见,而非主观推测臆想。穆青在将情感作为报道客体时保证了其发生的真实性,这也正是作品不仅没有偏离客观性,反而让读者对客观事实的认知更加清晰的原因。
(二)作为情感的报道主体
客观性重在报道主体能不偏不倚地反映事实,但在实现过程中,将情感与新闻置于对立关系之下,客观性操作成为报道主体在报道过程中不能掺杂情感,以避免报道主体的个体判断影响事实的客观反映。但在穆青的报道中运用了大量的情感,这就涉及穆青如何处理报道主体的情感与客观性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党的新闻事业,历来强调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6]报道主体的情感需要与人民群众的情感有高度共鸣,“齐爱憎”就需要在情感的发生过程中做到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和“共患难”,报道主体在亲身参与事实发生的过程中去验证情感是否真实,才能使情感不影响事实的客观反映。
穆青在写焦裕禄的过程中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感情,流泪最多:“什么叫激情,我的体会是到忘我的程度,你的思想感情都会在人物身上,你即使做一件事,洗脸、吃饭都是下意识的。”[7]在穆青写焦裕禄时,他对报道对象的情感如果是基于自身想象或臆测,未得到亲身验证,必然会影响到报道主体的判断进而损害到客观性。但他深入群众生活调查研究,与报道对象同吃同住,所描写的情感发生皆为其亲眼所见、亲身参与,在这种报道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才能实现真实与客观。
(三)作为情感的报道方法
穆青曾七访兰考、八下扶沟、四到宁陵、十进辉县、两上红旗渠,之所以能将笔下的人物“写一个,活一个,响一个”,一个重要经验是将情感作为报道方法。他对人物的情感之所以能反映得真实,重要的是报道对象能在他面前有真实情感,采访到了人民群众最真实、最直接的感受,这源于穆青能深入人民生产生活场景,在实践中体会人民内心的思想感情。
穆青第一次到红旗渠采访时,与采访对象任羊成成为朋友。任羊成在他面前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话都愿说。[8]在报道赵占魁时,穆青和赵占魁同吃同住,从最真实的日常中去观察记录,才有了穆青对赵占魁革命劳动情感的真实呈现。“勿忘人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能忽略人民的情感,正如他曾写的:“必须懂得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自觉地建立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思想感情。”[9]这也正是穆青为什么要将情感作为报道方法的重要原因。要懂得人民群众的情感,就需要用记者的情感与脚步体会感受人民群众的情感,知道人民群众的情感因何而生、从何而来,而非凭主观臆断,进而才能在将情感作为报道客体时保证其真实性与客观性,这也是穆青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和一线采访的缘故。
三、“勿忘人民”对认识新闻与情感关系的启示
客观性被认为赋予了新闻以专业性与职业性,成为新闻业的核心话语。在这一原则主导下,情感在传统新闻实践中意味着主观,被认为是对客观性的最大威胁,因此被拦在了新闻业门外。但在情感成为传播中的显性因素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新闻与情感的关系。在“勿忘人民”的新闻思想中,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是“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但穆青的报道不仅与客观性毫无相悖,还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勿忘人民”的情感实践说明,情感与新闻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冲突关系,关键是认识到情感发生的客观性,处理好情感与新闻真实、情感与新闻客观的问题。
(一)情感发生的客观性
在传统认知中,情感被认为是一种纯粹源于我们内心的存在。但在情感的进化论观点和社会建构论中,情感的发生是一种具备客观性的过程。情绪是人固有的生理模式,是进化而来的适应性反应。情感能通过主观整饰而被隐藏起来,但无法左右带来的身体变化,如心跳加速、肌肉紧张等。
有研究指出,新闻世界构建的是基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世界。[10]情感是对现实的认知方式,在新闻中将情感拒之门外,反而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完整呈现。因此,情感与新闻并非对立。在穆青的报道中就已将人民的情感作为报道客体来呈现,并实现了情感与新闻的平衡。
(二)情感与新闻真实性
“勿忘人民”新闻思想,尽管将大量情感作为报道客体,但对新闻真实性的遵循却从未疏忽。相较其他信息,情感因其可整饰性更易产生真实问题。对报道者而言,这种整饰不易鉴别其真实性,也是新闻专业操作忽略情感的原因之一。
情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而新闻反映社会生活,如因情感易产生真实问题就将其拒之门外,对社会的反映则有失真实。新闻不能忽略情感,而更重要的是,报道者将情感作为报道客体时如何实现情感真实。从穆青的情感实践中可知,如忽略采访对象真实发生的情感,对整个事件的反映就不能达到完全真实。穆青在报道人民情感时,全部基于人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用自身实践佐证情感真实,这也正是认识情感与新闻真实性的关键路径,也就是说,以报道者亲身实践体验人民的情感,可以兼顾情感与新闻真实,而不能因情感的可整饰性就放弃真实世界中的情感因素。
(二)情感与新闻客观性
在传统的客观性观念中,抵达客观性的唯一路径是报道者要避免情感,这种观念将情感与客观性对立。但情感的发生是具备客观性的,人可以左右情感的表达程度或方式,却无法拒绝其发生。情感作为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显然不能被忽略,也应是新闻报道的客体。情感被学界重视后,新闻业开始在传播中融入情感,“暖新闻”等形式的报道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尽管情感已经融入当前的新闻实践,但报道者如何不偏不倚地呈现情感?
客观性本身是被建构出来(非本质可抵达)的。[11]这意味着客观性并非是先在性的存在,其抵达路径亦非唯一,重要的是如何达到一种符合客观性的效果:相关信息和获得信息的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都能得到明确说明。[12]换言之,情感被作为报道客体时,报道者呈现的情感性信息与获得情感性信息的方式二者之间需要有合理性。要不偏不倚地报道人们的情感从而实现客观性,就需对所报道情感不夸大不缩小,不增不减,不能根据报道者喜好改变情感的原有属性。要实现这一过程,报道者刻意排斥情感,运用非情感方式报道情感,显然很难准确了解情感,毋宁说实现对所报道情感的不偏不倚。穆青既能心怀对人民真挚深厚的情感,并将其运用在报道中且又未脱离客观性,就在于他将自己置于人民情感产生的实地之中去感受人民情感因何而生、从何而来、是何程度,与人民时刻保持情感联系与共鸣,才能对人民的情感有客观呈现。因此,就如何实现情感与客观性统一而言,重要的不是报道者完全去掉情感,而是报道者如何运用情感去了解要报道对象的情感,不使报道者因不懂人们的情感而影响对所报道情感的判断和把握,出现对情感的偏倚呈现。
四、结语
“勿忘人民”新闻思想源于穆青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场景中的情感实践。理解“勿忘人民”新闻思想,就需对其记者生涯和报道实践中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入手。他心怀人民的赤诚情感跃然纸上,是“人民性”的充分实践与体现。研究认为,作为情感的“人民性”是解读“勿忘人民”思想的重要维度。诚然,已有对“勿忘人民”新闻思想的方法论阐释同样重要,但在当前情感成为新闻业越发重要的因素之下,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思想需要回归到情感的认识论角度阐释,以回答当前如何实现情感与真实性、客观性之间关系统一的问题,发挥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为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情感如何嵌入新闻:数字时代的新闻客观性研究”(2025-ZDJH-73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尹韵公,丰纯高.关于新闻理论中的“人民性”问题[J].红旗文稿,2006(18):12-14.
[2]李冉,邹汉阳.党性、人民性的话语起源与行动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05):38-44.
[3]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N].人民日报,2013-08-27(1).
[4]任彩红.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情感意蕴[N].深圳特区报,2024-03-26(A12).
[5]检讨与勉励:读者意见总结[N].新华日报,1947-01-11.
[6]郑保卫.重温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写在建党85周年之际[J].新闻记者,2006(07):3-7.
[7]穆青:勿忘人民,一枝一叶总关情[EB/OL].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09/13/c_1211367901.htm.
[8]刘冬杰.像火把一样照亮群众的心灵:穆青文风的源泉和活力[N].北京日报,2021-10-15(14).
[9]周华.探寻“穆青精神”的恒久价值:纪念穆青诞辰90周年暨新闻名篇名记者学术研讨会侧记[N].光明日报,2011-03-13(15).
[10]王润泽,米湘月.新闻世界:新闻学元概念和问题的新探索[J].新闻大学,2024(1):33-47+120.
[11]杨奇光.技术可供性“改造”客观性:数字新闻学的话语重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1(5):118-127.
[12]Tuchman,G.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New York:Free Press,1978:82-83.
作者简介:王怀东,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郑州 450001);曹芳,河南法治报社记者(郑州 450004)。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