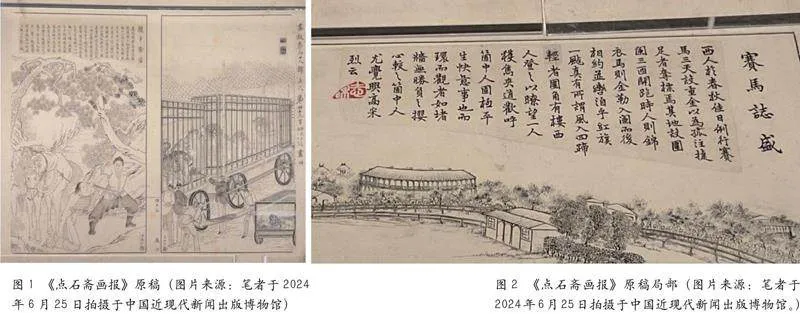苏轼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笔触老练,形神兼备,随意而成,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在书法创作上,苏轼的书法审美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书法创作要自出新意,别具一格;第二,书法创作要提高学养,内外兼修;第三,书法创作要追求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第四,书法创作要遵循法度,既要效仿古人,又要加强对技法的积累。只有这样,书法创作才能达到新的境界。
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音乐家,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苏轼涉猎广泛,精于钻研,位居“宋四家”之首。他的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格局;他的诗是宋诗的代表;他的书法崇尚自然、刚健婀娜。苏轼不仅留下了很多著名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论述也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及后世书法家的创作,加快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进程。
提倡自出新意
苏轼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人,他在诗、词、文、书法等方面都提倡创新,提倡自出新意,独出心裁。书法的汉字结构都是固定的,想要在书法上突破前人的框架极为不易。为了让自己的书法能够出新,苏轼提倡书法要通其意、出新意。
所谓通其意,就是指书法创作要体现创作者的情感意趣。这一观点是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中提出的,该诗集中体现了苏轼对书法的见解。这首诗一开始,苏轼就提出了“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不善书”是苏轼自谦的一种说法,他的主要目的是提出“通其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书法要跟随心意而动,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书法作品要能够看出创作者的心境,要体现情意。例如,在《黄州寒食诗帖》中,苏轼笔随意动,一气呵成,通篇气势磅礴,在一点一竖之间尽显诗句中的情意。《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至黄州时所作,整首诗诗境悲凉凄苦,将诗人的苦闷惆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开篇直抒胸臆,说自己来黄州已有三年,转眼又是春去秋来,雨打花枝,泥污燕羽,这幅画面让人无可奈何又苦闷万分。从平淡的叙述到惜春叹春,苏轼的情感变化十分明显,所以在书写这几句诗时,苏轼一开始落笔随意,尤其是“自我来黄州”几个字,大小相同,笔墨均匀,可以看出苏轼开始落笔时心情还算平静;三年时光转瞬即逝,转眼又到寒食节,想到此处惆怅便随之而来,“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几字的字体大小随着苏轼心情的改变出现了变化,尤其是第二个“惜”字突然变大,笔墨突然变重,和前面几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重笔写就的“惜”字所包含的厚重感情也扑面而来。与《次韵子由论书》相比,《黄州寒食诗帖》的诗境更为凄苦,因此整幅作品更加潇洒肆意,笔墨也更重,结字更为出奇,往往在不应断开的地方戛然而止,字体大小变化多端,疏密错落有致,很好地表现了整首诗的诗境。这幅书法作品是苏轼书法的代表作,也是苏轼对“通其意”最好的阐释。在这一创作理论的指导下,苏轼的书法作品极富生命力,艺术表现力极强,能够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因此引得后世创作者争相效仿。
所谓出新意,重点在“新”字,指的是书法创作不能拘泥于已有的框架,要敢于出新,敢于挣破枷锁。我国书法的历史和汉字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在汉字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自觉追求汉字书写的艺术效果。宋代以前,就已经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大家,如李斯、王羲之、王献之、王珣、欧阳询、褚遂良、张旭、怀素等。这些书法家技法高超,他们的书法作品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对后人来说既是重要的范本,也是难以逾越的高山。苏轼认为,要想突破这些“高山”带来的限制,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出新”,也就是要敢于尝试去走前人未走的路,不必完全遵守书法的法度。苏轼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认为他的作品全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挥就,所以不会“践古人”,这种潇洒肆意的创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文人的书法创作,推动了宋代书法“尚意”氛围的形成。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也是其“出新意”书论的体现。在这幅作品中,苏轼没有借鉴前代大家的创作风格和技巧,完全随心而动,用笔轻重、字体大小、行间疏密都依照自己的心意安排。黄庭坚给予了这幅作品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幅作品“犹恐太白有未到处”。
提倡提高学养
纵观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学养都是常人所不及的。艺术创作建立在艺术鉴赏和艺术领悟的基础上,而艺术鉴赏和艺术领悟需要创作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大众喜爱的作品。苏轼认为书法创作也应如此。因此,要想在书法创作上有所建树,创作者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第一,创作者应提高学术修养。苏轼认为书法创作的首要条件是多读诗书,提高个人素养。在柳氏的两个外甥讨求苏轼的笔迹时,苏轼回了他们一首诗。苏轼写道:“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苏轼认为,只有多读书,才能了解书中的真意,才会下笔如有神,到那时,也就不用去临摹别人的笔迹了。苏轼是个爱读书的人,他屡次劝说别人要多看书,他认为书法创作不仅要有纯熟的技法,还要有渊博的学识。他提倡“技道两进”,技法上要不断精进,学问上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书法创作才能随心而动,如果只关注技法,不关注学问上的进益,那么书法只会沦为献技之作,无法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书法作品也会失去生命力。苏轼提倡书法创作要提高学养这一观念和他提倡书法创作要自出新意是一脉相承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体现创作者的“意”。在《西楼苏帖》中,苏轼模仿了王羲之,但他不追求字体的相似,而是力求自己的书风能有王羲之的风韵。他认为王羲之不管是在学问上还是在思想修养上都达到了超然物外的境界,要想达到这一境界,首要之事就是提高自己的学术修养,通过读书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此达到下笔如有神的效果。
其次,创作者应提高品德修养。苏轼认为可以从书法作品中看出创作者的品德修养,提高品德修养可以丰富书法作品的“神”,让书法作品形神兼备。苏轼在《论书》中写道:“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苏轼认为,有长得漂亮的人,也有长得丑陋的人;有擅长言语的人,也有沉默寡言的人;有擅长书法的人,也有不擅长书法的人,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君子和小人是十分容易分辨的。因此,他认为书法创作的效果和创作者人品的好坏息息相关。这与“文如其人”的观点相似,很多人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一些品德高尚的君子可能并不精于书法,但这一观点也有合理之处,就像苏轼推崇王羲之超然物外的境界一样,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就是王羲之品德的体现,也正是因为重视品德修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才能成为“天下第一行书”。即便是外行,在看到《兰亭集序》这幅书法作品时,也能感受到其恬淡从容、飘逸潇洒的神韵,王羲之淡然的气质和极高的修养使整幅作品更具艺术表现力,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美学价值。苏轼一生命途坎坷,但他生性乐观旷达,又尤爱老庄之道,因此在处世上十分淡然豁达,他的书法作品自然也独具风格,自成一家。
提倡书本自然
“自然”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不论是诗人、词人,还是书法家、画家,都将“自然”当作自己创作的美学追求。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是因为他的诗仿若信手拈来,韵律和谐,朗朗上口。苏轼提出书法也需要“自然”,认为书法要充满自然感性之美,不能只堆砌技法,而是要随心而动,依意而行。
要想达到书法的“自然”,首先要获得心灵上的自由。老子提出“无为而无不为”,希望达到“人的自然化”。苏轼将其应用于书法创作中,如在《黄州寒食诗帖》中,苏轼落笔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字体的大小、笔墨的轻重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写到淡然处,笔墨就轻些;写到愤懑处,笔墨就重些。虽然整幅作品气势磅礴,跌宕起伏,情感上多见消极,但苏轼心灵上的自由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要达到“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是李泽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讨论后提出的观念。书法作品要想达到“自然的人化”,创作者就必须在书法创作中注入精神力量,让书法创作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延。苏轼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他将书法比作人体结构,“骨”“肉”“血”指物理层面,“神”“气”指精神层面,只有二者兼备,书法创作才能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要想使书法作品具备“神”和“气”,创作者就必须亲近自然万物,了解生命的价值和本质,并将其融入创作中。这一点在苏轼的晚期作品中可以看出。例如,在创作《洞庭春色赋》时,苏轼对人生的理解已经十分深入,因此该作品结构紧密,用笔老练,集中反映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提倡遵循法度
苏轼爱好广泛,在书法上提倡效仿前人,遵循书法的法度。遵循法度看似和自出新意相对立,但实际上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自出新意的前提是遵循法度,遵循法度的结果是自出新意。书法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创作,一笔一画都有技法上的要求,就像达·芬奇学画画先从画鸡蛋开始一样,进行书法创作的前提是写好点横竖撇捺,因此,只有技法足够纯熟,书法创作才能拥有无限可能。
遵循法度,一方面是效仿前人。书法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因此,模仿书法大家的技法是书法入门最快的方法。苏轼学习过颜真卿、王羲之、杨凝式等人的书法,并创造性地将这些人的书法风格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中,最终探索出了独具风格的书法道路。苏轼认为,要想走好书法这条路,就必须临摹书法大家的作品。从苏轼的早期作品《治平帖》中可以看到“二王”的影子,因为苏轼早期最崇拜的书法家就是王羲之,整幅作品字态稍显妩媚,结字较为纤细,这也是“二王”作品的特点之一。
另一方面是精练技法。精练技法是很多书法家一生的追求,只有技法足够纯熟,书法作品才能拥有更高的美学价值,书法创作才能达到新的境界。苏轼的书法风格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苏轼的早期作品字态妩媚,布局规整;等到中期时,苏轼又学习了其他书法大家的技巧,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书法创作中,所以这一时期他的书法作品气势磅礴,跌宕起伏,富有变化;到晚期时,苏轼的书法技巧已经十分纯熟,也形成了个人的书法风格,所以其书法作品笔意雄劲,结构紧密,笔墨老练。乾隆皇帝对苏轼晚期的书法作品《洞庭春色赋》的评价为“首尾丽富”,认为这是苏轼最出色的书法作品之一。
苏轼的书法审美观是在其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正确理论。苏轼的书法理论与作品不仅引领了宋代“尚意”的书风,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