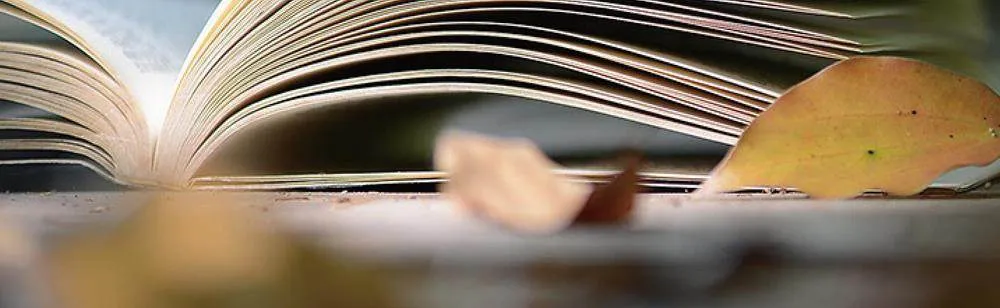
在建设“书香中国”的时代感召下,我国涌现出许多优质的读书类文化节目。其中,《我在岛屿读书》凭借诗意的场景营造、合适的嘉宾选择、多样的内容呈现和合理的环节设置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在传播文学知识、助力全民阅读和给予精神支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价值引导作用,为今后读书类文化节目的创作提供了创新范式和纾困策略。
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是今日头条与江苏卫视联合出品的外景纪实类节目,其紧密围绕余华、苏童、西川等文坛好友在岛屿读书、谈书、论书、评书的生活展开。该档节目自开播以来便好评不断,不仅两季节目均在豆瓣App中获得9.0的高分好评,而且还收获了国家广电总局的点名表扬。的确,《我在岛屿读书》开拓出了读书类节目的创新路径,为国内同类型电视节目在创新、价值引导和纾困策略上起到了镜鉴作用。
突围:将“读书”与“生活”自洽得当
场景营造:打造岛屿与书屋,再现阅读场域
法国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艺术三要素”概念,科学地分析、论证了艺术的发展规律,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作用。我国古代也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它们都强调了环境对艺术创作、行为习惯养成的巨大影响作用。《我在岛屿读书》则立足该观点,特地将节目录制设置于户外,选择岛屿与书屋为主要拍摄场地,竭力打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治愈场景和“谈笑有鸿儒”的文人墨客谈论的美好场面,精心创造阅读的场景和场域,潜移默化地引导观众参与阅读。例如,《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节目选择在海南分界洲岛录制,之所以选择此地,不仅是因为岛屿拥有独特的浪漫、诗意的栖息地特质,而且还因为此地是苏东坡曾经遭贬谪的流放地。古今对比,造就了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独有的浪漫氛围。并且“书屋”这一主要拍摄场地,也是源于“书屋”对文人的独特含义。“书屋”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读书人的精神自留地,其不仅是文人安身立命的道场,更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第一季节目中的书屋还被余华取名为“分界书屋”,目的是为了区隔纷繁的快节奏生活和诗意浪漫的阅读生活,营造一个怡然自得的阅读场域,呼吁更多人参与阅读,享受精神的陶冶。
嘉宾选择:展现真实与祛魅,悬置主持角色
《我在岛屿读书》与其他读书类节目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嘉宾的选择。该节目邀请余华、苏童、西川、祝勇、叶兆言等知名作家来到岛屿生活,通过洽谈文学、分享文学知识,展现文人真实的生活面貌,达到对文人“神”之地位的祛魅,用接地气的方式打造平易近人的文人形象,证明文学并非是束之高阁的不可触碰之物,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也能自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特别是“文学段子手”余华的加入,他在节目中“金句”频出,极大地打破世人对文人墨客的刻板印象。余华一句“能吃的人就能写作”“我好像是比苏童帅点儿”瞬间将严肃的文学聚会转换为文坛老友们的闲聊,不仅瞬间拉近了普通人与文学大师之间的心理距离,还增强了文学爱好者对文学追求的信心。此外,该节目邀请的飞行嘉宾涵盖了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摄影师肖全、《收获》杂志社编辑程永新、诗人欧阳江河、当代作家马伯庸、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焦典等,展现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艺术领域、不同社会身份的嘉宾之间的观点的碰撞,呈现了立体全面的文人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学追梦过程。除此之外,节目还弱化甚至悬置了主持人的角色,让控制节目节奏和流程的房琪、叶子参与到岛屿读书生活当中,扮演“图书管理员”角色,展现真实的书屋世界,以便观众能身临其境地达到“阅读”的高峰。
内容呈现:关照现实与诗意,回应社会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要求,我国文人自古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担当,注重在文艺创作中回应社会议题。《我在岛屿读书》同样坚持“铁肩担道义”的拳拳之心,对社会议题的讨论和讲解俯首皆是,它关照现实与诗意,自觉回应时代命题,实现了对现实议题的增量。例如,作家阿来携带另一重身份——《科幻世界》编辑到来,引发了作家们对科幻作品和方言写作魅力的讨论,大家纷纷赞扬科幻题材作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也追忆起各自的故乡,抒发家乡故土对自己写作的影响,肯定“乡音独特”的共鸣效果。此外,该节目不仅针对“小说改编剧本”“翻译文学作品”“碎片化阅读和精品阅读”“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AI写作能否取代作家写作”等现实社会话题进行了讨论,同时还关注文学世界的浪漫。例如,组织嘉宾在崖壁上观看电影、在海边面朝大海朗诵,让文学不再缄默,而是将其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新焕发文学的生机与活力,激发潜在受众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
环节设置:分享书单与来信,满足受众需求
《我在岛屿读书》能够异军突起的另一原因在于注重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正如作家苏童所谈,“所谓作家,就是那些给陌生人写信的人。陌生人地址不详,所以,终其一生,一个作家要发出无数地址不详的信件。这些信件命运各异,大多数信件投入漫长的黑暗中,或者安放在图书馆灰尘蒙蒙的角落里,只有少数信件是幸运的”。因此,该节目也高度重视读者的反馈,用最传统的媒介形式承载起这份赤诚的交流。例如,该节目设置有“读者来信”环节,余华、苏童等作家能够直接与读者来信对话,完成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者之间跨越时空的沟通和交流。读者杨本芬的来信提到她暮年才开始写作,但为了实现自己年轻时的文学梦想,现在仍在持续学习,并向余华等人推荐了自己写作的书籍《我本芬芳》,引发了作家们对老年写作的讨论以及对坚持写作的风尚的赞扬,实现了作家、读者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完美闭环。此外,在每期节目尾声,往往会选取部分嘉宾来担任“读书推介官”和“书屋值班员”,负责为观众“开书单”,推介值得阅读的书目,以满足观众对阅读的需求。同时,该节目与京东图书、今日头条达成了战略合作,使观众可以扫描节目播出页面的二维码购买节目中的同款书籍,有利于缩短消费的时间差,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
社会价值:开启文学朝圣之路,打造生活美学范式
传播文学知识,传承文人气质
如果说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让广大观众注意到了文学的力量,那么,《我在岛屿读书》则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我在岛屿读书》将我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学家们齐聚一堂,通过他们之间稀松平常的交流和捧读书本闲坐的阅读场景,向观众展现了阅读和文学对生活的影响。例如,房琪形容海浪拍打礁石时海水的颜色“像果冻一样”,而诗人西川却说“海浪打在石头上,它形成一次相见,形成下一次相见,就是没完没了地重复这样的一种相遇”。西川恰如其分的形容,饱含诗人的浪漫情愫,不仅让人惊叹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感知力,也能够让观众在作家身体力行的演示中感受文学的魅力,以便观众通过增强阅读的方式来提升文学素养,避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除此之外,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也通过节目让人感怀。苏童说,“背着铁生,我感受得到他的体温,那是文学圣洁的灵魂”;余华说,“巴金先生的长寿,给予了我们这一代作家自由成长的时间”;欧阳江河说,“苏东坡在我们身上活着,都活在月亮永恒的照耀下”。作家们在节目中向观众呈现了自己对文学追求的热烈、赤诚之心,也展现出了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这种情谊铸就了当代文坛包容、开放、互相成长的良好创作氛围,鼓舞着广大文学爱好者开启炽烈的文学朝圣之路,在文学的海洋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关注时代议题,助力全民阅读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国越发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我在岛屿读书》便在“建设书香中国”的时代感召下应运而生。它以推动全民参与阅读为主旨,时刻关注时代议题,让嘉宾于节目中各抒己见、参与讨论。例如,针对热议的“AI写作能否代替人类”话题,即便各个领域都有AI学术讨论甚至专著出现,但是作家的话语总是别具一格。苏童说,“文学一定是最后一个堡垒”,的确,在因为人工智能高度发达而引发的失业焦虑中,这句话能够让观众在节目中找到文学与现代舆论的契合点,也充分展现了电视节目“为人民抒怀”的使命与担当。除此之外,正如同苏童所说“阅读能够使人有更多的记忆,能够增强精神的厚度”,该节目通过全民阅读场域的构建,不仅能够促使观众重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感悟灵魂的召唤,还能够让观众收获文化养分,寻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
打造生活范式,给予舒压出口
《我在岛屿读书》不同于以往的读书类节目,它极大地削弱了综艺元素,更像是一部微纪实视频,不刻意设计任务和挑战,任由嘉宾自由行动。海岛、微风、阳光、美食、好友与柴犬,采用生活流的方式记录了中国顶尖文人集群的生活,向观众呈现了“生活美学”新范式。通过围炉煮茶、崖壁观影、海边朗诵、篝火话剧等一系列由嘉宾自发组织的文学活动无不将“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融入细枝末节中,并以“文学”为中心讲述了人与文学、生活与文学的故事。例如,海边朗诵会中,西川击鼓而歌,将“歌以咏志”具象化,向大海诉说着他与文学的故事;肖全的到来,带来《我们这一代》特别摄影展,通过光影的记录,展现了一段段鲜活的文坛往事、一幅幅沸腾的生活景象。如同读者留言,“你来我往之间,文学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日常生活的碰撞和巧思”,《我在岛屿读书》通过对文学家们诗意浪漫生活的捕捉,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地打造文人生活范式,带领观众在方寸之间,感怀万千,进入一种宽广而舒缓的精神世界。
《我在岛屿读书》的隐忧与纾困
形式固化:加强策划与创新形式
即便《我在岛屿读书》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但美中不足的是,节目始终以“岛屿+书屋”为阅读场景,通过作家与嘉宾的分享和讨论来呈现文学的魅力。长时间采用单一的形式可能会使观众感到单调乏味,缺乏新鲜感。此外,节目在创意点上的不足也影响了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了保持节目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节目组应当不断探索新的节目形式。例如,可以增加户外拍摄环节,将读书与旅行相结合,或者引入虚拟现实(VR)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阅读体验。针对策划力不足问题,节目组应当加强对书籍和话题的策划,选择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书籍进行分享和讨论。在节目录制前,可以对书籍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和深层含义,为观众提供更为丰富和深入的阅读体验。例如,可咨询陈晓卿、关正文或汤浩等知名导演的意见,将他们的独特见解引用到节目策划中,于文学深处进行精神的共振与交流,向外界展现出更为丰富的解读思维和视野,与观众一同构建出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文学世界。
解读片面:增添跨文学领域学者
该节目的又一不足在于嘉宾类别的选取较为单一。现代社会中,“文学无用论”大行其道,对此,乔·莫兰在《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一书中曾谈到“人文社科的危机实则是学科本身的危机,是知识组织方式本身的危机,关注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的互动和对话便可破局”。那么,在讲求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当下,《我在岛屿读书》可以选取跨文学领域的学者为飞行嘉宾,在节目中形成文学与工科、理科等不同学科之间的观点碰撞,这样不仅能够打破认知上的壁垒,促进形成更为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而且也能够更好地传递出阅读并非文学者专利,只要有足够细腻的生活洞察力,并且愿意阅读,就可以成为读者,甚至成为作家。虽然术业有专攻,作为一档读书类节目应当有文坛巨匠保驾护航,但要想迸发出新的思维火花,跨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组可邀请各行各业的阅读爱好者参与其中,以弥补对生活现象的解读片面。
互动不足:增加读者参与活动
节目从受众本位出发,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审美体验和观看需求,但从节目内部的建构来看,读者参与的形式单一且机会较为不足。读者往往以书信形式参与岛屿生活,只有只言片语的单向传播,并没有及时收到作家的反馈。第一季中作家黄蓓佳的到来,与节目组安排的小读者们进行了深入且直接的交流,在笔者看来,是一次值得借鉴的互动形式。第二季,中叶子带来的两位南大“旁听生”便形同虚设,并未做丝毫的沟通交流,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与此同时,生活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文学也应当适时做出调整,要想直接打破过去认知中的分野,作家也应当主动“拥抱”潜在读者。因此,在笔者看来,为了规避与读者互动不足的缺憾,节目组可以在观众中选拔适宜的人选,参与到节目的部分读书分享活动中,实现与作家之间的直接沟通。这不仅能够促成读者与作家之间思想的碰撞,拓宽艺术视野,而且也利于增强观众对节目的忠诚度。
《我在岛屿读书》从阅读入手,让作家们走入海岛,在场景营造、嘉宾选择、内容呈现、环节设置方面锐意革新。在缄默的文学深蓝中,不断向观众彰显文学的力量和生活的哲学,用慢节奏的方式述说着千百年来积淀的文人风骨,也以小见大地触发了观众对全面阅读、方言写作、虚构与非虚构、阅读意义等社会议题的审视与自反,诠释了读书类节目的价值回归和责任担当,为国内同类型电视节目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