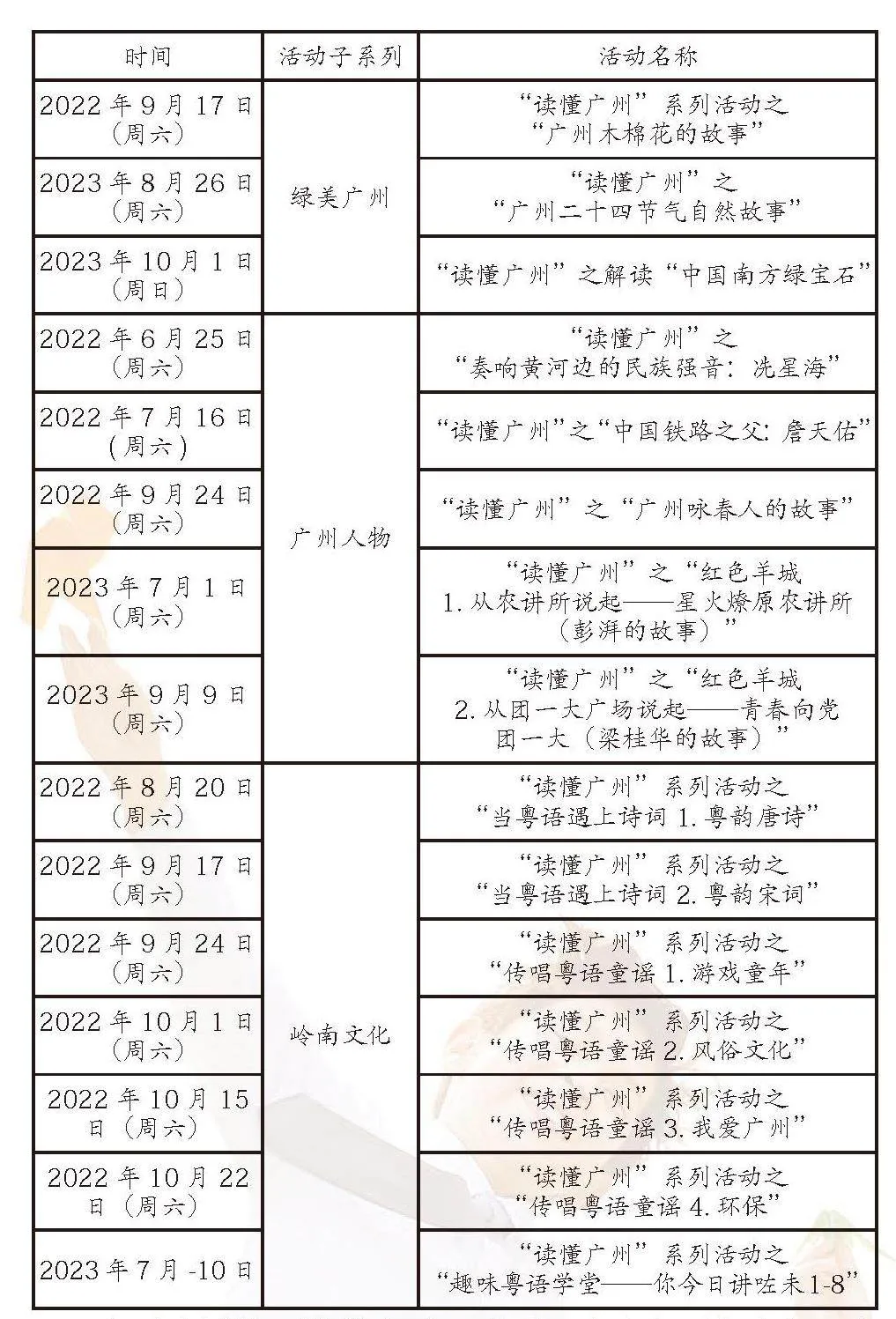摘要:广州作为国际型贸易海港城市,区别于其他内陆城市,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海外贸易起主导性作用。现以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切入点,探讨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两宋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城市格局不匹配。为此,朝廷不断扩大城垣、扩张空间、疏浚濠涌,广州最终形成“三城并立,六脉穿城”的城市空间格局。
城市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文环境的空间载体,是城市物质形态表征与社会形态的总和。广州自古便是岭南政治、文化重镇,公元前214年建城后,历经多次修建。数百年间,广州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变化,直至两宋时期,“三城并立,六脉穿城”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演变,但保留至今的整体城市格局仍以宋代时期为主。所以,研究宋代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宋代广州是我国最大的海港城市之一,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广州作为海港型城市,其商品经济、海上贸易、城市文化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两宋时期,广州的城市功能分区不断细化,城垣外扩,内外港联系加强,新城旧城融合,共同构成了新的广州城市格局。基于此,本文以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出发点,对两宋时期沿海港口城市的空间格局及演变进行分析。
宋代海外贸易对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扩建城池维护贸易稳定
宋代广州的商业发展迅速,导致人口大量聚集,城内居住空间十分紧张,当时富商、洋行大多居于城外西关一带,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宋廷为加固城防,对广州城进行第一次大规模修建,东城和西城的修建至此开始[1-2]。所以,修筑东西二城,主因是人口激增,保护贸易稳定。宋廷为改善城内民众居住环境,于宋神宗元年(1068)开始修筑东城;又于熙宁五年(1072)再次修筑西城[3]。南宋时期,宋廷于嘉定三年(1210)开始修筑南城(雁翅城)[4]。至此,三城并立的格局初步形成。由此可见,南城扩建的根本动因与东西二城相似,都源于广州贸易的发展。
兴修水利保障商业运输
1.疏浚濠涌
宋代,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迅速,指南针已运用于航海,货船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广州成为宋代船舶制造业的主要基地之一,这些条件有助于广州发展海外贸易。该阶段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海商,对海上贸易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依托稳固的航海基础,宋代广州的经济核心以海外贸易为主,城内丰富的自然水系为建设水道交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水网作为交通运输的命脉,对城市形态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5]。宋廷为方便往来商船在广州的转运、通航、交易,实现进出口商品的一体化购销,结合城市内部丰富的自然水系,疏浚濠涌,构建了完善的自然与人工结合的水网体系,发挥其航运、防火、排水、景观等功能。人工水网体系主要由以下水道构成。
六脉渠是宋廷在南汉水网的基础上重新疏浚而成的,水道呈六条南北趋势[6],承担着交通运载和城市排水的功能。商业发展对六脉渠的建设和布局的作用不可小觑。宋代六脉渠中的“五脉”集中于西城商业区。西城分布着众多商业区,这些商业区被路网分割开,为陆路交通提供了基础,这种布局顺应了商业扩展结果[7]。六脉渠汇集了广州城北的水系分支,并将它们分别引流至东濠、西濠、玉带濠,殊途同归汇入珠江,形成了由六脉渠、内濠至江河的三级水系[8]。为解决城内排水问题,宋廷将环城濠池与六脉渠连接,构建了贯穿全城的水网体系。水系的连通使船只可以直接驶进城内进行交易,便利了货物运输。
1011年,玉带濠开凿于子城南段河道,宽度70米左右,并于1210年修筑南城(雁翅城)时,将玉带濠括入其中。1071年,宋廷开始疏浚玉带濠。之后,玉带濠历经多次修建,其大部分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由魏璀带领建造,水面宽60米左右、深至9米[9]。玉带濠不仅保护了船只,还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商业发展。为招揽更多外商,朝廷陆续修建了一系列外商招待机构,如西澳东岸的共乐楼和玉带濠沿线的海山楼。西澳码头与玉带濠区域共同构成了两大核心区域[10]。
唐代,南濠(古西澳)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11]。但当时,南濠尚未并入广州城内,直至宋代修建西城时,南濠两侧皆为商业区,宋廷考虑商业密集区的防火措施,才将南濠纳入西城,位于西城南[12]。南濠的疏浚带动周边商业进一步繁荣,并发展为以南濠为中心的周边商业区以及附属管理机构等。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昭晔知广州,始凿濠为池,以通舟楫”表明,这次修筑专为通航船只开凿,南濠的修建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南宋时,东濠整体位于南城东部,始于东水关,往东承接扶胥波罗水道。东濠口为一海湾形势,水面广阔,东濠位于入海口附近,具有地理优势,是各地商船停靠的交通枢纽。《宋史·邵晔传》有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广州濠频海,海蕃舶至,常苦飓风为害,晔凿濠系舟,飓不能害”,提高了城市航运承载力[13]。
2.港口建设
港口自古以来都是广州的交通要塞之一。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珠江水系西、北、东三江交汇处,濒临南海,城中水网密布、水道纵横。优越的水文条件及优良港口使广州成为联系中原地区与海外各国的重要纽带,奠定了广州国际海港城市的地位。两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港码头包括位于东城的东澳、西澳、坐落于西城的清水濠和南濠;外港除了扶胥码头以外,还包括新建的琵琶洲港口和大通港口。港口选址呈现外港向城市内部移动、内港逐渐融入城内的总体特征。
首先,外港向城市内移的港口选址特征源于广州水运交通的重要地位。港口作为船只停泊、导航等的重要节点,具有联通内外的重要职能,广州海外贸易的商业模式对港口码头的选址具有直接影响。两宋时期,外港的形态特征呈现向城区位移的趋势,琵琶州港口与大通港虽然同为外港,但职能不同,分别满足了外贸和内贸的需求。其中,琵琶州码头主要用于联通海外贸易,而位于花地的大通港则是为了满足与西江、北江等周边流域与日俱增的内贸需求[14]。
其次,内港融入城垣的特征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广州城的港口周边发展出“蕃坊”商贸区。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外商人口增多,宋代“蕃坊”区域不断扩大,除商业区外,该区域周边还形成了居住区,体现出港口与城市进一步融合的特征[15]。由此可见,港口的经济职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随着港口周边商业区的经济职能越来越凸显,港口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港口的功能与其附近商业区的功能产生矛盾时,港口被迫向城市外围地区搬迁,导致城市空间形态上的改变。
商业主导改变城市布局
1.商业主导新型开放布局
中国古代城市职能以行政功能为主,城市布局以及道路规划往往以官衙、官舍等为中心。广州城中,子城和东城是这种城市布局的代表,其作为行政类官衙主要所在地,整体格局受政治因素主导,以府衙为中心,呈丁字形排布。宋代广州的经济职能日益显著,城市人口日益稠密,官衙、学宫、民居等区域交错混杂。例如,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载广州子城,“其中甚隘小,仅可容府署仓库而已”,之前以行政职能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布局,不足以满足广州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因此,宋朝改变了以行政职能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形成了“商业为主,行政为辅”的城市布局,体现出由商业主导的开放性布局。例如,西城以商业功能为主,其街道形态区别于子城和东城,街道布局呈现以道路为主的网格状,更利于商业运输和市肆布局。
2.书院搬迁远离商业中心
宋仁宗后,广州城中书院逐渐兴起。广府学宫于1044年兴建于西城,后因西城重修,便于皇佑二年(1050)迁至东城,熙宁六年(1073),广府学宫回迁至西城[16]。书院等文教空间同样受到广州城内商业环境的影响。当时的经略使章楶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对人有十分重要的教化作用,而西城的商业环境不适宜读书,便提出书院需要另择新址[17]。在他看来,番山地域适合修建书院,绍圣二年(1095),广府学宫在番山落成[18]。受此影响,贡院、番山书院和禺山书院等文教空间纷纷搬迁,选址于环境较好且不受商业干扰的番山、禺山。除了州学,县学也搬迁至远离干扰的区域。例如,西城的南海县学从府县周边搬至兰湖,东城的番禺县学搬迁至珠江边[19]。从书院的选址变迁和海外贸易发展中不难看出,书院等文教空间倾向于聚集在城市中环境优美、安静的地方,并且远离喧嚣的商业区。
3.增设“蕃坊”管理蕃商
随着宋朝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居住在城内的蕃商越来越多,但没有专门的居住区,与汉人混居城内。“土生蕃客”和“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等现象在当时屡见不鲜。为避免蕃商与汉人发生冲突,保护蕃商的财产安全,便于对蕃商进行管理,宋政府借鉴唐朝的治理方法,划分专门区域供蕃商们居住,这些区域被称为“蕃坊”(位于今光塔路怀圣寺附近)。并且“蕃坊”中设置“蕃长”以便管理和维护蕃商居住区的稳定[20]。宋政府还设置“蕃学”,用于解决蕃商子女的教育问题。“蕃坊”的设立体现出城市功能分区的细化,满足了城内不同居民的生活需求。
卫星市镇缓解主城压力
城市发展至一定规模时,部分城内居民生活受限,倾向于移居交通便利的城郊,一些商品生产和交易迁移至城郊的市镇。商品交易和人口具有一定规模后,逐渐形成较为独立的卫星市镇。这些卫星市镇分摊了广州城的部分职能,并且兼具城市和乡村的优点。其形成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军镇转化为市镇。石门镇是典型例子,其原为广州西北水路要冲,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是重要的军事市镇,加之战时粮草运输道路通畅,基本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地理、交通条件较为完备。由于宋代岭南地区远离战乱,石门镇等军镇的军事职能削弱,随着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军镇逐渐向商业型市镇过渡。其二,草市发展为市镇。草市是一种新的交易市场,论级别,其与“官市”相对立;论地点,其位于城外、交通要道等;论组织,其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市场,所以初期较为简陋。宋朝社会相对安定,政府以纳税为条件确立草市的合法性。在社会安定、政策扶持的双重保障下,草市很快成为最具活力的市场,当草市税收达到一定标准时,即可升级为“市镇”。通过以上途径,广州主城周围的卫星城镇逐渐发展起来,人口及交易压力得到缓解。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兴盛带动了广州周边城镇的发展,并形成了以广州城为中心、周边八个卫星市镇围绕的结构。因受到当地繁荣的海外贸易影响,这八镇均位于珠江航道网络中[21]。这些城镇虽然和广州主城的联系紧密程度各不相同,但大多位于广州水网的关键节点。
宋代广州城市空间形态基本形成
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宋代广州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城市的迅速发展,促使城市内部的功能分区越来越清晰,打破了以行政建筑为中心的传统城市格局,初步形成“商为主,政为辅”的城市结构[22]。体现出广州敢于突破传统束缚、不受里坊制和古城垣对城市发展的限制,选择了更加符合经济职能的城市布局,主动修建东西二城,将城外商业区纳入城中,扩大城市规模,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两宋时期,在朝廷主导下先后修筑了集行政办公与商业居住功能的子城、以商业区为主的西城、以行政功能为主的东城。为缓解广州主城的人口及交易压力,城市周围出现了卫星市镇。最终形成三城并立、雁翅城南面拱卫、卫星市镇环绕的城市格局。
古代城市水系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通运输与城市防洪,洪水是古代城市的最大威胁之一,当城市人口大量集聚,水上交通体系成为城市繁荣的基础[23]。相比同时期其他海港城市,广州的城市形态特征与更通达的水网体系、灵活的功能分区、自由的商业发展等息息相关。为满足商品运输的要求、保证船舶停靠的安全性,宋廷依托丰富的自然水系和地理环境进行港口建设和城濠疏浚,以海外贸易需求为导向,将原有的城中水道重新连接,完善内河水运网络体系。宋廷兴修水利,将河渠与商业街市结合,依托玉带濠、文溪、南濠和东濠组成商业区基本架构。至此,两宋时期的广州城水系格局基本形成,即内外八港、城外三濠、城内六脉。
[1]曹家齐.海外贸易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J].中国港口,2012(10):15-17.
[2]刘卫.广州古城水系与城市发展关系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3]谢少亮.广州古城空间格局保护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4]邢君.宋代广州城市工商格局[J].华中建筑,2008(06):163-166.
[5]孙振亚.商业贸易影响下宋代广州城市风貌特征[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9,13(03):40-45.
[6]潘建非.广州城市水系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3.
[7][12]潘建非.广州城市水系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3.
[8]关菲凡.广州城六脉渠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9][11][13]邢君.宋代广州城市工商格局[J].华中建筑,2008(06):163-166.
[10]邢启艳,陆琦,陈亚利.宋代海港商贸型城市功能分区演化及影响因素——以广州为例[J].南方建筑,2020(03):120-126.
[14][15]陈再齐,姚华松.广州古代港—城空间关系演化[J].热带地理,2019,39(01):108-116.
[16][19][22]邢启艳,陆琦,陈亚利.宋代海港商贸型城市功能分区演化及影响因素——以广州为例[J].南方建筑,2020(03):120-126.
[1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18](清)仇巨川.羊城古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20][21]曹家齐.海外贸易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J].中国港口,2012(10):15-17.
[23]刘卫.广州古城水系与城市发展关系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