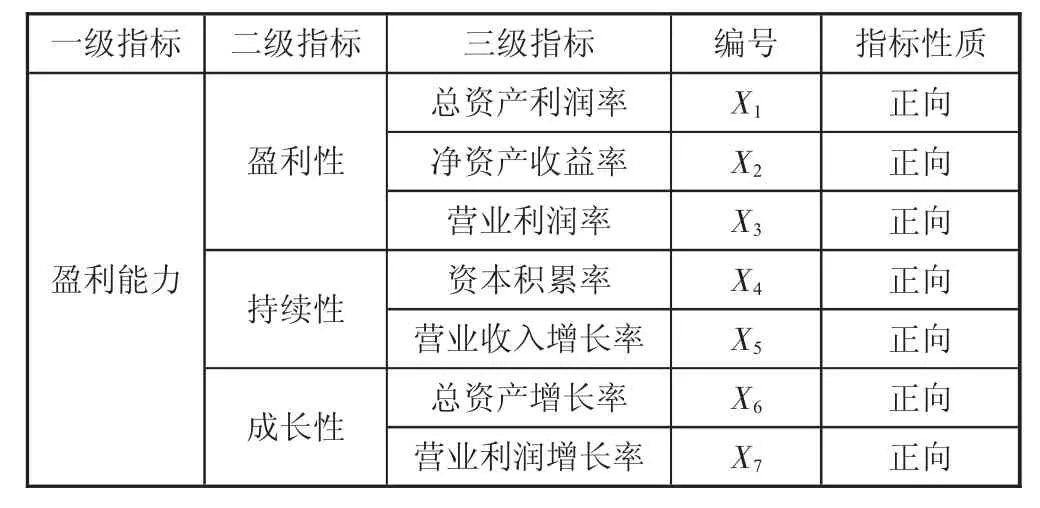作为屏障与分界线的终南山
终南山地形险阻,道路崎岖,大谷有五,小谷过百,连绵数百里。《左传》称终南山是“九州之险”,《长安志》云:“终南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至蓝田,相距八百里,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而外,莫如终南。”终南山为京城长安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其险峻的山势是拱卫京师的天然屏障,所以中国古代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于关中,多少都有以终南山为军事要塞而控制天下的意味。终南山山势巍峨,易守难攻,自古至今都是军事要地。另外,终南山也是从京城通往南方各地的必经之路,从京城往返巴蜀、汉中、东南都须经过终南山,山中自古就有子午谷、傥骆谷、武关、蓝田道、褒斜道等通往各州各道,所以说终南山也是京城联系地方地理、政治、文化、经济的要道。
在自然地理层面,“秦岭—淮河”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南北分界线,作为秦岭中段的主要组成部分,终南山也应被看作是南北地理的分界线。唐人认为终南山是一条综合性的地理界线。例如,欧阳詹《题秦岭》中云:“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其中,“悠悠烟景”无疑是指自然景观,“两边意”“各断肠”讲南北之别自不待言。温庭筠的《过分水岭》写道:“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终南山分隔南北,流水似乎通人情,陪诗人共度山中旅程之后,也分途而去了。
一方面,终南山在南北方降水、气候、河流、植被、土壤、农业生产等方面具有分界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方语言、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分水岭。
终南山在唐代不仅仅是一座横亘于长安城之南的山脉,它的空间意义被寄予了严肃深刻的皇权象征主题,“南山”与“北阙”一起成为庄严帝都的象征。“北阙”是指唐代皇家宫殿里的翔鸾阙与栖凤阙,“南山”是指位于长安城南连绵纵横的终南山。在唐代诗歌里,它们往往作为整个长安城的代称而被文人墨客写入诗中。杜牧在其诗歌《赠终南兰若僧》中写道:“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觉禅门气味长。”作者在此诗中将“北阙”与“南山”同时使用,两个单独的意象上升为一个新的、有独立整体含义的意象。南宋程大昌《雍录》中云:“未央又东,龙首愈增高,而唐大明宫尤在高处,故含元殿基高于平地四丈。含元之北为宣政,宣政之北为紫宸,地每退北,辄又加高。”大明宫含元殿处于长安城北龙首原上之制高点,翔鸾阙、栖凤阙在其两侧而又高出门屋,在空间上形成一种高高在上、俯视帝京的构形,同时也与高耸的终南山构成了区域环境的相互呼应。因此,在文化地理层面,“北阙”与“南山”成为政治权力、绝对权威的象征。作为长安区域文化地理的延伸,南山与宫阙街道一起成为唐王朝的代名词,文人墨客无不在作品中表达对政权的拳拳忠诚与热烈赞美,希冀获得君主的青睐而平步青云,有所作为。例如,张九龄《奉和吏部崔尚书雨后大明朝堂望南山》中写道:“迢递终南顶,朝朝阊阖前……双凤褰为阙,群龙俨若仙……既庶仁斯及,分忧政已宣。”作者描述了庄严肃穆的朝堂秩序,一种权威感油然而生,在这种整饬规范的君臣秩序中,作者赞美君王的仁德与能力,并借机表明自己对朝廷政务的拳拳忠心。
李憕《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中云:“别馆春还淑气催,三宫路转凤凰台。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遥随天仗发,林花不待晓风开。已知圣泽深无限,更喜年芳入睿才。”诗歌中的“北阙”“南山”相对而言,一南一北在文化上涵括了整个长安城的地理,自然界的高山峻岭映射了人类社会的精神营构之象,诗歌末尾,诗人照例表达了对朝廷的深深敬服。在这些诗中,南山不再是秀美的风景,而是尽在天子脚下往来的朝臣,它成为各级官吏的人格化象征。这或许就是唐代诗歌与南山之间的一种默契,南山的空间理念凝聚着权力的象征主题,这也让无数士子对南山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渴望留在都城,创造一番事业,南逾终南则是仕途多舛,人生困顿的开始。
都门与漂泊的界碑:兼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个时代,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兼容并包、文化的中外融合,创造了对社会文化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创造力,也给整个唐代社会带来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唐代士人都满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尤其是文士,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想考取功名,步入仕途,成就一番旷世伟业。由于国力的强大、社会的繁荣,文士身上的活力与自信被激发,他们满怀热情,撰写干谒诗,找寻机会,期冀创造不世功业。例如,李白梦想要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为此四处奔走,献诗作赋,拿自己的作品拜见王公贵族,希望得到引荐,步入仕途以济世报国;高适渴望有朝一日能“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从军边塞,后来封渤海县侯;祖咏也曾吟出“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慷慨激昂之句;杜甫也写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比稷、契,同样汲汲于仕进,为功名四处奔波。可见,唐人整体的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渴望建功立业的。
唐代士人十分重视功名,而长安文化的主导与核心便是典型的帝都文化,长安作为世俗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和主流文化的权威所在,是汲汲于功名的士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唐代文人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朝廷拔擢寒士,科举取士大大刺激了中下层文人的参政热情,到京城参加科举成为广大士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途径。他们从全国各地奔赴长安,四处拜谒,求人举荐,或温习举业,相互切磋。一旦考中功名,随之而来的是无限风光,雁塔题诗,曲江宴饮。孟郊的《登科后》写尽了举子及第后难以名状的狂喜之情。
在帝京长安文化的影响下,唐代士人都有很强烈的“恋京”情节,唐代政治格局内重外轻,士人皆以能在朝中任职为荣耀,放任外官,即使是品阶擢升,也不以为意,时时刻刻思念着长安。有诗可以反映这种情节,如“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刘禹锡谪居外地,终日怀着对长安的思念,即便是微小的外界触动,也会使他思及往事,视通万里,即便是天空偶然飞过的鸟儿,也使他发出远离长安的深切感慨。岑参以豪迈不拘、义气慷慨的边塞诗见长,但在怀念长安时却也一往情深,他在《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一诗中写道“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体现了其对故园的思念如流水一般连绵不绝。
李德裕谪居崖州,只留下《登崖州城作》一首诗歌:“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前半首诗借飞鸟反衬帝京之遥远,后半首借青山烘托悲郁的心情,含蕴深厚,允称杰构。另有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中“故园梨岭下,归路接天涯。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雁南飞不到,书北寄来赊。堪羡神仙客,青云早致家”,此诗颈联可谓唐人“恋京”情节的真实写照。
韩偓垂老去国离乡,孤身流寓湖南,而心却一刻都没有忘怀长安,诗人谪宦过洞庭,见月光皎洁,兴起家国之思,回想起昔年“星斗疏明禁漏残,紫泥封后独凭栏。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阙寒”(韩偓《中秋禁直》)的长安翰苑生涯,而今明月依旧皎洁,诗人却已离开长安,远在湖湘之地了。另外,诗人偶然看见桃子也无限伤感,只是因为此物每年宣进之后,皇帝都会赐予学士,“苦笋恐难同象匕,酪浆无复莹玭珠。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韩偓《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诗人将两地樱笋、牛酪细细比较,今昔之慨不由生发,末句怀念帝都,实际故国已远,魏阙不再,对长安的怀念、对翰苑生活的追忆,都蕴含着诗人不忘君恩、难舍朝廷的深情。事实上,君恩难酬、报国无门一直是韩偓南迁之后最沉重的心结。
再看韩偓深得杜甫《秋兴八首》之五神韵的《梦中作》一诗:“紫宸初启列鸳鸾,直向龙墀对揖班。九曜再新环北极,万方依旧祝南山。礼容肃睦缨緌外,和气熏蒸剑履间。扇合却循黄道退,庙堂谈笑百司闲。”作者以华美之笔再现当年朝中生活,在诗中,“南山”不仅仅是长安之南的高大屏障,更是帝都与政权的代名词。此诗作于唐朝灭亡数年之后,既得之于梦中,梦醒之后心中又别是一番滋味,全诗虽无一句涉及自身寥落状况,但表达的人世沧桑之感并不比杜甫逊色。
生活在盛世的文人士子都怀着巨大的政治热情,对于国家的政治中心长安,有着极强的向往与依恋之情。诗人李白一直渴望入京,希冀得到皇帝赏识而步入仕途,他四处干谒,在天宝元年(742),机会终于来临,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君王的垂青,自己经邦济世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有一种青云直上的感觉,即使是王公大臣,现在也要对他另眼相待,其狂放不羁的性格也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不久李白就因为得罪权贵遭到谗毁,被排挤出朝廷,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但在离开之后,他仍时时刻刻怀念着长安,“长相思,在长安……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李白《长相思》)。诗人始终对长安念念不忘,山高水远,关山阻隔,梦魂难越,见面为难。李白对玄宗、对朝廷的满腔热忱无处施展后,长安就成为他政治失意、感慨悲愤的对象。他的生命体验和人格魅力鲜明地体现在他的长安情结中。即使仍然不被重用,长安依然是他心中的圣地,他对长安的点点滴滴都心怀不舍,在以后的岁月中反复追忆。“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与史中郎敛听黄鹤楼上吹笛》),对于已遭贬谪的李白来说,即使他漫游各地,仍不灭重返长安的希望,时时渴望再度得到征召,对长安的政局也总是十分关切,但是这愿望直到诗人生命终结也没有实现。
“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这首诗作于天宝八载(749),这年春天,李白从兖州出发,东游齐鲁,在金乡遇见了友人韦八返回长安,写下了这首送别诗。从诗的前两句来看,韦八似乎是来金乡做客的,所以说“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这两句像说家常话一样自然,好像随手拈来,毫不费力。三四句凭空起势,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可谓神来之笔,而且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诗人因送友人归京,故思及长安,别出心裁地表现了思念长安的心情,写出了送别时的心潮起伏。“狂风吹我心”采用夸张手法描写送别时的心情。“西挂咸阳树”,用虚拟的手法表现对长安的思念,此处的“咸阳”代指长安,因为上两句已经连用两个长安,故此处用“咸阳”代之,避免了词语的重复使用。这两句表明作者的心已经追逐友人而去,很自然地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此情不可待”二句,语短情长,离别时的复杂心情仅用“不可道”三字带过,似乎万般心事都在不言中。最后两句,写诗人伫立凝望,目送友人归去的情景。当友人越去越远,最后消失不见的时候,诗人看到的是连山的烟雾,在这烟雾迷蒙中,蕴含着诗人与友人离别后的怅惘之情。“望”字重叠使用,显示了诗人伫立之久和依恋之深。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形成了忧国忧民、忠君恋阙的性格,他有着强烈的建立功业的愿望,时刻怀揣对朝廷与国家的责任感,即使身处逆境,其对国家与朝廷的关切也从未消减。杜甫曾在长安潦倒旅居十年后离京另谋生计,临别时对终南山充满了离情,写下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诗人离去之前仍要回望终南山,因为越过终南山就意味着离开帝都,为国效力的理想终落空。离开长安后,他仍抒发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长安的深深依恋,如《秋兴八首》。这组诗写于杜甫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地方藩镇无不虎视眈眈,想要夺取政权,国家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诗人自己疾病缠身,四处漂泊,却仍深深怀念京华岁月,“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秋兴八首》其四),这些诗歌无不满怀深情地感慨今昔,忧虑时局,表达了诗人对昔日繁华长安的深深追忆,同时,体现了诗人对家国深沉的情感。直到走到生命尽头,杜甫依然不能忘却长安,写下了“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长安一直以来是杜甫的心之所系,对长安的怀念正是对心中理想的追念,这理想是他最值得留恋的记忆,是自己一生都无法放弃的追求。
与离开长安的满怀悲苦相比,唐代士人若是从其他地区来到或者返回长安,其喜悦激动的心情往往也是难以言喻的。试看元稹的《西归绝句》(其二):“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书满商山。”首联指诗人左迁江州五年之事,被损的不仅仅是诗人的容颜,更是诗人的心灵与归愁。但是左迁的岁月马上就要结束了,诗人终于获准返回京城,所以连暖人的春风也吹到了武关。秦汉武关,位于商洛丹凤县,是古代丹江与江汉平原交通道路上的名关。诗人拿着回京的书信在丹江畔阅读,喜悦的心情已经透过作者的动作表达出来,虽无言语却胜似千言万语。商山上开满了桃花,似乎驱走了诗人的烦恼,在美好的春日景色中,诗人就要返回京城了,他的轻松快乐跃然纸上,似乎连我们这些后代的读者都能感受到一二。
终南山作为横断南北的界碑与分水岭,在唐代士人眼里有着特殊的意义,北逾终南,就进入京畿之地,步入政治中心、天子脚下,预示人生即将及第授官,飞黄腾达;南越终南山,就是离开皇权中央、帝京之地,往往意味着贬迁漂泊、人生坎坷磨难的开始。前者如韩愈,他在经历一次贬谪之后,于元和十五年返京,先任国子监祭酒,后转任兵部侍郎,接着亲赴镇州召抚王廷凑叛乱。回京后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贬谪生涯虽然苦闷凄凉,一旦回京,昔日的苦闷情怀在韩愈身上得到相当程度的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事随忧共减,诗与酒俱还”(《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幸有用馀俸……未有旦夕忧”(《南溪始泛三首》)的知足情怀。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