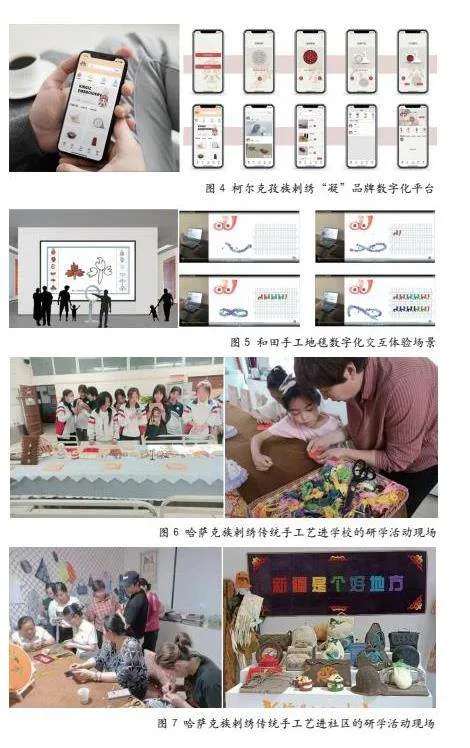现有的传统民间工艺保护工作主要侧重于保护民间手工技艺及其成果,大多忽视了在动态过程中赋予民间传统工艺新的文化意义。现以云南省大理市鹤庆金属工艺为例,指出外来研究者的他者视角及设计理念介入下的传统工艺保护项目,未能从根本上赋予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设计动态的生命力。本文将以设计人类学视角,审视大理鹤庆民间金属工艺的保护与开发状况,使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获得新的生命力,重拾民间文化对人的生命情感价值的赋能。
当前,传统民间工艺的保护多聚焦静态成果的展示与形式化技艺的传承,形成了以“保护”为中心的外部框架,往往忽视了文化生产的动态过程,对传统民间工艺的保护较为被动,难以为继。传统民间工艺作为活态文化的载体,其意义并不止于技艺成果的呈现,更在于工艺制作过程中人与材料、工具、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再生产。然而,现行非遗保护机制往往将技艺固化为静态的“文化遗产”,使其脱离当代生活的语境,成为形式主义保护的典型,在融入现代社会生产与实践的过程中处境尴尬。
将设计人类学的介入视角与传统民间工艺保护的现状结合,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理论论断,即设计人类学不仅批判了传统人类学对文化静态描述和他者视角的局限性,还为非遗保护注入了动态实践和未来导向的生命力。通过设计的介入,设计人类学将民族志研究从单纯的历史性实践描绘扩展成一种面向未来的实践建议,并通过设计活动推动文化生产的再生成。传统人类学往往将设计物解读为文化的象征,而未能将文化视为设计活动的成果加以理解。设计一直是物质文化的驱动力,而物质文化又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阵地之一,所以人类学与设计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设计人类学的观念与方法论的介入与重塑尤为关键。以大理鹤庆金属工艺为例,这一传统民间工艺目前的保护与传承多局限于静态成果的展示与形式化的技艺传承,尚未能真正融入当代生活语境。因此,设计人类学的介入可以通过强调“体验”与“干预”,推动工匠与研究者在技艺实践中共同探索动态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设计学通过理论指导与技术手段创新,不仅能够直接解决现实问题,还能够重新定义工艺实践体验,进而生成新的文化意义,建构开放性的生活语境。当代人类学通过设计参与世间万物的开放性动态关系,使知识在即兴中生成、涌现,获得传承与保护的新文化价值。
对现有传统工艺研究的局限性
“结果”导向的传统工艺保护局限
大理鹤庆金属工艺,尤其新华村的银匠技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传承历程反映了文化的动态流变性。历史上,大理鹤庆金属工艺依托家族作坊传承,通过师徒制代代相传,形成了地方性文化的深厚积淀。然而,这一技艺并非单一延续,而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不断丰富。明清时期,鹤庆银匠在与藏族、纳西族等文化的互动中吸收了多元化的工艺元素,使其金属工艺呈现复杂而独特的艺术特征。这种工艺的核心特性不仅在于其成品的美学价值,还在于制作过程中人与材料、工具和环境的互动与再创作。在新华村,银匠技艺虽然被列为保护项目,但多数保护工作局限于产品展览或传统制作流程的展示,忽视了工匠在日常实践中应对市场需求所进行的创新调整。目前,工匠已经有意识地保存和记录自身工艺脉络。然而,在工匠设立的传习馆中,展示内容多是历史和阶段性作品的梳理,针对工艺表现的内容较少,且呈现方式多拘泥于文字形式的展板。这种“结果”导向的保护模式难以回应现代社会对工艺的动态需求,使技艺逐渐脱离生产生活语境,陷入形式主义。
鹤庆金属工艺的实践经验表明,动态文化生产不仅是技艺传承的核心,也是文化生成的关键。在实践中,银匠通过“边做边想”不断调整技艺形式,既保留了传统特征,又满足了现代消费者对器物功能性和设计感的需求。根据需求和对象的不同,鹤庆工匠能够广泛地吸收技艺特点,并灵活融入自身的工艺体系。随着时代变迁,消费对象及其需求发生变化,鹤庆新华村的工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作藏族生活题材、宗教题材的金银器,逐步转变为制作以汉族茶文化及其周边的金银器。设计人类学提供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保护与开发视角,强调从静态保护向动态实践转变,通过研究人与物、工具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将文化生产作为不断生成与适应的活态实践。只有这样,鹤庆金属工艺才能在当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实现文化价值的再生产与持续传承。
外来研究者的他者视角问题
在鹤庆新华村的金属工艺传承中,外来研究者的介入往往以观察者身份进行静态记录,关注传统技艺的外在表现,如器物的工艺细节和纹样符号,但忽略了工匠在文化生产中的主体性。新华村的银匠以家族作坊为单位,通过日常实践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他们不仅传承了传统白族图案技法,还从藏族宗教器物需求中吸收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装饰风格。藏族金银工匠对錾刻工艺和纹样的理解比较深入,而白族工匠能够很好地处理大型金属料的初步加工,因此两方最初通过技艺交换的方式进行学习交流。然而,外来研究者的静态描述多将银器作品视为传统文化的固化成果,忽略了工匠在与材料、工具互动中的能动性。
20世纪中期,大量藏族寺庙对宗教器物的需求推动了鹤庆银匠的技术创新。他们对传统工具(如铁马、打制锤)的改良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在实践中创造出适应新市场的器物形式。这一动态生成的过程常常被外来研究的“结果导向”所忽略,工匠的实践智慧未能被完整呈现,主体性被置于次要地位。
近年来,部分设计开发项目试图通过复刻传统银器图案与技艺,实现鹤庆金属工艺的保护,但这种形式化的保护常常脱离现实的生产生活。新华村的银器被开发为旅游商品后,许多项目仅关注其美学价值和历史传承的静态展示,而未充分考虑工匠在实践中如何调整设计以适应现代消费需求。这种浅层的设计介入导致了文化保护与现实开发的脱节,无法充分激发工艺的生命力。新华村开发的出名的作品有寸发标“九龙壶”和母炳林“银内胆保温杯”。部分外来设计师介入后,仅复刻传统纹样用于纪念性商品制作,忽略了工匠日常生产中“边做边想”的即时创作特点。银匠为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通过创新设计(如加入现代装饰元素)实现传统技艺的当代转型,但这一实践过程并未被设计介入充分利用或拓展。
技艺流动中的文化生成
传统与新传统的流动性
鹤庆新华村的银匠技艺不仅是一项传统手工艺,更是不断动态生成与文化适应的活态实践。其制作技法、材料使用与装饰符号的演变过程,深刻体现了“传统”如何通过人与物的互动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新传统”。在制作技法上,鹤庆银匠技艺以传统的手工锻造为基础。早期银匠依靠便携的“小炉匠”设备,如风箱、锤子和钳子,在流动中完成金属加工。这一过程中,工匠不仅传承了白族传统工艺,还通过与藏族、纳西族的文化交流,学习并融入了花丝镶嵌、錾刻等复杂技法。材料的使用也体现了动态生成的特征。早期工匠多使用本地获取的银料,随着外部市场的拓展,逐渐引入铜、金等多样化材料,以满足不同文化与功能需求。在装饰符号方面,鹤庆银器从白族传统纹样(如花卉、鸟兽纹样)到藏族宗教图案(如八吉祥图)以及现代设计元素,展现了文化的多重嵌合。装饰符号不仅是文化的静态体现,更是在动态生产中通过工匠的“边做边想”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工匠通过与现代消费者的互动,在器物中融入了更具审美性和实用性的设计,形成了适应当代需求的“新传统”。新华村银匠在技艺互融的流动中形成的文化互嵌,是他们不断实现创新拓进的重要基石。
动态文化生产与意义生成
在鹤庆新华村,银匠的技艺在人与工具、材料的互动中展现了强大的文化生成力。设计人类学强调动态过程中的文化生成,这在新华村银器锻制技艺的实践中尤为显著。鹤庆银匠在生产实践中,通过不断改良工具与灵活运用材料,形成了动态生成的文化意义。传统的“小炉匠”手艺依赖风箱、锤子等工具,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工艺的进步,工匠们更新了更多高效的锻造技术和工具组合,如由传统的铁锤和铁砧捶揲的纯手工生产模式变为由气动锤辅助的半手工半机械模式。如今,还可以通过钢模冲压一体成型制作纹样丰富的银工艺品,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融入了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学到的新技艺,如藏族的錾刻技术。工具在此过程中不仅是技艺的辅助,更成为文化意义的创造媒介,通过与材料的互动生成了独特的地方性文化符号。
材料的选择同样体现了文化生成的动态性。当地工匠最初使用本地金属料,但随着市场的拓展,逐渐引入纯金、木纹金等其他材料,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材料的变化推动了文化符号的多元化发展,如将传统白族的鸟兽图案与藏族八吉祥纹样结合,这种跨文化融合生成了新的装饰语言,为银器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动态文化生产不仅丰富了技艺的文化内涵,还将技艺保护与市场开发有效结合,避免了传统技艺陷入静态保护的困境。鹤庆金属工艺的传承过程不仅是技法、材料与符号的沿袭,更是文化生产的动态实践。通过人与环境、工具、市场需求的持续互动,传统技艺在“生成”中不断适应现代生活,展现了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这种转变使鹤庆金属工艺成为“传统流动性”与“文化再生产”的典范。
设计人类学对传统工艺保护与开发的理论意义
动态文化生产与人类情感价值
鹤庆新华村的银匠技艺不仅是手工技艺的传承,更是通过人与技艺、人与环境的动态互动,生成情感连接与文化意义的过程。工匠与工具之间的关系尤为深刻,工具不仅是制作的辅助物,更是文化生产的参与者。例如,李文彬掌握的双对流焊接技术不仅体现了这一情感与材料互动的过程,还充分体现了工匠在情感与材料互动中的创造力。在焊接过程中,他通过对气体火焰热能的精准控制,使银焊丝与材料之间形成牢固的冶金结合。这一技术展现了工匠对工具与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在动态实践中赋予了材料新的文化意义。在这一互动中,材料不仅是被塑造的对象,也是文化意义生成的重要媒介,承载着工匠对技艺和环境的深刻理解。
动态生产推动非遗项目融入当代生产生活,实现活态传承。鹤庆新华村的银器制作,通过动态文化生产成功实现了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在设计人类学动态视角的介入下,传统技艺的保护不应止于形式化的展示,而应实现与当代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银匠们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更符合消费者审美的产品,这不仅保留了传统工艺的文化精髓,还生成了新的文化价值。在这种实践中,工匠通过动态调整和创新设计,保持了工艺的生命力。旅游业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新华村银器的流通,使其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
这种动态文化生产表明,技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适应和创造。通过动态的生产实践,工匠们不仅重构了人与技艺的情感联系,还将非遗项目从历史的遗存转变为活态的文化实践,实现了文化的再生产与当代传承。
设计人类学视角的启示
1.理论意义
一是动态过程的文化生成视角。设计人类学强调从“结果”到“过程”的研究转向,将非遗项目视为动态的文化生产实践,而非静态的历史遗存。这种视角为传统技艺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化生成的理论框架,通过探索人与工具、人与环境的互动,揭示文化意义如何在实践中不断生成与再生产。
二是反身性实践的主体性重构。强调研究者在设计介入中的自我反思和动态调整,以更加开放、参与和协作的方式研究与解决社会文化问题,要求研究者反思自身角色,避免以“他者”视角简单介入非遗保护与技艺传承,而是尊重文化生产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鹤庆金属工艺的研究与保护中,反身性实践通过主体性重构,将工匠从静态技艺的传承者转变为动态文化的生产者,使其在生产实践中展现更大的创造力和适应性。这种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反身性批判思潮,开启设计人类学由“结果”向“过程”的转变,设计不再仅视为“物”的结果,而是其与环境条件不断反馈的“行动”过程。研究者与文化主体合作共创,不仅推动了技艺的现代转型,还为非遗保护提供了一种更加平等、开放的理论与实践路径。通过与工匠的平等合作和共创,重新审视传统工艺传承的内在逻辑,为传统工艺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理论支持。
2.现实意义
推动传统工艺融入当代生产生活。在动态实践中,传统工艺的保护不再是单向度的“复刻”或静态展示,而是通过与现代设计和市场需求的结合,实现其在当代生产生活中的深度融入。设计的关键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即促进社会转型的新文化应该来自现代设计以外的设计。设计人类学视角能够激发非遗项目的创新潜力,使传统工艺焕发新的经济与文化价值。
大理鹤庆银匠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代表,不仅是民间工艺传承的形式,更是文化生成与再生产的重要实践场域。从设计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一工艺的保护和开发面临着从“静态保护”向“动态文化生产”转型的迫切需求。
当前传统工艺保护多聚焦于成果的形式化继承,忽略了技艺在动态实践中生成文化意义的过程。大理鹤庆银匠技艺的传承表明,人与工具、材料及环境的深度互动是文化生成的核心,由此通过“边做边想”的实践模式,将文化生成的理念动态化地介入民族民间工艺传承的动态环节。工匠不仅传递了历史技艺,还在生产中创新性地回应现实生活的新需求,让传统技艺注入了新的文化价值。动态文化生产视角凸显了非遗项目的活态特性,使其能够融入当代生产生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工匠通过工具改良、材料创新与设计介入,将鹤庆银匠技艺创造的现代装饰品与旅游商品拓展到对现实生活有更深度文化影响的功能性器物,成功实现了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结合。这种生产过程不仅展现了文化的延续性,还使工艺焕发强大的经济与社会生命力。设计人类学的反身性与实践生成视角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通过动态过程研究,重新审视人与技艺、人与环境的情感联系,赋予传统工艺保护鲜活的情感价值和现实意义。未来,非遗保护的重点应放在动态实践与文化生成,为传统工艺构建活态传承的可持续路径,使其在现代社会中持续焕发活力。设计人类学在对物的共同关注中不断育发,在物的“过程”观察中强调关注物的运动“轨迹”和“新语境化”,通过物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变化透视其中所映射的文化框架和文化内涵。
(作者单位:云南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