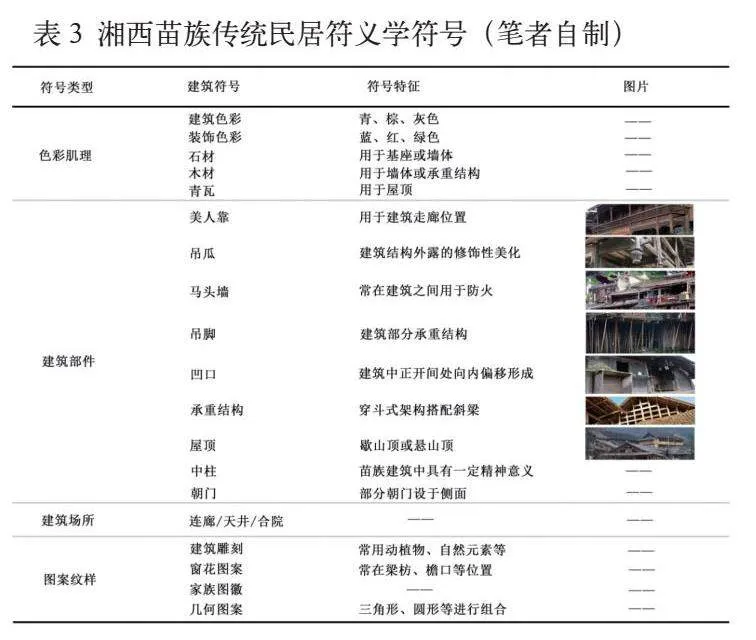摘" 要:海南苗族的蜡染手工艺极富原始特色,与我国其它地区的蜡染工艺相比,在细节上有许多不同,是人类早期蜡染手工艺的活态样本。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海南苗族蜡染的原始特色工具、图案和工艺流程,探讨了原始的点蜡竹笔对其蜡染图案风格的影响,并针对其工艺特色在当代的传承问题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海南苗族,蜡染,手工艺,非遗传承
蜡染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服饰印染技艺之一,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制作中应用尤为广泛。海南苗族女性服饰是我国苗族女性服饰的五大类型之一[1],她们所穿的短裙采用的就是蜡染手工艺,是以蓝靛染为基础的一种蜂蜡防染技艺。与我国川黔滇等苗族聚居地区的蜡染手工艺相比,海南苗族蜡染的工艺流程相似,但绘图工具更为原始、蜡染图案更为简单,保留了人类早期蜡染手工艺的古朴特点和粗犷风格,被列入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原生态的蜡染绘图工具
海南苗族蜡染的主要绘图工具可分为绘图笔和辅助工具两大类,绘图笔主要有点蜡的竹笔和打底稿的豪猪刺;辅助工具主要有熔蜡竹笼、竹筒蜂蜡、竹尺和竹匾,都是就地取材、粗加工或未加工的原生态工具。
(一)点蜡竹笔
点蜡竹笔是海南苗族蜡染手工艺中最有特色的原始工具,用新鲜竹篾弯成,笔触为弧平面,属于一次性的简易工具。其制作步骤是:砍一节长约30厘米的白竹或毛竹,竖向劈开成宽约0.5cm的竹条;取一根竹条用刀剥去内芯,把中间段削细并蘸蜡液烤热,两端向上弯成长臂的“U”状,用藤皮或绳线绑定,一支长约15cm的点蜡竹笔就制作好了。将竹笔放置几天晾干或小火烤干至颜色微黄(不干的话粘不住蜡液),就可以用U形笔头来点蜡了。竹笔的笔头有大小两种规格:大竹笔的弧底长约1cm、宽约2mm,小竹笔的弧底长约5mm、宽约1mm(如图1)。大竹笔用来描画粗长的外轮廓,小竹笔用来描画细短的内部花纹。用海南苗族妇女的话来说,大竹笔是用来“看路的”,小竹笔是用来“看花的”。
相比之下,我国其他苗族基本都已采用金属蜡刀来点蜡,因为金属蜡刀有保温、流畅、耐用等优点。“贵州苗族用于点蜡的工具主要是铜或铝制蜡刀,也有用竹刀、铁刀和锑片刀等……因为用金属蜡刀画的线条精细流畅,近年来在苗族地区已渐渐普及。”[2]不仅如此,金属蜡刀早已经发展完善和系列化了,仅刀头就包括了三角形、梯形、圆轮花朵形等多种形状,可以流畅绘制各种形状的线条。因此,海南苗族的点蜡竹笔可以说是目前少见的原始点蜡工具了。
(二)豪猪刺
豪猪刺是海南苗族蜡染打底稿的工具,取自豪猪身上自然脱落的硬刺。豪猪刺一般长约20cm,细长圆润,中间略粗,一头尖一头钝,使用钝的那头能在白布上划出痕迹且不伤布。用豪猪刺打底稿的优点是干净,不会弄脏白布和手,也正因为如此,打无色底稿也就成为了海南苗族蜡染的工艺特色之一。
(三)竹笼架
竹笼架是海南苗族熔蜡的专用工具,用竹篾编成,为正反喇叭状镂空造型,束腰处有隔层,高约30cm米、口径约25cm(如图2)。竹笼上部用蕉叶垫底,内盛木炭灰,围放三块石头,中间埋火炭,石上搁瓷碟和蜡块,就可以很方便地熔蜡和蘸蜡了。其他地区的苗族以前主要采用冬季烤火的炭盆来熔蜡,现在则有了更为方便的恒温插电熔蜡器。海南长夏无冬,故海南苗族设计了这种轻巧别致的熔蜡竹笼架,具有鲜明的因地制宜特色。
(四)竹筒蜂蜡
海南苗族采用天然的蜂蜡为蜡染介质,并制作成独特的圆筒状蜡条工具(如图3),既方便保存又方便使用。其竹筒蜡条的制作、使用都富有特色:取蜜蜂蜂房加水煮开,冷却后用竹勺底沾取蜂蜡并刮到竹筒里;再将积满蜡屑的竹筒放到炭火上烤,待蜡屑烤化后自然冷却,就得到了长筒状的蜂蜡。使用时,先将竹筒口沿削掉一圈,露出一截蜂蜡,直接搁在竹笼架的碗里进行加热即可熔蜡。每次点蜡剩余的蜡液还可再倒回竹筒中凝固保存。图3是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的两根海南苗族制作的竹筒蜂蜡,上面是从竹筒中剖取出来的一整根蜂蜡条,下面则是一截用剩的尚在竹筒中的蜂蜡条。
(五)竹尺
竹尺实为一细长竹片,用于在布上打蜡染底稿时作比尺用,一般长约40cm、宽约1cm,具有天然环保和简单易得的优点。
(六)竹匾
海南苗族点蜡采用浅口平底的圆竹匾作为垫板,不但轻便,与点蜡竹笔的使用也比较契合。因为海南苗族的点蜡竹笔是竖直使用的,其笔触仅为短小的弧形平面,与竹匾背面贴合度较好,不影响点蜡的均匀平整。
二、单一的传统蜡染图案
(一)单一和抽象化的“大青山纹”传统图案
从历史上看,海南苗族传统的蜡染图案仅有一种三角形的“大青山纹”,因此具有高度单一化的特点。海南苗族约形成于明代中后期,自己没有文字,汉文古籍中对其服饰的记载亦极少。但是,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照片来看,海南苗族的蜡染仅用于女子短裙正面,且图案都只有同一种“大青山纹”(如图4)。1957年国家组织的对海南苗族的全面社会调查报告中也有佐证:“(海南苗族)妇女……下身穿一条长不过膝的短裙,裙为上衣所掩盖,仅在祺夹空隙处显露出白色美丽的蜡染图案花纹,花纹一律是整齐排列的三角形。据他们说,这种服装从祖先到现在都是如此,花纹也是一直保留着”[3]。
从图案本身来看,海南苗族蜡染的“大青山纹”具有几何抽象和重复构图的特点,风格朴实,辨识度非常高。这种“大青山纹”象征着海南苗族世代居住的群山,通常由8~10个二方连续的大三角形组成,其间又是以无数短小的线段构成抽象的神树、蝴蝶、八角花等内容。虽然“大青山纹”的图案比较简单,但由于点蜡竹笔的原始性,完成一条蜡染裙点蜡的时间并不短:“如果是农闲时,点一条蜡染布料要10天时间;如果农忙,则要10多天或20天才能点完。”[4]
(二)原始点蜡竹笔对蜡染图案的潜在影响
海南苗族蜡染“大青山纹”的几何重复构图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其原始点蜡竹笔工具的影响所致。
一方面,由于点蜡竹笔的使用方法非常原始,每蘸一次蜡只能在布上涂一小笔,故其线条都是接续而成的,单一和重复的直线段图案无疑是提高其点蜡效率的最佳选择。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青山纹”图案皆是由短直细密的线段组成的。
另一方面,海南苗族的点蜡竹笔难以描绘曲线,故以抽象化的几何直线构图最为合适,因此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我国其他苗族也有个别使用竹制点蜡工具的,但其工具要略进步一些。例如,贵州省的“麻江绕家人制作枫香染所需要的相关工具比较简单、粗糙,大都是自己制作的。绘制枫香染的工具一般为长10cm左右的竹制小刀,一头是尖头,另一头是平头,平头的一端绘制直线、弧线、圆圈等几何形线条,而尖头用来绘制点状纹样”[5]。点蜡刀笔工具对图案线条风格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粗放的蜡染工艺流程
海南苗族的蜡染和其他苗族的蜡染流程基本相同,但由于工具和图案的不同,工艺环节更为粗放。
(一)“练布”
以前海南苗族用自织的白布蜡染,通常要先“练”一下布。“制作时先将自织的白布用草灰漂白,再把魔芋煮熟搅成浆糊状抹在白布背面;晒干后,放在面板上用牛角或竹节磨成平滑的布壳;按照需要剪成大小不同的幅面,然后点蜡。”[6]“练布”可以使白布变得硬挺、光洁,更适合于点蜡,又不影响蓝靛染料的渗入。
(二)打无色底稿
海南苗族蜡染图案没有粉本,直接以竹条为尺,用豪猪刺在白布上划出大致轮廓,如同布上的折痕一般,故称无色底稿(如图5)。海南苗族妇女对世代传承的“大青山纹”图案烂熟于心,故只需用划痕标记大概位置,点蜡时即可信手拈来。
(三)点蜡
点蜡时,制作新的点蜡竹笔,蘸上蜂蜡蜡液,根据划痕在白布上一点点涂出“大青山纹”图案(如图6)。在点蜡过程中,需保持封蜡层的厚薄均匀适度。由于蜂蜡是点蜡的优秀原料,黏性较大,不易破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点蜡竹笔的不足。
(四)蓝靛染布
点蜡完成之后,提取植物蓝靛料给蜡布染色,反复冷染成蓝黑色即可。
(五)除蜡
烧一锅开水,把染好的蜡布放进去又提起来,反复多次直到把封蜡完全去除,再洗净晒干,即得到了蓝黑底白花的蜡染裙布。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先生在其著作《海南岛民族志》中曾赞叹:“(海南)苗族的蜡染法是极原始的……染色后用开水溶去蜡,就显出染成深蓝与雪白花样的鲜艳的棉布。用这样原始的方法,竞能染出惊人的花样来——令人以为使用了比较复杂的方法。”[7]
四、海南苗族蜡染手工艺特色的传承问题
在过去,海南苗族的蜡染技艺主要是作为女性必备的家庭生活技能而一代代自觉传承。如今,海南苗族蜡染技艺虽然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受各种现实因素影响,其手工艺的传承依然面临着较大的问题。
(一)自染布的衰落使蜡染染布环节变得相对不便
海南苗族妇女过去一直是自己提取植物蓝靛给传统服装染色,蜡染裙的染色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如今,妇女们基本都是购买成品黑布来缝制本民族服饰,省去了自己染布的环节,使得原本可以随时染布的蜡染变得相对不便了。
(二)刺绣和印花挤压了蜡染的生存空间
由于蓝靛染的减少,也由于传统的蜡染工艺程序相对繁杂低效,如今海南苗族妇女们开始用刺绣和印花来替代蜡染。她们有的直接在黑裙布上刺绣“大青山纹”(如图7),有的则定制机绣或工业印花的“大青山纹”短裙。这些绣花或印花的短裙在外观上和传统的蜡染裙相似,但却直接挤压了传统蜡染手工艺的生存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问题的背后也体现出了当今海南苗族对蜡染这种原始手工艺生产方式的迫切改进需要。
五、对海南苗族蜡染技艺传承问题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传统非遗技艺的传承已经转向“活态传承”。非遗的“活态传承”具有“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两大规律:恒定性是指手工艺非遗的核心特质不能随便改变;活态流变性则是指手工艺非遗的某些方面会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生长、改变[8]。对此,研究者普遍认为,“传统工艺遗产中一些重要的、核心的部分承载了这种传统工艺遗产的特色或风格。传统工艺遗产是相对稳定的,但也不是完全静止的,有的也会有变化,但不能改变变化的基本方向,否则就会导致整个工艺特色或风格的改变,发生变异。而一些次要的部分即使发生变化,甚至重大的变化,对传统工艺遗产而言关系并不大”[9]。因此,传统手工艺非遗除了核心工艺和核心图案保持恒定性传承之外,其它都是可以作适应性改变的。故此,海南苗族蜡染技艺可以在保持其核心工艺特色不变的前提下,合理改进工具和丰富图案,更好地促进其活态传承与发展。
(一)改进一次性点蜡竹笔的材质
笔者认为,可以在保持工艺原理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进点蜡竹笔的材质来提高其品质。一次性的点蜡竹笔是形成海南苗族蜡染工艺特色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竹笔的结构和原理是应该保护的核心部分。但是,传承人可以在保留竹笔独特的直线段、短笔触的绘图特色的前提下,采用金属等更耐用和好用的材质来替代现有的一次性竹笔材质,使其在传承过程中既能提升核心工具的品质和效率,又能延续核心工艺的艺术特色。
(二)打破蜡染图案的单一和用途局限
海南苗族历史上单一不变的“大青山纹”图案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要,其非遗文创产品也不等于简单照搬和直接挪用纹样。因此,在保持其蜡染图案艺术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开发新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蜡染图案,也可以借鉴海南苗族丰富的刺绣图案进行蜡染图案创新。进而,才有可能突破过去单一的蜡染图案和仅应用于海南苗族女子传统短裙的局限,开发出新的具有海南苗族风格的蜡染图案并拓宽其应用场景,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切实促进海南苗族蜡染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和活态传承。
六、结语
蜡染手工艺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普及,但不同地域的蜡染技艺在工具和工艺细节等方面往往会有所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蜡染服饰的风格特色。海南苗族的蜡染技艺是我国目前比较少见的还活态保留着原始特色的蜡染手工艺非遗技艺,从而形成了其蜡染裙的特色和差异性。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需求的变迁,海南苗族蜡染只有在保护其核心工艺环节和艺术特色不变的同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向前发展,才能使其得到更符合非遗发展规律的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1]范生姣,麻勇恒.苗族侗族文化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27-129.
[2]杨文斌,杨亮,王振华.苗族蜡染[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71-72.
[3]中南民族大学.海南岛苗族社会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84.
[4]王翠娥.海南苗族蜡染织绣工艺调查——以五指山市南圣镇牙南村染织绣工艺为例[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9):164-167.
[5]周莹.贵州省麻江县绕家枫香染工艺[J].纺织学报,2015(3):83-87.
[6]高昌,林开耀.海南苗族蜡染工艺特点[J].装饰,1999(3):16.
[7]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M].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译.海口:海南省民宗委翻印(内部参考).2016:176.
[8]王文章.坚定文化自信,推进非遗保护[N].人民政协报,2018-03-26.
[9]张建世.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以四川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为例[J].民族研究,2017(2):78-87.
作者简介:张红梅,博士,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海南少数民族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