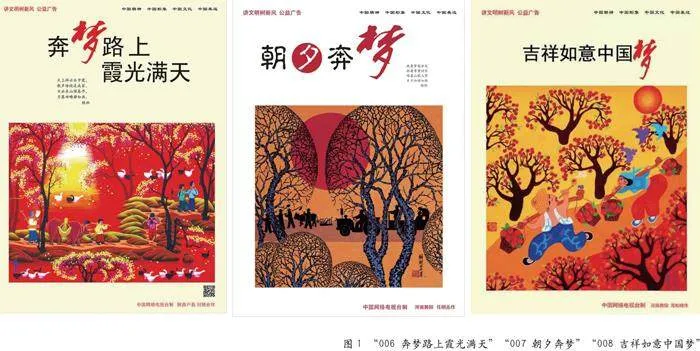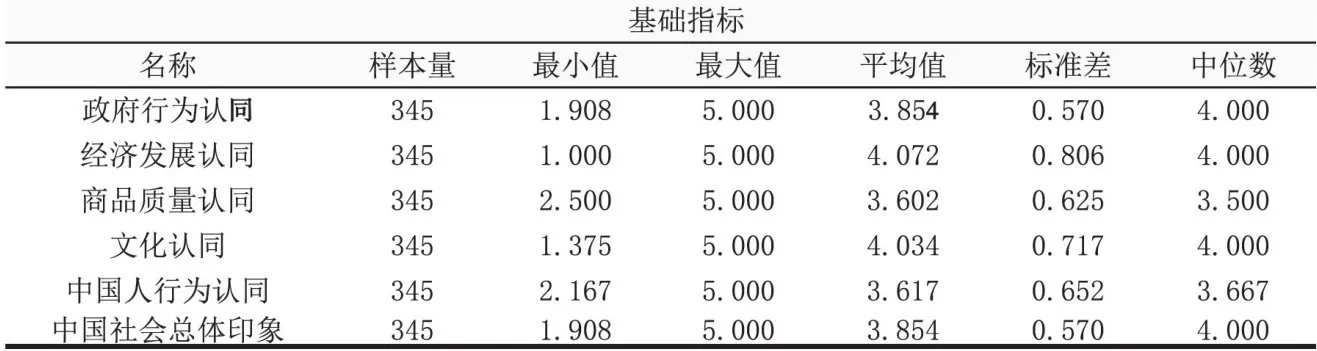摘" 要:基于罗兰·巴特图像符号学的三层信息论,对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9件艺术作品进行语言讯息、外延图像和内涵图像层面的分析,发现这些中国艺术作品运用古今中西文化符号展示了一个多元融合的中国国家形象,在文化身份建构、符号使用与解读、全球语境中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的传播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但也体现了在中国自我形象建构过程中迷茫焦虑的状态。
关键词:罗兰·巴特;图像符号学;威尼斯双年展;艺术作品;中国形象
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形象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发展壮大,也经历了从强调传统文化符号到追求全球化艺术表达的演变。成立于18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是全球规模最大、受众最多的艺术博览会,于1993年迎来了第一批中国艺术家参展,于2005年迎来了中国国家馆[1]。此后中国一直以中国国家馆形式向威尼斯双年展输送及展示大量艺术作品,不少艺术家及其作品受到了学术界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威尼斯双年展已成为向世界尤其是向年轻人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本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中,中国国家馆如何通过艺术符号来构建和传播中国形象?对外到底展示了什么样的形象?其效果如何?
一、理论基础:罗兰·巴特图像符号学的三层信息论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奠定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符号学的基本框架,即“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二元对立结构。他认为符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强调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和线性特征[2]1。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论与索绪尔不同,他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符号(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皮尔斯的符号学更加关注符号的解释和意义生成过程,对后来的符号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2。20世纪中叶,符号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泛应用于文化媒介研究、文学分析等领域。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等学者相继对符号学进行了丰富和扩展[3]。
罗兰·巴特作为20世纪后期符号学的代表性人物,对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创新。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了文学、摄影、时尚、广告等多个方面。其中,影像修辞论是巴特符号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巴特在《影像的修辞》一书中分析了图像作为符号系统的复杂性,他提出图像包含三层意义:信息性意义(linguistic message)、编码性意义(coded iconic message)和非编码性意义(non-coded iconic message),即三层信息论。通过对广告图像尤其是意大利平面广告的分析,揭示了图像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息,阐述这些信息层次是如何在一幅图像中共存并协同工作的。他强调图像的修辞不仅在于视觉元素本身,更在于这些元素如何被文化和社会编码并解读。这一理论将图像的信息分为语言讯息层(Linguistic Message)、外延图像层(Non-coded Iconic Message)和内涵图像层(Coded Iconic Message)三层[4]261-272,揭示了图像传达意义的多层次结构:
(一)语言讯息层(Linguistic Message):为图像中的文字部分,包括标题、说明、标语等。具有锚定功能(Anchorage):固定图像的意义,减少歧义。通过解释和限定,文字信息可以引导观众如何理解图像,排除其他可能的解读;传递功能(Relay):补充图像信息,提供额外解释。文字信息可以补充和扩展图像内容,为图像提供更丰富的语境。
(二)外延图像层(Non-coded Iconic Message):指的是图像的纯视觉元素,如颜色、形状、构图、物体等都是直接呈现的,无需复杂解码即可理解。提供图像的基本视觉信息,直接影响观众的感知和理解。这些信息是图像的表层意义,观众通过直观感受即可获得。
(三)内涵图像层(Coded Iconic Message):是通过文化和社会习得的符号系统解读出来的深层意义,需要观众具备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全面理解。传达图像的深层文化和社会意义,通过符号、隐喻和象征等方式构建复杂的意义体系。
巴特的三层信息理论聚焦于分析图像意义的产生与互动要素,可为视觉艺术作品的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二、基于三层信息理论的" " " " " " " " " " " " "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代表作品分析
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作品,从早期的保守传统表达到现代的大胆创新和文化自省,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化。2024年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以《集:多样性中的和谐》(Atlas:Harmony in Diversity)为主题,定位“美美与共集”,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王晓松和独立策展人蒋军共同策展,展示了1个数字文档集成(100幅古代中国绘画的文献)和8位当代艺术家作品即一共9件艺术作品,旨在探索和谐与多样性的文化价值观,通过艺术作品展示古今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理解[5]。
本研究将对中国国家馆9件艺术作品进行语言讯息层、外延图像层以及内涵图像层的分析,并在每个类别里面分出具体指标,例如语言讯息层以所展现文字为主要指标,外延图像层中分为色彩、画面、形式和风格,内涵图像层中分为符号、隐喻与象征。
(一)语言讯息层:描述时空多元信息
展览现场语言讯息最多的是导览手册上的作者和作品介绍,作者介绍以单位、身份、作品风格和国内外影响力为主,作品介绍以运用材料、创作过程、艺术手法和表达意义为主,如关于作品《亭》(Pavilion),导览册介绍了作者车建全于2003年起以湖滨亭为拍摄对象,用20年时间以固定视角连续捕捉四季中同一个场景,创作了由20幅影像组成的“亭”系列作品,想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亭”在不同季节的多种形象。
从实际展览的艺术作品来看,语言讯息主要集中于作品标题和作者名字,部分以诗画为主的作品中,其主要内容用来定位艺术作品中所涉及的物品、尺寸、年代以及地理位置。如作品《宣纸塔》(Rice Paper Pagoda)的标题就告诉观众其所描绘对象及材料是什么,而作品《状态》指明的是一种情境,《文献装置:海外“大系”图像文献展》(Archive Installation: Image Documentation Exhibition of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则不仅表示出了年份、展示物品以及展览语境更标注了所展示作品的位置与内容,整体上语言信息在这些艺术作品中起到了一个补充介绍与指引观众思考方向的作用。并且在地点描述上呈现出一种多元的世界位置,在命名上也体现出双语特点,既有中文也有英文,形成一种中西结合与全球化的语言信息。本次展览前言多次提及“多元”“传统”“现代”“未来”“地域与全球”的描述,例如关于“多元”的描述,前言中出现了“它象征着全球范围内不同种族、信仰、身份、思想、目的、背景和文化的多元光谱的融合”“体现了吸收和接纳,促进了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机会”等文字,关于“传统与现代 ”则出现了“策展团队从20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沃伯格《记忆女神图集》中汲取灵感”“这是一种平衡和融合传统与现代、区域与全球的努力”等相关描述。整体来说,言语层面在此次展览中比例较少,以前言、作者与作品信息为主并辅以一定的地点与位置信息。
(二)外延图像层分析:传统手法与现代科技结合
从外延图像层面上来讲,作品整体上沿袭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主要审美与色彩,其中以浅色调如米色、白色为主,在色彩风格上呈现出低饱和度与黑白的色彩选择,在画面上则延续了多种中国传统绘画与水墨的风格,其中主要呈现出抽象的类似于水墨笔触的线条以及多种中国传统对象物体,如竹子、文人、山水、雀等古代中国艺术常见的描绘对象,同时也能见到一些西方与全球化的物象,例如比萨斜塔、世界地图、大海与草坪等,呈现出中西交融的画面。例如在《传——与古为徒 与古为新》(Learn from the Past, Innovate for the Future)作品当中,画面上呈现了诸多中国古代现代的亭台楼阁和比萨斜塔之类的西方建筑。又如《文献装置:海外“大系”图像文献展》(Archive Installation: Image Documentation Exhibition of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既有宋代赵佶《竹禽图》等中国传统绘画文献画面,又包含了文献所分布的世界地图。
所有作品整体呈现出传统媒介与当代数字媒介相结合的形式,其中传统媒介材料以宣纸、麻绳等为主,例如《宣纸塔》(Rice Paper Pagoda)选择了古代书法与绘画常用的宣纸、棉线、竹子进行构建,将传统意义上平面使用的宣纸进行空间与功能上的重构,从而进行“形”上的再表达。而现代材质媒介主要以数字屏幕、金属材质、灯光为主。例如《淬厉新之》(Heritage Reimagined)使用了多个电子屏幕作为展现绘画的媒介,《状态》(Status)则使用金属材质来表现书法形式,因而也呈现出一种中西结合的风格。从形式上看,展览整体以当代艺术常见的装置为主,并采用了抽象表现主义风格。例如《书非书》(Writing-Non-Writing),用绳子的不同打结法将文字抽象化,从而进行形而上的表达,并且以一种不规则的装置来呈现作品。
(三)内涵图像层分析:多元包容又宏大空洞的叙事
从符号实现隐喻与象征的内涵信息层来看,中国国家馆作品总体呈现出一种多元与复古的意象,如采用中国文人画、书法、水墨等传统符号,并配以一定数量的全球化符号例如世界地图、西方塔景观等,展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多元并进、美美与共的内涵意义。如《淬厉新之》(Heritage Reimagined),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再创作,用电子屏幕的当代科技方式来呈现,对传统媒介形式进行解构与重构,最终体现出一种中西方文明相融合的理念。而《传——与古为徒 与古为新》(Learn from the Past,Innovate for the Future)则强调传承与创新,通过学习古代文化实现现代创新。但同时,这些作品本质上是一种传统文人画的意象,与古代艺术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并无本质性区别,让受众能展开当代联想的主要聚焦在当代媒介及西方技法的使用上。
如果再进一步对每一件作品进行深挖,结合所有信息则显得叙事不够丰富并且空洞乏味,例如《亭》(Pavilion)用固定视角来拍摄20年来不同季节的同一个亭子,观者应当佩服于作者“纪录”的恒心毅力,但由于作品云雾迷蒙的主画面本身缺乏视觉冲击力以及前面文件柜里又陈列了系列中外展馆的水景影像文件,给人感觉除了“历时杂糅”“中国文化”等以外,并没有更多清晰生动的文化内涵可传递。另一个作品《百鸟图迹》(Symphony of Birds)把《珍禽写生》和《中国古画总集》中各种鸟类用徽章雕塑的形式来展现,本想通过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方式来指挥表演者戴着鸟形饰品穿梭于室内外空间(园林)、唤起群鸟聚集的意象,但实际上由于缺乏组织,表演在观众开放日并未进行,多枚微型鸟类雕塑和徽章就简单无序地放在文件柜中,让大家除了知道这是来自中国的鸟的作品以外别无所获。总之,结合所有的文字与图像符号,得出的是一个宏观叙事,其本意是在把各种各样能体现“中国艺术”并含有“包容”“全球”意义的作品集合在一起,让观众看到“这里有很多融汇古今中西的具有中国特质的中国作品集合在了一起”,每个作品以其模糊的个体叙事与相似内涵通过集合的方式为整个展览进行了恰如主题的宏大叙事,其本质是告诉观众这是中国的,中国的价值观是多元包容、古今并存的,但较为“宏大空洞”。
(四)符号的解读:被西方艺术思潮与现代科技包装的作品
符号的使用在中国国家馆展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展览中主要使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亭台楼阁”“飞禽走兽”“风景名胜”“传统技艺”以及“当代技艺”作为主要表达符号,使展览在整体上充满一种具有传统中国风格的异域风情。例如作品《魂·韵》(Soul·Rhyme)是一组人物雕像,作者焦兴涛使用金属加工厂剩余的铜条和铜片,结合中国线条化和外国块状化的雕像元素,进行古代雕像解构与当代再造,并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生成多样化动态图像和人物,象征古今中外文化交流,既具有前工业时代风格、散发怀旧魅力,又展示了文化传统与当代生活的融合与冲突。
但针对很多符号来进行解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展览总体呈现的还是“新瓶装旧酒”的形象。利用传统中国文化符号如“宣纸”等强中国性的材料,配合西方的艺术思潮与媒介,并不能赋予整个展览一种全新的中国叙事。用不同方式来诠释一种古代叙事的价值在这里是一个疑问。例如作品《淬厉新之》(Heritage Reimagined)通过电子屏幕展示传统中国绘画,但其本质上展示的仍是“中国绘画”,用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来诠释中国山水虽然有中西结合之意,但其内核仍然是中国山水画。从观者角度来说看到的是一种被西方艺术思潮与现代科技包装的作品。用水墨结合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并不新鲜,在数十年前赵无极便是这种方法的开创者,徐冰早在90年代也使用过类似的叙事。这些作品除去本身的宏大主题以外,即使结合作品名字与所有信息,也很难得出更多的叙事细节与层次。
在所有9件作品中,除去对于西方新媒介的使用与艺术思潮的结合,中国当代符号是缺失的。一方面这些作品是“政治化的高度去政治化”,通过一种政治上的价值观而将政治符号进行抹平,而现代政治符号的使用是构成当代艺术“当代性”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传统符号与中国当代生活方式并没有产生关联,观众无法通过简单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中国山水”来想象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与生活,这样的符号使用反而会加深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让中国故事停留在古代层面,正如徐翔曾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当代文化传播相对较弱,导致文化形象失衡[6]。
另外,这些国家馆作品的选择并非某一人的随意决策,其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官方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总体上无论从作品的选择、主题以及整体展览的策划来讲,其系列作品与核心符号所表达的从价值上来说皆围绕着“多元包容”“融合古今”所展开,传递出的是“古今并存”“中西融合”“中国特征”“异域风情”“宏大空洞”的形象联想。
三、结论:自我形象建构的多元融合和迷茫焦虑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通过精妙的影像修辞,展示了一个多层次、丰富多彩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些艺术作品在文化身份的建构、符号的使用与解读、全球语境中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的传播等方面展示了深刻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对自我形象建构中的多元融合态度和迷茫焦虑状态。
(一)传达了积极融合理念的中国形象
首先,展览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及中西文化对话,构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例如《宣纸塔》(Rice Paper Pagoda)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宣纸,通过现代的灯光技术展示,构建了一座象征意义深远的塔。宣纸作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重要媒介,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和艺术成就,而灯光技术则引入现代元素,象征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与发展。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根基的同时,积极融入现代世界的态度,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其次,符号的使用与解读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手段。展览中大量使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这些符号通过文化编码和解读,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次意义。例如《魂·韵》(Soul·Rhyme)通过结合中国和外国的雕像元素,进行古代雕像的解构与当代再造,象征了文化交流与融合。雕塑作为一种高度象征性的艺术形式,中国和外国雕像的结合,象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鉴,传达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理念。通过文化编码和解读,这些符号传达了中国想要在全球语境中确立文化自信的开放态度。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理解和感受,体现了文化间的共鸣与互鉴。
(二)缺失当代中国形象的有效构建
通过上述符号分析及解读,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展览其本质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多维度他者视角下的身份叙事,是一种对于当代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展览的策划者试图融入多重眼光来构建中国形象,这是从一种自我想象中的多重他者眼光出发来构建所谓的中国身份,既想满足国际化,又想体现出一种传统主义,同时还想体现出一定的先锋性。这种多重眼光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官方视角下用于对外传播的中国艺术形象。但这种形象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已经脱离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并没有体现中国的当代文化,展览中当代文化身份与形象的构建非常有限,其本质还是一种对于自我形象的迷茫与焦虑。正如戴锦华所言:“犹如一个影院中的观众,是一个多元的、梦幻般的同时身置多处的主体。”[7]中国国家馆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构建出了一种具有多重他者视角、异域风情的“梦幻”身份与形象。可以说,展览中的作品通过国际化的艺术语言和符号,展示了一个开放包容、古今并存、异域风情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刻画了一个宏大空洞且让人产生刻板印象的中国形象。杨晶(2016)所说的“中国符号作为一种策略出现在当代艺术的场域之中,不管早年间为了进入西方的重要展览和艺术体制,还是后来希望威尼斯双年展为自己带来丰厚的资本,中国符号在迎合西方的同时,带了无法避免的缺憾。首先是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其次是自身文化身份的缺失与模糊”的情况依然存在[8]。
在实际效果方面,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虽然没有像第57届(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那样被网络及各大媒体评论家炮轰到体无完肤,没有出现“作者有自我东方主义感、作品只是玩弄传统巫术的东方符号”之类的评论,可以说通过系列传统与现代符号的运用向世界传递出了“和谐与共存”“开放与包容”等价值观,但整体受到的国际媒体关注度非常有限,抛去中国媒体的海外版,仅有Forbes、E-flux这两个主流媒体(E-flux为艺术主流媒体)的关注,其中Forbes给予了正面引导,而E-flux则只是对展览的介绍,从国际传播广度上来说较为有限,绝大多数的国际艺术主流媒体对展览均没有报道,更没有影评人对其进行展评撰写[9]。通过Instagram对威尼斯中国国家馆进行搜索的结果也非常有限,按照定位搜索“Chinese Pavilion at Venice Biennale(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则少于100条结果,而同样以定位搜索俄罗斯与德国国家馆则超过了1000条结果。
由此可见,中国当代艺术作品通过参与海外展览的方式逐渐走上了全球艺术舞台,但要从中真正建构起一个多元融合、自信独立又内涵丰富的中国形象,还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History.”La Biennale Di Venezia,La Biennale di Venezia[EB/OL].[2024-03-24].www.labiennale.org/en/history.
[2]郭鸿.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J].外语研究,2004(4):1-5,80.
[3]吕红周.美国符号学纲要[J].外国语文,2022(4):23-30.
[4]巴尔特.图像修辞学[M].方尔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61-272.
[5]详解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当代艺术与古代文献互动[EB/OL].[2024-05-15].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338401.
[6]徐翔.国际社交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及差异——基于网络文本的内容挖掘[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5(4):124-131.
[7]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68.
[8]杨晶.威尼斯双年展中的“中国符号”: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策略[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6:46.
[9]e-flux.Shi Hui and Wang Zhenghong at the 60th Venice Biennale[EB/OL].[2024-06-24].https://www.e-flux.com/announcements/605112/shi-hui-and-wang-zhenghong-at-the-60th-venice-biennale/.
作者简介:蒋天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