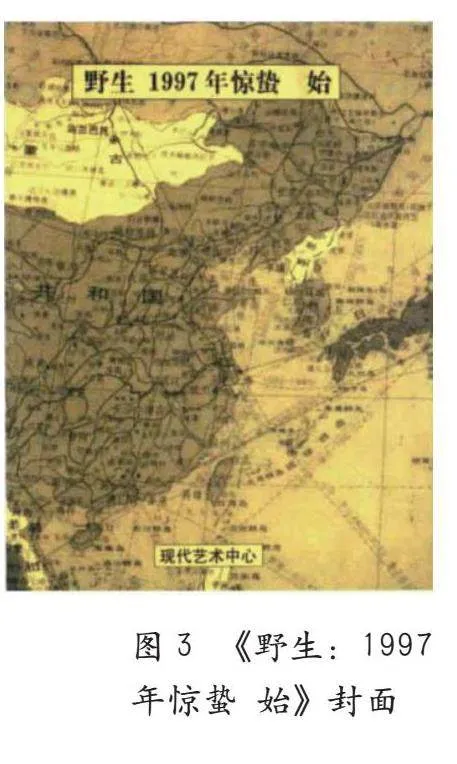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和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城市空间愈发追求公共性与人性化。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吸引全球公众学习与生活,同时聚集了各地艺术家及其作品。然而,近年来私人领域的快速扩展逐渐侵入城市公共空间,导致其逐步失落。与此同时,数字网络的普及使互动装置艺术走出美术馆与艺术馆,进入商场、江边等户外空间,引发广泛互动。本研究在这一背景下,从空间理论与艺术理论的角度探讨互动装置艺术对上海城市空间的介入作用。研究发现,互动装置艺术不仅能够通过促进观众的参与与互动,实现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还能促进观众与艺术家之间从建议到对话的发展,从而重构城市物理空间。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上海城市空间公共性的复兴与重现。
关键词:互动装置艺术;上海城市空间;公共性
一、背景
装置艺术作为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类型,自20世纪60、70时代诞生以来就广受关注,也诞生了许多诸如Frank Popper、Shaw and Hershman、Karina Smigla-Bobinski、草生弥间、徐冰、陈箴等著名装置艺术家。早期的装置艺术主要集中于室内环境,随着90年代计算机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互动装置艺术应运而生。它以“交互性”为典型特征,允许观众进入艺术品内部,与之互动并参与创作。观众在交互过程中可以与艺术家的思想进行互动,领略创作者的情感与创意,还可以自我生成个体的审美经验。
然而,计算机技术的崛起也使私人领域得以大规模扩张,进一步导致个人化、异质化的延展。这一私人化的扩张逐渐侵入城市公共空间,导致城市公共空间的逐步失落,私人化成为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发展中的一个意外结果[1]。城市空间本质上是公众的聚集地,承载着公共性特征,但随着私人空间的不断渗透,这一特征逐渐被侵蚀。近年来,随着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场域变革以及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艺术与大众之间的连接愈加紧密,这些具有艺术表征的场所逐渐贴近大众,互动装置艺术这类具有强烈“隔阂性”与门槛的艺术作品开始走出室内,频繁出现在商场、广场等户外空间,架起艺术家、公众、城市之间的沟通桥梁。
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互动装置艺术作为一种媒介,在介入城市空间时是否能够促进城市公共性的复兴与重构。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关注互动装置艺术如何发挥作用实现公共空间的重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其对城市空间公共性复兴的贡献,以期为未来的互动装置艺术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与发展建议。
二、城市空间与公共性
(一)公共性
在西方社会中,提起公共性概念不能跳过学者汉娜·阿伦特。她最早从学理的角度提出“公共性”概念,并对其做进一步的系统阐释。在她的三本著名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和《革命论》中论述了“公共性”的两层概念。一是“公开和在场”。公开意味着能够在公共场合被人群看见和听见;“在场”则指本世界的真实性,不是被虚构所塑造。二是“共同”,不同与“私有”概念,“共同”意味着世界对所有人都是共享的,不为某些人所独占[2]。随后,阿伦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出人类活动的三种形式,即劳动、工作和行动,它们分别对应着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的公共领域重现了古希腊城邦的人际联系,强调无需中介模式即可实现言行的共享与共通。继承阿伦特部分思想的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明确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即“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无障碍地开放,公众在公共领域内对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的批判性”[3]。在此维度上,公共性成为公共领域中的原则与象征。而后哈贝马斯引入交往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批判色彩的公共领域理论,转向理性与协商的公共领域理论[4]。即社会公共舆论与公共意见能够通过理性主体的自我表达与自我确认实现社会交往理性,促进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的产生。之后的理查德·桑内特更明确地把“公共性”与社会公共领域相关联,指出“在公共领域内,个体与他者相遇、交流、建立联系,这种充满丰富人际关系和意义的公共生活中,蕴含着公共性”[5]。
在我国,“公共性”的概念虽未被明确地提出,但始终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结构中。传统社会以儒家文明为基础,建立了家产式官僚制度、家族—宗族结构和小农经济结构,这些都内含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连接,实现了团体共商共建的公共性特征[6]。《礼记·礼运》中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说,蕴含着古人对于“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7]。韩非子所言的“自环者为私,背私者为公”也意味着“公”有公平、平等的意味,包含着对公共伦理性[8]。
(二)城市空间的公共性
传统的空间理论常把空间当作是一个客观的容器、或者某种行为发生的具体地点,或者是一种物理上的学理概念。在社会学领域中,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空间”与“城市”相结合,提出了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等。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包含着物理概念和精神概念两重含义,且会呈现出多种形态。然而,传统的二元划分限制了人们对于空间概念的认识,因此他引入了“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指出空间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9]在这种视角下,空间生产表现出城市的极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与空间性组织等现象。所谓的“空间生产”意指空间本身的生产,是一种动态的延展与流动。在这个维度上,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自由交往与活动,进而建立起一种动态空间即城市空间。
有学者指出,城市空间本身就拥有孕育公共性的潜力。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皆暗示着城市空间中存在着公共性。学者钱俊希、许凯和克劳斯·谢斯罗斯等人也认为,公众在使用公共空间进行交往和生活时,实质上生成了社会性集体意义和文化习惯,这种习惯构成了公共性。因此实现城市空间公共性的复兴需打破传统资本生产的单一逻辑,寻求空间生产的差异化。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作为生产维度的引入能够有效促进空间生产的多样性,进而推动公共性的实现。
(三)互动装置艺术
作为后现代艺术中的重要一环,装置艺术汲取了后现代主义中的“挪用拼贴”与“现成物”中的先锋因素,并逐渐衍生出自我特征,成为具有独特三维特征的艺术形式,通常是由两件以上的拾得物或现成品组装而成[10]。与雕塑艺术不同的是,装置艺术常在大型户外空间或画廊中展出,本质是对“可复制物品”的一种反叛。因此,对于装置艺术,不同学者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罗伯特·劳申伯格强调了装置艺术中“装配(combine)”的内涵[11],而毕晓普在其著作《装置艺术》中则以更加新颖的角度来定义了装置艺术,即其不再是一种传统固定视角被凝视,而是寻求与观众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这个一概念延展了装置艺术本身的特征,“主动性”与“自主性”被重点强调[12]。
不同于装置艺术,互动装置艺术自诞生之初便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多被归类于“新媒体艺术”。因此十分有必要从关键概念上进行深入探析。所谓“互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便被赋予了多重含义。贝丽尔·格雷厄姆和萨拉·库克指出,互动意味着“互相起到作用”,存在于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以及作品与观众之间[13]。然而,传统机器与人之间无法实现真正的互动对话,因为暂时的机器无法做到足够的智能来支撑起一场确乎平等的、发生在人与机器之间的对话。但是机器却能够打造出一个平台,使人际互动得以发生。中文中的“交互”也包含了“交流”“互动”等相关的含义,在中文《汉典》中交互包含着两个内涵:一是指相互、彼此;二是指交替地、相互地。在这两个内涵中都强调着双方的沟通与传播,是属于有来有回的行为。在英文的语境中,“交互”与互动单词都为“interact”,指代两个或以上的事物相互发生关联。在计算机语境下,“交互”是指称编程人员通过编写程序来向机器发出指令以控制该机器或程序的运行,程序在接收到指令后会根据编程人员的需求来相应地做出反应或反馈。无论何种领域与语境中的“交互”都指涉了同一语境下,参与活动的对象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因此,“交互”内在地蕴含了一种双向性。在这种交互过程中,需要观众实际参与到艺术作品中,或者根据系列指令去展开行动。莱诺·奥利·塔皮奥(Olli Tapio Leino)教授指出,在互动装置艺术中观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观众必须投入精力和体力来帮助实现艺术家的愿景,一个完整的交互作品必须要有观众的参与才完整[14]。在《重思策展:新媒体后的艺术》中也明确地指出,在当下的新媒体艺术和互动装置艺术中,艺术家、观众和参与者的角色被模糊了,有时候参与者就是观众。这表明,在定义上就已经蕴含了互动装置艺术具有实现介入艺术作品、城市社会空间的可能。
在艺术领域中,装置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空间艺术,因为其利用空间的架构来创作。它利用现成品与综合材料,创造出具有多样化形式语言的艺术,并将空间纳入创作之中,形成二维或三维的物质实体。互动装置艺术是装置艺术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进化版,即交互装置以计算机为综合材料来创作出具有互动性的艺术作品,促使真实物质与数字虚拟作进一步的结合,来形成物质与非物质、在场与非在场、交互与连接的多元混合。以列斐伏尔(1991)为出发点,学者Linda Ryan Bengtsson(2012)将空间视为社会空间,指出参与者可以在特定地方或地理区域进行协商与互动[15]。在此背景下,互动装置艺术的整合可能重塑社会空间的建设条件,进一步影响人类对空间的感知及与互动装置艺术的互动所产生的人际关系。
本研究以各位学者的空间理论为基点,侧重于把当前的空间分为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围绕城市空间公共性这一线索,探索互动装置艺术如何介入城市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进而引发城市空间公共性的复兴与重构。
三、互动装置艺术的介入实践:" " " " " " " " " " " " 城市空间公共性的复兴可能
(一)从观看到互动:城市社会空间的复兴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公民可以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最终达成一个公共意见以影响国家决策。公共领域是私人生活世界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政治系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促使整个社会整体与生活世界呈现出一种平衡有序的状态[16]。但哈贝马斯也提出现实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并不存在,但是公众可以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与哈贝马斯有所不同的是,桑内特在其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中指出,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会呈现出一定的分割与距离,人性的自我表达通常会表现在私人领域中。当公众到达公共空间也就是所谓的公共领域中时,会开始带上掩饰的面具开始表演,以掩饰本来的自我。在这种情境下,城市空间成为了一个舞台,在当中的每个公众都是一个戏子,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并开始交往。桑内特指出,这种便是公共领域和公共人的陷落,而艺术则是能够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即“艺术能够补偿伴随着陌尘人在街头上、在现代城市的公共领域中出现的死寂与冷漠”。
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就存在着艺术“介入”公众的案例,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曾在其论文《未来的艺术品》中指出“未来的艺术创作会是不记名的,会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以及观众的紧密结合是终结分裂和现代资本社会特殊化这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17]。在1958年,著名艺术家伊夫·克莱因在艾里斯·克莱特画廊创作的装置作品《虚空》横空出世,受到了诸多关注与争议。在这部作品中,因为艺术家本人并设置没有任何的物品和内容,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在这个房间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完全由观众本人来解读。观众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自由地解读这部作品,实现作者与观众的交互沟通。在学界看来,这部作品其实已经具备了介入城市公共艺术的可能性。
而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西方艺术界的激浪派事件以及偶发艺术将观众互动融入艺术创作中。著名装置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过一句著名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概念,强调社会上的每个公众都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能够拥有自主去解释艺术的权利,并且能够实际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成为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这个概念与博伊斯另外一个“社会雕塑”的概念相辅相成。“社会雕塑”指的是整个社会被看成是一件艺术品,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为这件作品贡献着自己的创意[18]。博伊斯的著名艺术作品《如何给死兔子解释艺术》便是社会雕塑概念的重要体现。该作品展现出了一副奇特又令人遐想的画面,蜂蜜涂满博伊斯整张脸并在脸上贴上金箔,脚上身着一双靴子并与一块铁板连接在一起。博伊斯的怀里抱着一只死去的兔子,而他正在对着兔子喃喃自语。他在表达什么?以及他是对谁说的?这一切的解释权都回归到观众身上,他把观众也当作是这件作品的一部分。可见,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地把将艺术的概念泛化,其实这也潜在地为装置艺术的交互性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博伊斯另一个著名的作品《七千棵橡树》就是在德国的卡塞尔艺术馆前的广场上摆放着七千块玄武石,并在每颗玄武石上都种上橡树。1987年,博伊斯的儿子温采尔种下了最后一棵橡树,标志着这个作品的完结。在这个作品中,每个公众可以自由地参与到橡树的植种。这种参与在不断完整作品本身的同时,也促使观众自身成为了艺术家。让七千个卡塞尔市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参与到艺术作品中,实现了艺术作品的公共性[19]。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装置艺术变得愈加流行,产出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艺术家们开始发散思维创作,装置艺术本身也脱离了“实体物”的控制,虚拟的材料和技术都能当作是创作材料。因此“新媒体艺术”“交互装置艺术”成了新型的创作形式。这一时期装置艺术的“交互性”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定点观赏”的审美习惯也逐渐被“在场感知”代替,观众成为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观众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成为常态。
互动装置艺术作为装置艺术的类别之一,不仅介入城市公共空间,也重新定义了艺术与公众的关系。在这当中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这种艺术形态会进行自我革新,二是互动装置艺术也有可能会催生出艺术与公众之间的新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艺术本身的功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赏性,而是转向了交互性。互动装置艺术打破了传统艺术空间的疆域,把所有的观众放置在同一个空间维度下,促使艺术家、观众、参与者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与交流。艺术家在通过观众与作品的互动中传达自身的想法,架构起双方沟通的桥梁,并把自身作品的解释权下放给观众,让观众成为艺术作品中的一环,参与到艺术的创作中,实现艺术的完整。观众在与作品的互动中体验艺术家其内在寓意,并通过自身的理解去形成新的寓意。而别的参与者在通过观察观众的互动来进一步产生新的想法与思考。在这个维度下,观众与观众、观众与艺术家、观众与艺术三者之间的精神空间进行联通共享,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互通共建,实现了城市社会空间公共性的复兴。
上海每年一度举办的油罐艺术节通过展出诸多互动装置艺术来重塑公众与艺术的关系,实现城市社会空间中公众、艺术、艺术家的多元互动。在2019年TeamLab携手油罐艺术界展出的“teamLab油罐中的水粒子世界”中,TeamLab团队以“水”作为为主线,实现了与展览载体的艺术中心5号“油罐”之间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影响。在这过程中作品与作品、人与作品之间的边界被消融。在展览中的五个作品皆把观众带入其中,推动观众利用互动实现与艺术作品、艺术家、其他观众之间精神空间、实体空间交往的可能。例如在第二个作品《花与人,不为所 控却能共生》中,当观众站立其中,花朵便能“感知”到其的存在,便会开始绽放。而当观众在有意无意中有了触摸与踩踏时,会造成花朵凋谢。此外,当不同的人在当中漫步之时,都会造成花朵盛开凋谢的改变[20]。漫步在其中的观众通过与花的互动,感受到了与“花”的连接,也进一步实现了与艺术家、艺术作品精神空间的共通。
(二)从建议到对话:城市地理空间重构的可能
艺术介入城市空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一日之功,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情境主义国际都提倡“艺术介入生活”及“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概念,著名的学者列斐伏尔和居伊·德波都是该概念的提倡者。
列斐伏尔的系列空间理论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在超现实主义维度下,“指向日常生活的主要问题”成为了核心要义。这当中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艺术生活化,即超现实主义者们会致力于把日常生活的部分来进一步陌生化,例如把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来把它放置在异乎寻常的神奇组合中,促使日常的东西变得焕然一新,出现了新的形态[21]。二是“在场的瞬间”呈现。在超现实主义中,日常是各种游遁、偶发事件和暗示性的并置,处处充满奇迹。而后的情境主义国际也表明了艺术能够参与到日常生活空间中呈现出新的形态。作为20世纪法国的重要“政治-艺术运动”,其致力于寻求对艺术和政治的新的结合创造性表达,会通过创作大量的艺术和政治合成作品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帮助人们打破常规,去挑战社会的不公正事件,促进城市社会的改革与建设[22]。《景观社会》的作者居伊·德波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重要成员,观察到了现代都市中的巨大异化现象,是商品性在媒介世代下的放大,进而导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被一种巨大的景观所包围。这种媒介包围的景观使人们远离自然,而被迫生活在第二自然中。同时在景观中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景观进一步对人们进行控制。因此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景观化和商品化,促使真正的生存空间和物理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为解决景观社会下的个人异化和空间压缩问题,情境主义国际者们提倡将现代主义大都市作为一个大型游戏场,在这个游戏场中采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戏谑地改造城市空间属性,进而改变传统的都市人们被驯化的情况,促使人们从原有的场景中脱离出来,拥有更多的主动性。
在超现实主义与情境主义中,艺术介入生活的深层含义在于打破日常的单一性与重复性,赋予城市空间新的灵活性与公共性,重新构建城市物理空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艺术结合。
何为日常生活?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被超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异化的现象形态,而是一个异化不断产生又不断被克服,能量无穷的、永恒轮回的存在论世界[23]。这种思想是在马克思“异化”思想上的运用与升华,列斐伏尔认为通过艺术美学的介入,能够实现“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并最终再现日常生活的形式。
在21世纪初,巴黎的“巴黎海滩”活动是艺术介入日常生活空间、重构城市物理空间的经典案例。巴黎海滩活动促使了传统公共空间塞纳河右岸和巴黎市政厅广场被海边的沙滩、躺椅、舞池等设施占领,整个空间宛若是一个大型的交互装置,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其中,与海滩、草坪、舞池、躺椅等进行互动。这种艺术空间的创作促使传统的物理空间被进一步重构,而艺术家、市民、观众成为了城市物理空间的设计师,摆脱了传统的空间语境的影响,把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在当前的背景下,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消解了美术馆、艺术馆等对艺术的统治,传统美术馆和艺术馆中核心的“展示”“陈列”“收藏”和“购买”等功能也一步步地被许多新的空间形式所取代。美术馆所建立起来的“隔墙”正在被数字技术所打破,进而转向了一种无形态、无边界的新型空间形态。网络技术的可获取性,也潜在地促使艺术介入到城市空间中成为常态,商场、地铁、公园、江边、学校等场所都可成为互动装置艺术落地的新空间,而这种转变也逐渐促使传统物理空间的规划得以重构。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艺术参与到城市空间中逐渐成为了常态。备受瞩目的上海双年展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以上海为背景的当代艺术博览会,进一步探究上海城市与艺术展览之间互动关系的大型展览。作为已经举办了十四届的优秀展览,其本身就已经作为上海城市空间中的一部分。以往的上海双年展都以特定的主题来讲述上海故事,并把艺术展览开设在上海各个角落,实现上海艺术介入城市空间。在2023年举行的第14届上海双年展通过聚焦“宇宙电影”主题,借助绘画、装置、雕塑、影像、行为和文献等多元艺术形式,以全球化表达和艺术性叙事,立体呈现国内外对宇宙哲思和宇宙美学的不同诠释,探讨宇宙现象与人类生活的关系[24]。这个展览项目之一的“类地登录:行星候选者”就通过影片胶片形式展现出对于宇宙、艺术的想象与思考,同时结合VR、胶片等形式实现观众与展览作品的互动,让观众们在虚拟和现实空间中来回穿梭,实现真正的艺术介入生活。
此外,上海艺术节、TeamLab等艺术活动的开展,实现了艺术家们真正地介入到城市空间的建设中,为推动上海市的空间设计提供多维可能性,为实现上海公共空间的公共性重构添砖加瓦。
四、结语
不论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或是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亦或是桑内特的城市公共人理论,都在强调着艺术作为一种新形态与新方法介入城市空间的可能性。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私人领域的逐渐扩张促使传统公共空间的缩小,进而引发公共性陷落危机。然而,数字技术在缩小私人领域的同时,也为艺术介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即以新媒体技术为综合材料创作的互动装置艺术渐渐发展成为城市空间中不同于传统以往艺术的新型形式,也是如今城市文明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力量。它以特殊的交互性促进公众从参与走向互动,实际参与到艺术作品创作中,使得观众、艺术家、参与者三者之间的社会空间阈限被打破,实现了共通与交流。与此同时,互动装置艺术不仅介入城市物理空间,还推动了艺术生活化的可能性,削弱了美术馆、艺术馆等传统场域的统治地位,促进了城市物理空间的再造与重构。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集结着大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每天都有不同的互动装置艺术作品设计与展示,实质上已将这一艺术形式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进一步推动公共性的复兴与重构。然而,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互动装置艺术仍面临诸多挑战,如灵活性不足等问题。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或许能更好地实现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从而推动城市空间公共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殷依文.当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私人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2]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49-74.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6-205.
[4]王凤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J].理论学刊,2003(5):38-41.
[5]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1-89.
[6]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J].社会学研究,1997(4):110-118.
[7]黄朝钦.公共性视域下社会化媒体的公共表达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9.
[8]朱嘉,吴晓,王晓.基于GIS技术的城市开敞空间适宜性布局[J].风景园林,2019(9):90-95.
[9]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1.
[10]萧元.装置艺术的概念及其呈现方式[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26-138.
[11]MARYLYNNKOTZ,RAUSCHENBERG.Art and Life[M].NewYork:H.N.Abrams,2004:84.
[12]Claire Bishop.Installation Art:A Critical History[M].London:Routledge,2005:144
[13]格雷厄姆,库克,龙星如.重思策展:新媒体后的艺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221-224.
[14]LeinoOT.From interactivity to playability[J].ISEA,2013.
[15]Linda Ryan Bengtsson. Re-negotiating social space:Public art installations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M].Karlstad University,Faculty of Economic Sciences,Communication and IT,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2012.
[16]陈立镜.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8.
[17]Danielle Follett,Anke Finger.The aesthetics of the total artwork:on borders and fragment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Md.,2011.
[18]彭伟,夫博.艺术介入社会:博伊斯和他的作品[J].公共艺术,2016(3):50-60.
[19]姜子闻.装置艺术介入城市公共艺术及其交互性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22.
[20]国际花艺资讯.火爆全球的teamlab和Klaus都来到了上海[EB/OL].[2019-04-15].https://zhuanlan.zhihu.com/p/62448310.
[21]塞托.日常生活的实践之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译.南京:南京大学,2015:174.
[22]张一兵.烈火吞噬的革命情境建构: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的构境论映像[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6):165.
[23]孔子显,王常柱.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逻辑起点、主线及其当代启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3(9):25-31.
[24]上海市人民政府.“宇宙电影——第十四届上海双年展”今日开幕[EB/OL].[2023-11-08].https://www.shanghai.gov.cn/nw31406/20231109/1636a36f74084af39d425f1e9783d3e8.html.
作者简介:刘小莉,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型社传媒与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