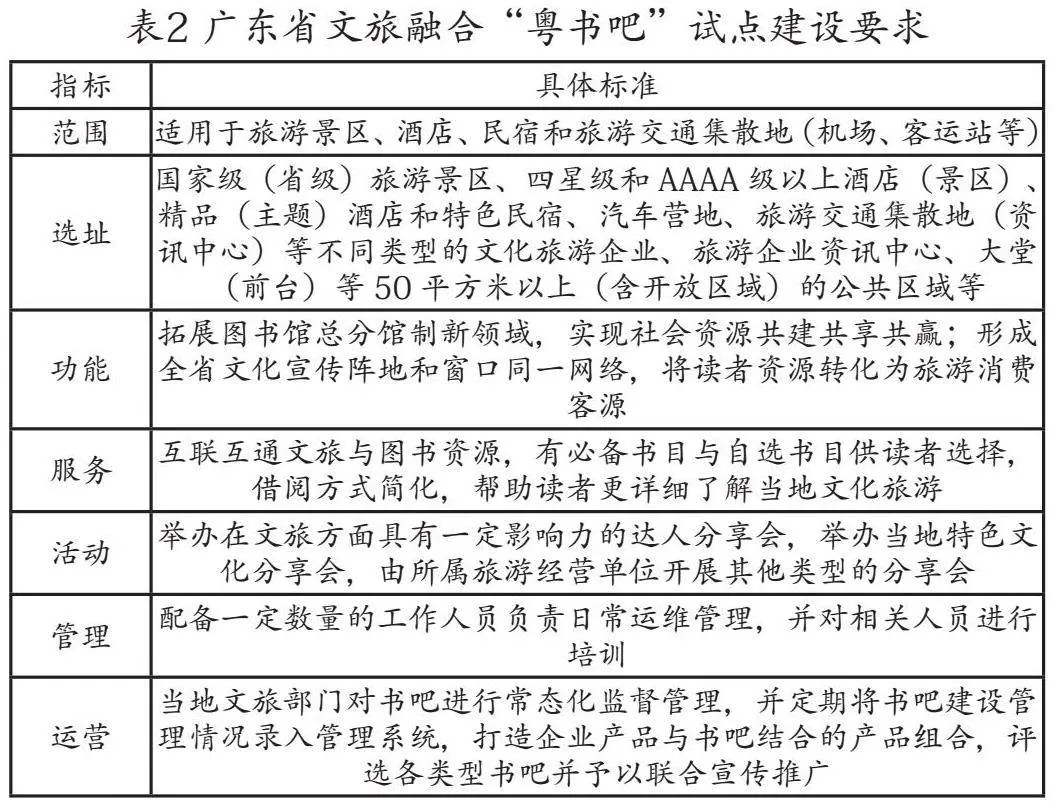摘要: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传播面临挑战与机遇。中国是全球不可或缺的重要稳定力量,中国文化对国内外影响力的提振迫在眉睫。现提出在数字时代充分利用全真互联网与AI技术相结合,以“新质”文化传播增强中国文化叙事能力的观点,分别论述了文化叙事生态构建所需的三条“新质”技术路径,阐述了叙事生态构建的参与者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价值观与情感联系的方法,并批判性地提出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三大显著问题,以供业界参考。
背景概述
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体。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文化在语言文字、宗教哲学、艺术文学、节日习俗等方面,对当今亚太地区的影响是持续而多维的。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GDP总量占全球60%,贸易总量占全球的近一半;随着2020年RCEP的正式签署,全球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贸易、投资和产业从欧洲与北美向亚太地区聚集,为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机遇与新动力,世界的文化格局,正在迎来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作为该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任一领域“动一动”都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蝴蝶效应,鉴于此,中国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不可或缺的重要稳定力量。
新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信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词汇,它不仅涵盖自我文化认同与外来文化包容,还指向向外反射的价值观念与信仰体系。当代,某一文化现象不能单独归结于某一地区或国家,所以承认文化的多元杂糅是打破封闭式文化保护的重要观念变革,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经之路,此番,文化内容之“新变”必然产生文化的“新质”传播。
中国文化影响力现状
中国文化影响力与西方文化影响力在“初速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被工业革命、科技进步与军事实力的崛起迅速推动。从文化影响史来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电报与无线电发明与广泛应用之时,中国错过了电子传播时代的“黄金时期”;西方大众文化传播形式如电影、流行音乐、时尚等出现的时机较中国更早,具有成熟的传播策略与体系。从文化影响域来看,中国文化因其历史溯源久远且文化内涵理解成本较高,因而深度的文化探讨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在大众传播上则存在着阻力;全球的汉语使用总人数虽然最多,但国际普及率相较英文却非常低,文化传播存在区域性局限。前数字时代,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使西方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更加深远,使学术界在近百年间不得不先站在西方叙事语境下回望、引导、批判、研究本国的文化。
中国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也会为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带来阻碍。首先,国际话语权被削弱,会影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推广,影响世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主张的认可度。其次,经贸合作与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与动力不足,由此带来的技术引进与人才交流受限问题,制约了技术的创新。但随着互联网与AI技术的发展,数字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影响力逐渐迎来“弯道超车”的宝贵时机。互联网与AI构建的知识平权让传统文化的考古周期被大幅缩短,汉语的语言局限也被AI实时辅助翻译迅速突破。虽然上述两大发展趋势能够改变中国文化影响域的问题,但是仅从技术手段上迭代并不足以激活中国文化对内、对外的影响力,其最主要困境仍然在于国内外大众对于中国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思辨尚浅。只有中国文化运用“活态”叙事语境,同时具备泛度与深度,才可能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活态+多模态”叙事语境构建
文化传播的方式用“叙事”替代“论述”将更为柔软,且更具感染力与渗透力。叙事是传统的表达方式,也正因为其普通与常见,反而被忽略其重要性。相较于论述的抽象性和结构性逻辑,大脑中的叙事生成过程是非线性动态图像的叠加。叙事作为文化的载体,因其情节关注度高、容易被记忆和复述,从而具有极强的文化输出隐蔽性,每一层受众在参与叙事的过程中都会根据自身的经验与情感对叙事进行二次解读,以形成“个性化在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叙事从“故”事被进一步替代为“即”时事件,受众的数字在场成为常态;叙事从过去的自上而下逐渐过渡到上下贯通,开源、共享、平权构成了叙事的新特征。文化传播的内容与时间在愈加“碎片化”的同时变得“轻量级”,从而灵动地渗透至人的生活。
碎片化叙事是重构宏大叙事的材料,宏大叙事是碎片化叙事的主线,于文化叙事而言,只有两方面兼顾才能在主角视角的故事细节与上帝视角的文化渊源之间来回体验。构建一个灵活的、多模态的叙事语义网络,既可以有针对性地挖掘文化数据分析与热点,又可以创造多模态叙事实体节点,还可以在原创节点上进行再度创新,以进一步丰富该语义网络。从社交媒体网络的固有特性和网民的阅读习惯来看,具象化、短小的内容更容易使人关注,相反,理性的、晦涩的、冗长的信息往往被人忽视。大众化自媒体的感性叙事是铺开文化传播面的重要途径,同时专业媒体的专业度和可信度也是网络所需要的,使公众不至于在“众声喧哗”中迷失方向。以多模态媒介叙事构建关于中国概念、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风格的“活的”语义生态,强化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语义,能有效地对有关文化的概念权重进行再分配,以平衡非中文语境下的文化解释。
AI辅助数据挖掘热点叙事
2022年,通用人工智能ChatGPT横空出世,促进全球AI行业实现井喷式发展。同年,我国《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发布,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数据矩阵,标志着我国正在建设新时代数字文化强国。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语义网,其包含的信息不仅可以供人阅读,也能被计算机理解与处理,涉及资源描述框架(RDF)、网络本体语言(OWL)、RDF查询语言(SPARQL)等,使其在知识表示、推理、交换、复用等方面成为可能。依托互联网进行中国文化语义的数字生态建立,是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国家话语打基础。笔者预测,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对互联网自然语言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将成为普通互联网用户的新常态。
在互联网话题海洋中,快速定位年度热词是获取或创建文化叙事的捷径,通过问题链引导AI进行分析让这个过程变得非常容易。首先,利用AI对互联网内容进行平均采样,这一过程可覆盖更广泛的话题并杜绝用户的历史行为所带来的偏好和偏见;其次,通过词云权重快速定位当前的叙事热点,这一主动的过程可以削弱算法推送所导致的信息茧房;最后,利用AI对当前热点和过去热点进行比较,反映人们关注趋势的变化。这些热点既可以作为兴趣方向供参与者选择性获知,也可以激发参与者新的内容创作灵感。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每一次提问都贡献了有关该叙事的内容供AI学习,也贡献了搜索记录供引擎进行数据收集与算法优化,从而成为该内容数字叙事生态的一部分。
全真互联网承载具身叙事
系统功能符号学认为符号模态通常包括语言、图像、声音、空间和身体动作等。符号可以是具体也可以是抽象的,它们是人类交流和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指的多样性特征决定了符号的物理性可以是多形式的;其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任意性决定了符号可以被设计和引导;其约定俗成的特性决定了符号必须被群体所接受与使用;其系统性特征决定了符号必须存在于与其他符号相互作用的空间中才能具有意义。全真互联网提供给用户虚体数字在场的条件,为多模态的符号构建意义网络并实行文化传播奠定基础。
对符号的狭义理解多集中在其体现的静态化、图像化特征上,人们往往会忽略,转瞬即逝的肢体动作也能成为符号并传递特定信息。全真互联网放大了虚拟具身叙事的功能,与上一代互联网相比,其沉浸感和临场感凸出,是动作符号模态传播的优良载体。通过虚拟数字形象在特定公共虚拟平台进行的某种数字行为,能够使传播者、受众与环境跨越时空实现数字在场,通过语言、肢体语言的互动以及与环境的配合,达成文化的具身传播,扩大文化的“活态”影响。例如,武术中的起式抱拳礼、围棋中的持子姿势、敦煌舞中的“反弹琵琶”、潮汕英歌舞等都可以被抽取出来,用于驱动各种平台的三维虚拟数字人,以制衡当前知名动作捕捉数据库几乎被西方占据的形势。动作符号的缺点是在传递复杂含义时功能较为欠缺,关于它的研究适用于一般性多模态话语素材的表意分析,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能对语料素材进行较为准确的诠释,但在涉及历史、语言情境和文化等复杂的跨文化传播现象下,单一方法的使用有可能会出现解释力度不足的问题。
分形传播“链条式二创”叙事
狭义的“二创”是相对于“原创”而言的第二次创作,而本文将“二创”解释为相对于任意一次创作(包括二创)后的迭代创作,其创作结果的形式不限,仅仅维持创作内容的叙事关联。在遵守版权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前提下,注明引用来源,加入迭代内容,能提高内容生产与传播效率,有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原创内容耗时长、传播方向单一、内容原始,当内容发布后会经历“分形”传播,而该内容第一级传播者的浏览历史、转载链接、截屏录制等对原始内容的操作记录会引导第二级传播者向上溯源,以此类推。根据熵增定律,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涌入视线的杂乱内容必然会使人们对该内容的关注兴趣降低,导致传播减速传播甚至传播断链;而链条式二创则衔接了源内容和新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有效地延长了关于该内容的叙事生命周期,进而达成对文化影响力的拓展。其一,其能够扩大受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视角诠释原作,可以吸引原作所在圈层以外的人群的关注,使一级传播圈转变为二级创作圈。其二,二创在为原始内容注入新创意时缩短了溯源的周期,不仅为原作收获关注,也在提升自身关注的同时提高了再创生产力。其三,二创本身是一个新内容,但由于它的创作门槛较低因而可以保持传播者的参与兴趣,可以为中国文化叙事生态贡献一个语义节点。
AI数字时代的文化叙事生态构建关涉三个思维模式变革,文化内容建设思维要从“直觉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文化传播思维要从“图文传播”转向“虚拟具身传播”,文化的延续与重塑思维从“原发性创作”过渡到“模块化、接口化创作”。成功的文化叙事不仅仅是对单个“故事”流畅地讲述,它需要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完整生态来托举,即完善的中国文化符号“能指”与“所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与链式二创。此外,极其重要的是,要将中国文化的叙事生态搭建为与参与者建立起深层次的价值观与情感联系的膏腴之壤,让每一次叙事有脉可通、有源可溯、有据可依。
文化新质传播的衍生问题
文化叙事语境的活泛文化生态是由传统与新兴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文化的理论内容、文化集中展示场地、文化创造者、传承者、解读者、批评者、教育者、文化周边产品制造商等共同构建,在任一环节都存在数字技术支撑的、不断链的文化“泛”传播。虽然这一生态可以维护文化叙事的完整性,但也将面对下述问题。
文化产品泛滥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相互配合将文化内容的“创造”导向“生产”,文化内容参与者难以避免地陷入消费主义思维。法兰克福学派曾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认为它并非“大众文化”的当代形式,而认为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技术的成果是标准化、同一性的,是对艺术的背离,并带来价值危机。诉诸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快速制造与复制,使文化产品的数量远超文化消费的需求;因为商业利益驱动而迎合广大用户对新奇与即时满足的追求,不断推出同质化、低俗化的“新”内容,从而降低对文化产品精神追求的满足。同质化文化产品的大量涌现,必然使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迫使文化工业继续推出新的刺激内容吸引消费者注意力,进一步加剧文化泛滥与浪费。
陌生文化偏见
文化原本就是具有地区性质的概念,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人们对区域文化的隔阂。全真互联网虽然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实现跨越时空的即时传播,但这并没有留给人在现实的物理空间中逐步适应一个陌生文化的“过程”。全真互联网空间中,用户的数字身份是虚拟具身传播的载体,其行为通过网络可能被其他用户捕捉,并永久留痕。互联网屏障让人们降低了对地区文化的敏感性以及对自身约束的道德感,因而极易导致一些因缺乏尊重与理解的歧视,甚至违背伦理道德的数字行为的发生,在进一步加深文化偏见的同时,埋下不同文化间的敌意,也就更谈不上对不同文化叙事的认同了。
过度技术依赖
尽管全真互联网能够将现实文化传播以沉浸方式“近距离”呈现在用户面前,但它仍然无法替代现实人际交往中文化的情怀传播。智能时代,“化”正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迭代悄然散播“智能崇拜”,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呈现了技术狂热和人性关怀缺失的社会文化特征。媒介的掌控权由第三方操控,媒介一方面满足了某些受众的全新需求,提高了社会生活效率;另一方面,媒介又用娱乐化的碎片化信息填补用户节省下来的时间,使人们失去深入了解和体验生活的机会。如果我们的世界变得过分地依赖于这些系统的功能,那么它的自由度就会降低,意义也将降低,人类的辨别力也会下降。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世界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交流,以促使双方建立更完善的世界观,所以互联网技术与AI辅助应被作为帮助个体走进真实文化环境的一块“跳板”,而并非代替人的感官去感受世界。
数字时代的中国文化话语建设任重而道远。知识平权的当代,文化传播不再是靠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所作出的“完成时”定义,而是依靠大众共同将文化的新质传播推向“进行时”。信息接收者同样是信息生产者,这“两位一体”的身份在当代大众身上展现前所未有的平等性。大众在参与中国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只需具备“鉴往喻今”的文化传播观念便可完善文化叙事生态。一是谋篇布局观,中国文化叙事生态的建立,是为了让中国的发声具备多元的证据支撑环境;二是通权达变观,利用中式动作符号实现虚拟环境具身文化传播,建立中国动态符号的辨识度;三是抛砖引玉观,让文化内容创新站在前人基础之上,延续中国文化的“活态”传承生命周期。我们在享受文化新质传播带来红利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其衍生的问题,以避免其负面效应对叙事语境生态构建的反噬,准备充分地践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新时代“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建设尽一份力。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虚拟现实互联网的红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2SKJD080)。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